萬物互聯?/技術決定論與文化決定論
本章將討論萬物互聯?中的技術決定論與文化決定論,以及它們對數字媒體和日常社會的影響。在歷史部分,我們將討論文化決定論和技術決定論的歷史背景,以及它們如何成為文化決定技術還是技術決定文化的爭論。歷史部分還將討論對文化決定論和技術決定論有重大影響的關鍵理論家。
在定義章節中,我們將討論這些術語的定義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巨大變化的。隨著新媒體和文化運動的興起,技術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不斷發展,成為理論家和哲學家之間爭論的主題,這一部分還將探討什麼是“新媒體”。
在下一章主要概念中,我們將探索技術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的一些主要概念,並提供理論示例。本章將分別討論技術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並試圖區分兩者。本章的目的是透過這些理論的主要概念,描繪技術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的概況。
在反對部分,我們將討論一些反對其中一個或兩個理論的理論家,並展示他們的觀點以及他們提出的想法。
最後,未來章節將深入探討技術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在未來幾年對社會的影響,重點關注以下主題:民族認同、政治安排、壓制激進運動的規律、工作效率、就業和交流。
理解文化決定論的定義,一個好的方法是將這個術語拆分開。
什麼是文化?什麼是決定論?文化是區別一個群體與另一個群體的態度、習俗和信仰的總和。決定論是一個哲學觀點,認為每一個事件都有無法被其他方式導致的條件。因此,文化決定論是一個理論,它認為我們的情緒和行為水平取決於我們成長所在的文化,這意味著我們的文化和社會影響力支配生物影響力。
文化決定論讓我們思考我們是否相信文化塑造了我們是誰。如果你是在不同的文化中長大,你會和現在的你不同嗎?因此,文化決定論意味著我們的想法、情感和行為模式受到我們成長所在的文化的影響。我們透過社會學習成為我們,這包括像吃飯、交流和穿著這樣的細微習慣。 [1]
文化決定論理論 [2]本身比技術決定論理論 [3]要古老得多,因為在技術完全發展之前,文化被認為決定性地塑造了行為。事實上,在古希臘,人們普遍認為,只有那些說他們語言的人才能理解他們的行為、價值觀和社會體系。希臘人認為他們的文化是定義他們為一個民族的,這是你必須透過成為他們社會的一部分來學習的。文化決定論支援這樣一種觀點,即我們的情緒和行為模式是由我們成長所在的文化塑造和塑造的。人們還認為,該理論也可以應用於經濟體系和政治體系。 [4]
弗朗茲·博阿斯是一位德裔美國人類學家,即對起源和行為的科學研究,他是最初認為人類行為受文化起源而非生物影響影響的思想的創始人。他建議,要屬於某個社會群體,你必須遵守已經存在的文化規範,因為文化微妙地決定著我們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 [5]
文化決定論者強調我們文化的歷史條件以及這些條件如何決定我們的行為。這表明文化是決定社會如何創造和發展技術以及它如何使用的控制因素。 [6] 這與技術決定論者的觀點相矛盾。許多理論家對該理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例如羅伯特·巴羅、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和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
上面介紹了決定論與人類意志創造自我的概念,它遵循了關於人性的標準模型,即試圖界定人類可以從自然中分離併成為自身創造者的界限。 這隱含著一個未明言的假設,即人類擁有自由意志,僅僅是需要確定這種獨特屬性何時開始發揮作用的問題。 因此,我們被告知文化決定論使人們從生物決定論中解放出來。 在這本著作的後面,用“超級有機體”來指代人類社會,提及了一些人試圖闡述完全決定論的社會秩序模型。 上面給出的“決定論”的定義有助於支援人類從自然控制中解放出來的模型,因為它說決定論意味著“條件”不可能是其他狀態,因此沒有額外的選擇因素是相關的,因此否定了自由意志的任何可能性。 這種決定論的定義因此圍繞著選擇的原則展開,而這種將“決定論”的含義與“選擇”的含義聯絡起來的做法並沒有被明確說明。
這將我們帶到了決定論與人類生活中自由意志的關鍵問題,因為我們今天所知的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很多東西都依賴於自由意志的概念,而上面對文化決定論的解釋遵循了必要的文化模式,即自由意志在某個時刻被啟動。“決定論”的定義,如果沒有文化力量對其定義的限制,將會有所不同。 它會允許其含義由科學客觀性的抽象原則來決定,並將它的含義與自然存在物件聯絡起來,在本例中,人類社會被視為一個自然物件,它只能是它本身的樣子,但不是因為“條件”必須是它本身的樣子,而是因為這個物件可以被認定為一個自然物件,而自然物件只能是它本身的樣子;這是一個使科學成為可能的原則。 超有機體社會模型是唯一能夠實現這種決定論理想的模型。 科學導向的決定論定義必然是不妥協的,它不容許任何替代方案,因為它斷言人類可以被理解為完全自然的形態,而我們在本著作中發現決定論定義的其他方面與這種科學定義背道而馳,例如“強硬決定論”的概念,它被定義為在無法證實的環境中使用時的毫無道理的偏執。
至少,上面對這本著作中關鍵概念的定義相當膚淺,它支援一種符合既定學術權威的主題觀點,並沒有將主題開啟,讓讀者對其有一個更全面的理解,而這正是這些關鍵概念所暗示的。
說文化使人類從生物因素中解放出來是對所討論概念的操縱。 它假設文化不是一種生物必然性,而實際上,文化顯然是一種生物必然性,因為語言的力量創造了文化,使文化成為完全基於人類生物學的行為活動,語言是個人解剖學特徵。 上述對社會的描述從一個觀察點開始,假設人是人類動物,然後從這個觀察點開始討論社會實體,以一種贊成或反對的方式,從而使兩種選擇都被認為是同樣有缺陷的,這一點是積極的,因為它們都允許至少在原則上維護自由意志的政治理想,因為它們都認為個人是獨立存在的個體。 而真正的選擇,即允許決定論提供一個真正的選擇,必須基於一種自然主義的觀點,即人類動物是一個超級有機體。 在人類社會生活背景下,決定論的正確定義表現在人類動物是超級有機體,而不是人。 這種定義將“決定論”的含義從“選擇”的含義中解放出來,透過將決定論的含義與一個自然發生的物理實體聯絡起來,從而可以從這個實體中尋找決定論因素,並將所有由此產生的決定論性質的思想與之聯絡起來。
羅伯特·巴羅
[edit | edit source]美國人羅伯特·約瑟夫·巴羅(1944-2015)研究宏觀經濟學,並在哈佛大學任教。 在此之前,巴羅曾在加州理工學院獲得了物理學學士學位。 畢業後,他將注意力轉向經濟學。 他於 1970 年在該領域獲得了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 他為《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每日新聞》等出版物撰寫了大量關於宏觀經濟學和經濟的著作。
在巴羅之前,歌德、費希特、奧古斯特和施萊格爾等作家曾寫過關於浪漫主義的著作,認為浪漫主義對文化決定論產生了很大影響。 這種觀點認為個人的價值觀和習俗是相互關聯的,並且受地理環境和周圍環境的啟發。
這可以與媒體理論一起研究,媒體理論是關於組織媒體與社會之間關係的社會-政治-哲學原則的理論。 該理論允許作家對媒體對社會的影響力進行自己的解讀。 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大眾媒體原則的關鍵概念往往與我們在社會中所擁有的主要價值觀和定位相一致。
一些作家認為,政治安排是由大眾媒體決定的。 但是巴羅認為,在決定政治安排時,實際上是個人行為和價值觀的影響更大。 因此,巴羅會認為,與技術本身相比,文化對社會行為的影響更大。
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
[edit | edit source]
卡爾·威廉·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出生於 1772 年,是德國詩人和著名的文學和哲學人物,他是耶拿浪漫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也是比較語言學的先驅。 他是文化決定論作為一種理論發展中的重要人物。[7]
浪漫主義,以其對強烈情感和個性的強調,以及對環境和歷史的崇拜,受到了文化決定論的很大影響。[8] 包括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在內的許多作家都為這場藝術和文學運動做出了貢獻。 浪漫主義是由社會和文化塑造的,特別是與地理位置相關聯。 與作家所在地相關的社會實踐影響了藝術形式,而不是主題的客觀規則。 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的著作影響了浪漫主義,從而證明了社會和文化可以推動社會演化。 文化決定論者的觀點是,權力關係是由周圍的大眾媒體建立的,這些媒體引導著社會變革。[9]
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
[edit | edit source]
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是一位德國哲學家,他生活於 1762 年至 1814 年,他創造了命題-反命題-綜合命題。 他受到伊曼努爾·康德著作的極大影響和鼓勵,尤其是關於物自體的存在——他根據自己的感知和信念發展了這一概念——費希特對意識的概念特別感興趣。
他提出了一種名為“科學學”的哲學體系(《知識科學基礎》),其中“解釋了自由意志、道德責任的行動者如何同時被認為是時空因果關係物質物件的世界的組成部分”。[10] 丹·佈雷澤爾 (2001) 說
- ”因此,費希特認為,哲學的第一個任務是發現一個單一的、不言而喻的起點或第一原則,從這個原則出發,人們可以“推匯出”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也就是說,我們體驗自己作為有限的認知者和有限的行動者的經驗。 “[10]
費希特在工作中如此專注於“自我”和自我意識,以至於他的著作中甚至沒有提到技術決定論。 這可能表明他完全相信任何決定論都起源於個人的動機,因此支援文化決定論的觀點。“費希特將他的工作的力度指向了決定論的含義,而是尋求人類自由或能動性的可能性。”[11] 這段引言可能會否認任何形式的決定論,但它明確地將人類意識定義為行動的起源。 它說,自由和能動性並不能決定行動,而是適應和促進行動。 在與費希特的信仰相關的決定論問題上,可以將其與比技術決定論或文化決定論更以自然為中心的立場聯絡起來——儘管它比技術決定論更文化決定論。 隨著人類自由被承認和探索,文化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技術。
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
[edit | edit source]
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是一位德國作家和政治家。 他是 19 世紀初浪漫主義時期的作家;一場藝術、文學和智力運動。 浪漫主義受到了文化決定論理論的很大影響。 然而,歌德並不相信技術或決定論的社會發展觀。 相反,他認為世界是透過持續的、外部的和內部的衝突而發展起來的。
哲學有兩類:教條主義和非教條主義[12] 歌德及其作品屬於教條主義哲學的範疇,因為這種哲學分支不是從對自然的觀察開始,而是將哲學視角置於自然之上。歌德的觀點和信念是相似的,因此在社會中形成了一個推測性和建設性的體系。
最初,歌德受到自然科學思想家的啟發,喬爾達諾·布魯諾 和 巴魯赫·斯賓諾莎,但後來他另闢蹊徑,歌德的哲學著作成為展現對人類真諦和深刻理解的作品。歌德認為,要了解自己,必須履行對自己的責任。如果你盡到自己的責任,你就會找到自己是誰,這就是為什麼歌德不同意文化決定論的著作。歌德無法認同這種認為我們的文化決定了我們是誰的決定論觀點,也不願超越這種觀點。
帕特里克·布坎南
[edit | edit source]帕特里克·布坎南,暱稱“帕特”,是一位古保守派政治評論員。古保守主義,主要在美國使用,是一種政治哲學,側重於宗教、地區、國家和西方身份。[13] 古保守主義者可以被視為“老保守派”。布坎南還是一名作家、廣播員和政治家。他是政治界的重要領導人,曾擔任理查德·尼克松、傑拉爾德·福特和羅納德·里根的資深顧問。他曾試圖在 1992 年和 1996 年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如今,帕特里克·布坎南聲稱,社會中的文化標準是決定我們政治安排行為的主要因素。布坎南因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而被視為古保守派,他認為文化決定論是當今保守派的主要爭論話題。
布坎南仍然擁有一個活躍的官方網站,可以在這裡找到:http://buchanan.org/blog。
技術決定論
[edit | edit source]為了定義這個複雜的術語,將技術和決定論分開會更容易。技術是技能和方法的集合,用於為實際目的生成科學知識。如前所述,決定論是一種哲學立場,認為每個事件都有條件,這些條件不能由任何其他手段引起。因此,技術決定論是指那些只有技術才能負責的事件和情況。
技術決定論假定一個社會的技術推動著其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觀的發展。據信該術語由美國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索斯泰因·維布倫(1857-1929)提出。20 世紀美國最激進的技術決定論者很可能是克萊倫斯·艾爾斯,他是索斯泰因·維布倫和約翰·杜威的追隨者。威廉·奧格本也以其激進的技術決定論而聞名。
隨著科學的適應,技術在一段時間內迅速發展。技術決定論者會爭辯說,技術的這種演變對現代文化產生了直接影響。
術語“技術”過去與寫作和印刷有關——如果追溯到數千年前,甚至與狩獵工具等有關——但現在它更多地與計算機和電視有關。
技術決定論者認為,這種技術演變塑造了社會的價值觀和規範,這些價值觀和規範代代相傳。
因此,隨著技術的進步,它對社會產生了直接影響。
總的來說,技術決定論是一種還原論理論,這意味著關於理論的類似哲學立場相互還原。該理論假定一個社會的技術驅動反映了該社會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觀。技術決定論理論提出了兩種主要的思維方式:技術的發展已經走上了一條超出文化影響的預定道路;其次,這些技術本身就會影響社會,即不受社會條件影響。它將技術視為所有人類活動的基礎。技術被視為歷史的驅動力,以及社會組織模式的基本條件。
從技術決定論的根源衍生出硬決定論和軟決定論。硬決定論認為技術發展獨立於社會問題,技術創造了一套強大的力量,作用於規範我們的社會活動及其意義。軟決定論是一種被動觀點,關於技術如何與社會政治狀況互動。技術是我們演化的指導力量,但我們也有機會對這種情況的結果做出決定。下面提到了許多適應和影響技術決定論的理論家。他們每個人對該理論的獨特立場非常有趣。
當然,索斯泰因·維布倫 的觀點導致其他理論家發展了技術決定論。他的觀點對卡爾·馬克思、馬歇爾·麥克盧漢、哈羅德·因尼斯、萊斯利·懷特 和 西格弗裡德·吉迪翁 等理論家產生了很大影響。
卡爾·馬克思
[edit | edit source]
對社會經濟發展進行 技術決定論 觀點的最早主要闡述來自德國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卡爾·馬克思,他的理論框架基於這樣一個觀點,即技術,特別是生產性技術的改變,是人類社會關係和組織結構的主要影響因素,社會關係和文化實踐最終圍繞著特定社會的技術和經濟基礎展開。馬克思的立場已經融入當代社會,人們普遍認為快速變化的技術正在改變人類的生活。儘管許多作者將人類歷史的技術決定論觀點歸因於馬克思的見解,但並非所有馬克思主義者都是技術決定論者,一些作者質疑馬克思本人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決定論者。
卡爾·馬克思堅信技術是社會各個方面的核心,因此它是社會秩序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馬克思相信資本主義社會,並將社會視為一種生產力——遵循生產方式。此外,他還注意到技術是一種生產力,他認為技術有助於組織社會。因此,技術將對文化和社會變革產生重大影響。
在眾多有影響力的理論家中,馬克思是第一個用社會經濟發展的觀點來闡述技術決定論的人。卡爾·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關係可以主要由技術發展來構建。
馬歇爾·麥克盧漢
[edit | edit source]
然而,還有其他理論家從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相信技術決定論——其中一位是馬歇爾·麥克盧漢(1911-1980)。麥克盧漢出生於加拿大,在多倫多大學任教。他在傳播學領域專門研究並具有重大影響力,該領域直接與技術相關。
哲學家麥克盧漢以他的“媒介即資訊”[14] 觀點而聞名,該觀點認為媒體影響著我們思考的方式。因此,技術將推動我們的思想、信念、價值觀和規範。因此,他的觀點是,技術將對塑造社會產生巨大影響,根據麥克盧漢的說法,現在的社會將由網路和連通性來定義。
麥克盧漢似乎認為“技術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自主的力量,它將帶來繁榮,併成為人類的救世主(Surry and Farquhar, 1997)。”[15]
此外,作為一位關於技術決定論的有影響力的理論家,麥克盧漢的研究還包括被稱為“人體延伸”、“地球村”[16] 和“冷熱媒體”的概念。

哈羅德·亞當斯·因尼斯 是一位 1894 年出生於加拿大的政治經濟學家,他影響了馬歇爾·麥克盧漢 的作品。因尼斯仍然是關於 傳播理論 的一個基本且著名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他探索了傳播的社會歷史,特別是在過去 4000 年媒體的影響方面。[17]
他關於傳播的著作,《帝國與傳播》 (1950) 考察了從古希臘和羅馬帝國時期到印刷術的改進的現代時期,石、陶土、紙莎草、羊皮紙和紙等媒體的影響。[18] 馬歇爾·麥克盧漢 指出,在他的另一部作品《傳播的偏見》(1951) 中,因尼斯發展了一種新的歷史觀。
- “大多數作家都在忙於提供關於哲學、科學、圖書館、帝國和宗教內容的敘述。相反,因尼斯邀請我們考慮這些結構在相互作用中所施加的權力形式。他將每一種組織化的權力形式都視為對複雜體系中其他組成部分施加某種力量。”[19]
因尼斯透過評估新媒體最初的開始方式來建立他的觀點。麥克盧漢承認因尼斯利用歷史上的技術事件來考察社會從中吸取了什麼,以及這對塑造文化有何幫助。因尼斯認為,社會的變化可以歸因於傳播媒介的進步,以及這些媒介如何推動權力關係的發展。[17]
萊斯利·懷特是一位 1900-1975 年在世的美國人類學家,他受到馬克思和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最出名的是他在“技術和科學發展方面的文化進化”方面的研究。[20]
他在 1934 年發表在美國人類學家的文章“能量與文化的進化”中提出了一個定律,即“能量”乘以“技術”等於“文化”。他提出的另一個定律是“在文化發展過程中,社會進化是技術進化的結果。”[21] 懷特認為,在人類發展初期,人類會利用自然資源作為能量,這將促進技術的發展,進而促進文化的進化。正如阿拉巴馬大學的埃利奧特·奈特和凱倫·史密斯所說
- “能量捕獲是透過文化的技術方面實現的,因此技術的改變可能反過來導致更多的能量捕獲或更有效的能量捕獲方法,從而改變文化。”[22]
懷特聲稱,文化是由人類適應其環境的技術手段決定的。文化對他們面臨的問題的反應方式以及他們在自然界中提供的解決方案決定了這種文化中的價值觀和行為。
西格弗裡德·基迪翁是一位瑞士歷史學家、建築評論家,重要的是一位非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是一位著名的世紀中葉的人文主義者,致力於打破科學、技術和行動之間的界限,作為一種與歷史互動的方式,將歷史視為“多重關係”的生動過程。基迪翁希望我們思考我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一切習以為常的物品。
他最著名的著作是《空間、時間與建築》 新傳統的發展。他的書旨在展示和探索現代藝術和建築的文化背景。透過他的書,我們看到了他希望彌合學科和文化界限的願望。基迪翁對技術有了新的願景,並希望恢復人與機器之間他所期望的平衡。透過他的書,我們能夠看到他的非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展現,但我們也看到他不僅適應了技術決定論的立場,而且重新定義了它。[23] 基迪翁希望我們思考我們為什麼以這種方式坐著和站立。他和上面提到的理論家一樣,對技術決定論的進步產生了重大影響。[24]
林恩·湯森德·懷特,小出生於 1887 年 4 月。他從 1933 年到 1937 年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中世紀曆史,後來在斯坦福大學任教幾年。[25] 他是歷史與技術學會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的許多大學講座都是基於他在 1962 年出版的一本書,名為“中世紀技術與社會變革”。這本書是引發有爭議理論辯論的導火索之一。懷特在他的書中解釋了他如何相信技術影響了社會變革;他專注於馬鐙,以及它如何有利於伊斯蘭教的發展。他還討論了與牛相比,馬在田間的使用變得更加方便,曲柄如何在需要的時候被髮明出來。如果沒有蒸汽火車和汽車,我們現在會怎麼樣?懷特的書評價很差,但從那時起,它仍然很有名,並且一直在被閱讀。
懷特從“中世紀技術與社會變革”中得出的信念引發了關於宗教如何影響西方人對自然界開發的態度的辯論。許多評論他作品的人認為,這直接攻擊了基督教,激怒了數百人。他的書獻給馬克·布洛赫。他一直堅信,技術發展是人類行為的主要因素,並且一直被忽視。懷特說:“如果歷史學家要嘗試寫人類歷史,而不是僅僅寫我們種族中那些有塗鴉習慣的小而專業部分所看到的人類歷史,他們必須對記錄採取新的看法,向它們提出新的問題,並利用考古學、肖像學和詞源學的所有資源來找到答案,因為在當代著作中找不到答案。”[26]
簡介
文化決定論是文化發展的一種普遍觀點,認為環境影響決定了個體的個人領域。其定義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但最終,該術語強調了一個人的行為如何受到技術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對社會的影響。文化決定論的定義由雷蒙德·威廉姆斯在他的著作《電視、技術與文化形式》中確定,儘管它已被許多不同的理論家定義。一些理論家認為文化決定論與文化悲觀主義相當,文化悲觀主義基於這樣的概念,即每種文化都是一個超級有機體,它有一個發展時期,然後就會消亡。與文化決定論的聯絡在於,我們不是文化的形成者,而只是其發展的物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是支援該理論的主要知識分子。
歷史與起源
正如本章中所述,文化決定論自19世紀上半葉就存在於知識界的討論中。它在費希特、歌德和馬克思等哲學家的著作和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費希特將決定論專門應用於自然;對他來說,人類存在的理由僅由絕對者在其自身自由實現中決定,因此人主要是一個可以塑造的物件,而馬克思和黑格爾則更進一步,將費希特的自然決定論應用於社會和歷史決定論,使人處於被動角色。
在《文化視野:文化史論文》[27]中,歷史學家恩斯特·貢布里希聲稱,受這些哲學家啟發的新的思維浪潮加強了文化統一的理由。他說;
可以說,如果文化條件的多樣性本身沒有導致文化史的出現,那麼對文化條件的多樣性的興趣就不會出現,如果沒有一個新元素——對進步的信念,而進步的信念本身就能統一人類的歷史。

變化
文化決定論在這些年中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浪漫主義時期之後,該術語的使用開始應用於社會中更具前瞻性的方面。在當今,它被用來應用於數字媒體以及技術的潛在未來。
文化決定論實際上創造了技術,技術是一種媒介來表達其資訊,昇華它們,並使它們令人放心。技術只是文化氛圍的反映,因此不應譴責技術,而應譴責文化。
透過雷蒙德·威廉姆斯和其他 20 世紀的理論家的工作,人們對文化決定論的興趣重新興起。文化決定論影響的有趣變化伴隨著對意識形態的影響。這種思維方式強調人們的行為,這句話“槍支不會殺人,人是殺人犯”是文化決定論在社會中的一個例子。透過文化決定論定義的變化,人們一直在爭論社會的影響還是技術的影響對人們的生活更具影響力。 “文化”本身的定義在這些年中一直在發展,這影響了人們對文化決定論定義的批評和讚揚。
新媒體
文化決定論是批判性閱讀新媒體的重要因素。正如技術決定論章節中所述,“新媒體”是一個非常模糊和廣泛的術語。憑藉我們今天擁有的技術,什麼是“新媒體”,什麼不是“新媒體”,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就文化決定論而言,新媒體很重要,因為它使文化能夠改變社會。我們掌握的豐富媒體是過去理論家無法預見到的。因此,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決定論定義可以被視為過時,它是一種不斷適應的意識形態。
哈羅德·伊尼斯將新媒體描述為一種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交流和理解的偉大交流改進;他將時間和空間維度新增到媒體中,將新媒體歸類為一種主要面向空間的交流形式,它不是面向跨越幾個世紀的資訊傳輸,正因為如此,伊尼斯對新媒體以及整個西方文明得出了一種非常悲觀的觀點。
再次,文化決定論與文化悲觀主義之間的類比又回來了。
理論家
文化決定論領域的領先理論家是雷蒙德·威廉姆斯。威廉姆斯於 1921 年出生於威爾士,對新左派的程序產生了影響:一個促進平等權利的政治運動。他屬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在當時的文化研究中影響很大。
與馬歇爾·麥克盧漢類似,威廉姆斯對新媒體著迷。然而,他們之間的關鍵區別在於,威廉姆斯更關注技術是如何在第一時間形成的,以及這對社會產生了何種影響。他非常批評麥克盧漢。雷蒙德·威廉姆斯對文化決定論的看法受到了馬克思主義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啟發。它基於這樣的概念,即文化是由時代精神決定的,它是一種基於生產的文化觀,它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化方法以及葛蘭西、馬爾庫塞和霸權的研究之上。對威廉姆斯來說,技術如果沒有我們創造它的人類的倫理和思想,就沒有意義。與麥克盧漢的觀點不同,媒介並非資訊,而是我們就是資訊,媒介只是載體。
約翰·哈特利是文化決定論的擁護者,但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他寫道;
“文化——話語的、媒體的、知識生產的和意義創造的生命領域——本身可能決定諸如階級、衝突和國家等問題。” [28]
簡介
首先,對技術決定論的簡要而一般的定義是,媒體技術如何影響特定社會中的人,包括他們的思想、感覺和行為,以及它如何影響不同技術時代之間的文化。這種影響從最初成為社會變革的重要因素的早期開始就一直在增長,然後這種影響傳播得更廣,對各行各業的人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種進步在定義中帶來了變化,新的媒體形式(如電視)被引入,並且存在不同的決定論水平,例如軟決定論和硬決定論:新媒體的定義難以確定,因為它是一個非常廣泛的術語。該理論本質上假定社會的技術推動了其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觀的發展。麥克盧漢等理論家反對威廉姆斯,因為他的信念與硬決定論一致。
歷史與起源
正如本章中更詳細地討論的那樣,可以簡要地從技術決定論的定義角度來回顧歷史。技術決定論一詞最初被認為是由美國社會學家索斯泰因·維布倫提出的,在這個工業革命時期,技術決定論的定義來自圍繞技術的思想,技術是重要的管理特徵。當時的想法是,技術進步對社會的影響比大多數其他問題更大,因此它對整個社會變革做出了重大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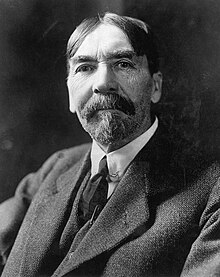
儘管技術決定論正在成為大多數工業文化中核心理想的一部分,但顯而易見的是批評聲隨之而來,並影響了其他人對這種觀點的看法。這種早期的批評來自於人們的思想,認為這些社會自動化和縮減勞動力會導致人類失去控制和決策的能力。像亨利·亞當斯這樣的批評家將這種技術決定論的想法視為消除了社會過去的傳統價值觀,並改變了人們體驗世界的方式。 [29]
到 20 世紀初,人們在流行文化中更廣泛地討論新技術,因此技術決定論的思想及其在社會中的定義變得越來越普遍,因為更多的人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這種新技術。 [30] 當時許多文章和書籍都包含了這些想法,並圍繞這種技術決定論的概念提出了許多定義。隨著 20 世紀的繼續,技術決定論的思想繼續透過廣告的形式不斷增長:這意味著技術影響社會的這些想法現在對接觸任何形式媒體的大多數人來說都清晰而生動。
變化
技術決定論定義中的一個主要衝突是“軟決定論”和“硬決定論”之間的差異。硬決定論的定義是技術完全獨立於所有社會問題,因此技術進步管理著我們的文化行為,並限制了我們影響這種行為的自由。相反,軟決定論被定義為仍然將技術視為社會變革的主要驅動力,但認為我們最終確實擁有影響潛在結果的控制權。導致技術決定論定義中存在差異的另一些要點是圍繞相關技術的思考和衝突,例如必須匿名才能使其與技術決定論的概念完全相關,或者是否存在比匿名性更重要的因素需要考慮。 [31]
從 19 世紀到 20 世紀的作家對技術決定論持批評態度的理論家及其觀點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可以注意到,仍然有一些人堅持批判這種觀點,但關注的重點從風俗習慣和信念轉變為政策和控制。
電視的出現及其融入人們的生活對於重新定義技術決定論意義重大。電視可以被看作一種老媒體形式,它本身在這些新媒體時代不斷適應,從增加新頻道到智慧電視。[32] 對定義的這種改變可以看作是電視帶來了對技術如何透過移動影像和聲音影響社會的新理解,這些影像和聲音共同傳遞了人們有意識或無意識接受的想法。
新媒體
術語“新媒體”指的是在過去十年中獲得了廣泛普及的一系列不同的流程和實踐。它既是一個極其模糊和寬泛的術語,又可以被認為是一個非常確定和明確的術語,因為它暗示著“新媒體”現在已經完全實現為物質和社會實踐。然而,這種說法並不正確:人們通常使用這個詞來描述完全不同的東西。許多人將“新媒體”定義為透過網際網路按需提供的內容,或透過包含互動式使用者反饋和創意參與的數字和移動裝置訪問的內容——比如社交媒體或線上新聞、部落格、維基和影片遊戲等網站的全球現象。因此,“新媒體”本身沒有明確的定義,而是一個更常用來對所有這些不同的互動式社會實踐、創意參與和內容創作進行分類的術語,當然它還沒有完全實現為物質,因為它每天都在不斷發展和演變,以及我們作為一個社會集體使用或消費它的方式。
首先,如今當有人在談話中提到“新媒體”時,通常指的是傳播媒體,以及提到人們工作的機構和組織,例如媒體、電影、廣播等,以及這些機構的物質產品,例如電影、書籍、光碟等。然而,這個寬泛術語的含義也指的是技術變革的強度: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技術發展突飛猛進。儘管技術進步始終在不斷變化中,但這段時期透過印刷術、攝影術到電視、再到電信的發展,標誌著之前的時代。新媒體的一個關鍵點是它徹底改變了主體(使用者和消費者)與媒體技術之間的關係,改變了影像和傳播媒體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和接受方式,以及賦予媒體技術中的意義。
透過網路通訊連線個人電腦是所有興奮、批判性關注和商業投資的根本原因:全球資訊網軟體的發明真正發展了網際網路,反過來,網際網路的增長成為了“技術想象”的主要投資場所,在精神分析的背景下,指的是人類在他們支離破碎和不完整的自我中渴望成為的影像、表徵、思想和實現、整體和完整感的直覺領域。[33] 也許這就是我們人類如此關注它的原因。
理論家
關於技術決定論,該領域的領先理論家是馬歇爾·麥克盧漢,他認為媒介即資訊。這本質上意味著圍繞一種媒介(我們自身的延伸)的社會和個人問題以及後果,是由於這種新媒介或任何現在已成為我們生活一部分的新技術造成的。他使用了電燈的類比:電燈是純粹資訊和媒介的來源,沒有資訊,除非它被用來拼出特定的廣告或名稱。根據馬歇爾·麥克盧漢的觀點,這個想法本身是所有媒體的基礎:任何媒介的內容始終是另一種媒介。例如,寫作的內容是語言,書面文字的內容是印刷。麥克盧漢的觀點與威廉斯的觀點不同,因為他相信硬決定論:電燈或燈泡不像書有章節,不像電視有節目那樣有內容,但它是一種對社會有影響的媒介,因為它讓人們在黑暗中也能看到,為他們打開了原本封閉的環境。[34]
主要概念
[edit | edit source]技術決定論
[edit | edit source]媒體中的技術決定論是一種哲學和社會學概念,認為媒體的力量和技術對塑造社會具有影響。本章節將探討與技術決定論相關的一些關鍵概念。其中包括對關鍵理論家和理論例子的考察,這些例子將使媒體領域內技術決定論的概念更容易理解。
關鍵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
[edit | edit source]加拿大知識分子馬歇爾·麥克盧漢是技術決定論理論的主要倡導者。他非常贊成我們受到技術進步控制,而技術進步又影響著我們的文化。在他那個時代,他的想法似乎激進而有爭議,但儘管如此,他仍然很有影響力——不僅在學者中,而且在更廣泛的公眾中。他的主要思想在他的主要著作中有所探討——《古騰堡星系》[35](1962年)、《理解媒介:人的延伸》[36](1964年)和《媒介即資訊》[37](1967年)。

讓麥克盧漢的思想如此引人注目的是,儘管麥克盧漢於1980年去世,但在計算機和網際網路出現之前,它們似乎準確地預測了技術的未來。麥克盧漢最重大的三個論點,在下面將詳細討論,分別是
- 任何媒介的內容始終是另一種媒介的想法
- 媒介和技術是人體的延伸的想法
- “媒介即資訊”的想法
麥克盧漢還將技術發展看作從口頭交流到書面交流的四個發展階段的轉變
- 原始的口頭文化
- 識字文化
- 印刷文化
- 電子文化
這表明技術始終推動著人類前進,如今,我們仍然處於技術進步的發展階段。由於技術,世界似乎比以前“更小”,因為我們現在更加互聯。
麥克盧漢認為,技術不能簡化為其社會用途——重要的是技術本身。在對這些概念的討論中,一個清晰的主題始終存在——麥克盧漢堅持認為,這種技術的影響力能夠影響我們與他人和世界之間的關係,以及我們如何對待他們。儘管這些想法已經存在了幾十年,但它們仍然對當今學者的思考方式具有很大影響——現代人對計算機和智慧手機等技術的依賴,以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與技術的互聯性,他的理論似乎確實具有很大的相關性。
理論示例
[edit | edit source]技術決定論發揮作用的一個恰當例子是麥克盧漢在他具有開創性的著作《古騰堡星系》中給出的例子。這將1452年約翰內斯·古騰堡發明印刷機視為人類歷史上的一個特定轉折點。[38]

麥克盧漢認為,印刷機以簡單社會變革無法實現的方式徹底改變了社會,並透過允許個人之間快速通訊來改變了社會及其中的個人。用本章之前提出的一些思想來說,印刷機在從識字文化向印刷文化的過渡中發揮了作用。
印刷術的發明促使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發生了社會和經濟轉型。印刷書籍所需的時間和精力遠遠少於之前的抄寫手稿方法。除了製造速度更快之外,由於生產成品所需的工作量減少,這種工藝的成本也更低。除了經濟問題之外,印刷機可以快速製作多種材料副本,並將其分發到更廣泛的區域,而手稿的釋出範圍有限,主要透過口頭傳播。這種新發現的將書籍分發到更廣泛區域的能力,使新的思想和概念得以紮根,並促進了社會發展和變革。以該時期的一個例子來說,印刷機的速度和成本促成了馬丁·路德在 1517 年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39] 如果沒有廣泛傳播翻譯後的宗教文字,例如路德聖經,這場改革運動就不會如此成功,它促使歐洲人民的識字率大幅提升。[40] 麥克盧漢認為,由於歐洲人口識字率的提高,由此產生的思想的擴充套件和表達為現代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概念(例如民族主義)的出現提供了根基。民族主義
技術延伸了人的身體
[edit | edit source]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論的主要前提是,媒體通常會改變人類與世界互動的方式,任何一種特定媒介的具體特徵都會改變這種感官關係,重點在於媒介特徵的重要性,而不僅僅是透過媒介提供的內容。因此,它特別強調技術勝過文化。
麥克盧漢關於技術決定論的理論認為,媒介是“我們自身的延伸”。[41] 他認為,字母表延伸了眼睛,車輪延伸了腳,而電腦延伸了神經系統。因此,在他看來,這些延伸了人體的東西都是媒介,尤其是在他寫這些東西的時候,計算機還不像現在這樣普遍。他還斷言,這些延伸了我們身體的東西改變了身體感官部分之間的自然關係,並影響了我們的思想和社會,因為它們改變了人類感官範圍之間的比例,這對我們的心理功能有影響。
根據麥克盧漢的理論,語言是一種媒介,因為它是我們內在意識的延伸。因此,口語是人類意識和文化進化中的一個關鍵發展,也是後續技術延伸演化的媒介。這在當今仍然適用,因為語言不斷發展,導致技術不得不隨之發展,例如“自拍”一詞被新增到牛津英語詞典中,更多帶有前置攝像頭的手機被髮布,以適應這種現象。
然而,他的論點也受到了一些批評,因為有些人認為“媒介”一詞過於簡單,因為它將渠道、程式碼和資訊都囊括在這一術語之下,從而在他的框架中混淆了載體、內部程式碼和資訊的內容。麥克盧漢也被貼上了技術恐懼症的標籤,並因他對意識的電子延伸表現出明顯矛盾而受到批評,儘管事實上他更感興趣的是探討技術作為人體延伸的意義,而不是將其貼上好壞標籤。
媒介即資訊
[edit | edit source]該理論首次發表時,標題打錯了,是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麥克盧漢認為,這是一個更好的標題,因為它可以從四個不同的角度解讀:message、mess age、massage 和 mass age。[42]
在他出版的《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書中,麥克盧漢探討了媒介即資訊的理念。該理念的主要觀點是,無論“內容”如何,媒介都會決定對人類社會帶來的任何變化。麥克盧漢用來論證這一理論的關鍵例子之一是電和光。根據該理論,燈泡是一種媒介,因為它本身不包含任何“內容”,但它確實控制著內容。例如,如果沒有光,許多活動在太陽落下後就會受到阻礙,因此媒介決定了活動。麥克盧漢還認為,正是電影這種媒介“將我們帶入了順序和聯絡的世界,進入創造性配置和結構的世界”,這得益於線性連線。[43]
透過電影作為媒介的理念,立體主義應運而生,它試圖透過使用平面以及模式、燈光和紋理的模糊性來決定觀眾的視角。用更簡單的說法,它將所有不同的部分整合起來,創造出一個整體,觀眾將其視為最終的產物,例如,他們看到的不是立方體的不同側面,而是立方體本身。因此,由於立體主義不是關於“內容”,它成為了麥克盧漢對這一主題的思想的一個很好的例子。[43]
熱媒介和冷媒介
[edit | edit source]理解技術決定論的關鍵概念之一是馬歇爾·麥克盧漢對“熱媒介”和“冷媒介”概念的使用。這與他著名的短語“媒介即資訊”相呼應,麥克盧漢根據觀眾的參與度對不同的媒介進行排名。這一理論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受到了批評,但儘管如此,它仍然被認為是麥克盧漢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4] 對這一主題的研究非常稀少,這些實證探索取得的結果模稜兩可。[44]
- 熱媒介
熱媒介為聽眾或觀眾提供了大量資料,並與他們互動,讓他們在無需進一步解讀所呈現的文字的情況下就能產生情緒反應。[44] 觀眾無需填補任何空白,因為文字中提供了所有與首選解讀相關的資訊。廣播、報紙和電影可以被視為熱媒介平臺,因為它們以這種方式與觀眾互動。[45] 麥克盧漢在談論熱媒介時使用“高畫質晰度”一詞——他的意思是,熱媒介提供的資料足以增強一種感官,例如攝影在視覺上提供了大量刺激,因此被認為是高畫質晰度。[46] 熱媒介限制了觀眾參與的程度,因為所有資料都直接提供。
- 冷媒介
另一方面,冷媒介要求觀眾進行觀察,並填補似乎缺失的資訊。[44] 冷媒介文字提供了模糊的資訊,它們要求觀眾積極參與,以弄清文字的含義。電視和電話屬於冷媒介。[45] 為了將冷媒介與熱媒介區分開來,麥克盧漢指出,冷媒介與熱媒介不同,它是“低清晰度”。[46] 電話上的對話提供了很少的資訊,留下了許多空白讓參與者去填補,因此它是“低清晰度”。冷媒介讓觀眾能夠更加自由地參與。
案例研究:技術視角
[edit | edit source]為了更好地理解技術決定論思想的應用,進行一個案例研究可能是一次有意義的嘗試,這個案例研究將在本章後面從不同的角度重複進行。在這個具體的案例研究中,網際網路將成為討論的重點,並將從純粹的技術角度進行探討。
網際網路的發明使社會開始受益於各種形式的資訊獲取的增多。與印刷術對社會的影響類似,這種隨後的知識可以更好地告知社會中的個人,或者 - 如果遵循馬歇爾·麥克盧漢提出的論點 - 改變他們對整個世界的體驗。網際網路催生了隨後影響深遠的技術,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智慧手機。回顧麥克盧漢在本章開頭提出的論點,作為技術存在的計算機可以說是一種人類神經系統的延伸。網際網路的建立,作為將每個人連線到一個全球網路的方式,繼續放大了這種影響,帶來了與技術的新感官關係,從而幾乎完善了技術作為人體延伸的概念。社交媒體網路現在在社會中司空見慣,並且它們本身改變了人們相互交流和體驗媒體的方式。
結論
[edit | edit source]在技術決定論中,麥克盧漢贊成技術進步引領和影響文化的觀點。正如本章關於技術決定論主要概念的部分所論證的那樣,技術決定了文化發展。麥克盧漢為他的觀點提供了幾個論點,這些論點已經被探討過,例如技術作為身體的延伸、冷熱媒體以及媒介即資訊。技術如何決定文化發展的例子是約翰內斯·古騰堡的印刷機,這是一種使大規模出版成為可能並導致識字率提高的機器,正如麥克盧漢所說。
文化決定論
[edit | edit source]文化決定論反對技術決定論,聲稱一種有生活經驗的文化會影響人們及其行為,因此也影響了技術的發展。與數字媒體有關的是,文化決定論處理了一種觀點,即沒有一種使用特定技術的既定方式,而是個人在他們自己的文化中找到使用它們的方法。本章的這一部分將回顧文化決定論的主要概念,包括一位關鍵理論家和一些理論例子,在一個能讓概念看起來更切實的語境中,並將文化決定論帶入媒體領域。
關鍵理論家 - 雷蒙德·威廉姆斯
[edit | edit source]一位為文化決定論辯護的理論家是威爾士學者雷蒙德·威廉姆斯。威廉姆斯是英國媒體和文化研究的傑出人物,他的觀點在學術界比麥克盧漢有爭議的觀點更廣泛地被接受。威廉姆斯是麥克盧漢的對立面,他強烈反對麥克盧漢的觀點,堅持認為技術隻影響已經存在的結構,並強化權力關係。他認為麥克盧漢片面地認為技術是改變文化的責任。威廉姆斯的理論,下面將更詳細地討論,探討了

- 技術發展的原因
- 塑造技術的一系列社會、文化和經濟因素
- 技術被用於特定目的的方式
這些觀點在他的書電視:技術與文化形式[47] (1974) 中有所闡述。威廉姆斯聲稱,技術的興起源於人類自身的視角——他們的需求、結構和雄心比技術對我們的影響更大。因此,技術的增長受強大的個人行為者影響,而不是技術本身。他將技術視為人類用來解決問題的工具。這意味著技術有多種用途和結果——由於許多不同型別的人利用了技術的益處,他們永遠不會只有一種用途。
與麥克盧漢不同,威廉姆斯認為媒體的內容很重要——技術的功用不能與其本身分開。因此,技術是由人類及其現有的信念賦予意義的——是我們的技術使用,而不是技術對我們的使用,影響了文化以及我們如何行事。
理論示例
[edit | edit source]在他的書電視、技術和文化形式中,雷蒙德·威廉姆斯將電視列舉為一項最終是社會、經濟和文化因素的產物,而不是純粹的技術產物。威廉姆斯認為,電視是利用各種先前存在的技術——即電力、電報、攝影和無線電——的結果,而這些技術本身都是為了截然不同的目的而發明的。最終,根據威廉姆斯的說法:“這些生產和通訊中的流動性和傳輸系統,無論是在機械和電力交通方面,還是在電報、攝影、電影、無線電和電視方面,都是一個總的社會轉型階段的動力和回應。”[48]
威廉姆斯認為,上述技術都是為了滿足社會需求而產生的:發明是為了應對工業化世界最初的難題,而工業化世界本身則提供了對哪些技術被認為是可能的新的可能性。例如,電報作為一種通訊媒介是“鐵路發展的結果,鐵路本身是對工業體系發展以及相關城市增長的回應。”[49] 與其前身一樣,電視最終是對各種社會問題的回應。如前所述,印刷機的發明允許將新思想傳播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從而導致了進一步的技術進步。這些新技術是故意設計用來傳播新資訊和意識形態的,這些資訊和意識形態主要是我們今天所認識的現代大眾媒體的形式:廣播、報紙以及最終的電視。
社會群體
[edit | edit source]早在 1945 年,瓦內瓦爾·布什 就預見到了計算機將促進資訊連線,以適應每個使用者的需求。[50] 由於雷蒙德·威廉姆斯 的工作,這種定製軟體以滿足人們的個性化需求的能力已完全實現。

人類意圖和特定社會群體的需求導致了技術出現和推動現有社會實踐的具體條件。威廉姆斯指出,技術發展有幾種可能性和結果,因此幾個不同的社會群體可以將技術的預期用途據為己有、改編、修改或顛覆,以滿足他們自己的需求。例如,在 2011 年夏季席捲英國各城市的騷亂 中,社交媒體被廣泛認為加劇了局勢。觀看人們“隨意搶劫”[51] 煽動了混亂,因為它將人們聚集在一起,並允許暴徒組織騷亂。不僅如此,社交媒體也被用來美化他們的行為,例如,一名男子偷竊一袋樂購經濟型大米的圖片在網上瘋傳。
不同的社交媒體顯然服務於不同的目的,推特 140 個字元的限制使其區別於臉書,因為推特只應該提供對個人觀點的簡短瞥見,而臉書在資訊方面更加多面——從相簿到你的工作經歷。因此,不同的社會群體可能會更傾向於使用不同的社交媒體,具體取決於他們希望其服務的目的。許多老年人傾向於使用臉書,因為它允許他們透過校友群組等與老朋友重新建立聯絡,而推特可能無法以相同的方式滿足這種需求,特別是考慮到識別某些人可能更加困難,具體取決於他們的推特使用者名稱是什麼。因此,社交媒體平臺可能通常存在於服務於相同的目的(娛樂、自我表達等),但它們在截然不同的環境中服務於這些需求,而且往往以與最初設計用途不同的方式使用。
案例研究:文化視角
[edit | edit source]正如本章前面提到的,案例研究將是比較不同思想流派的方法。在關於技術決定論的部分,從該特定角度討論了網際網路。在這裡,將從文化決定論的角度來看待它。
為了網際網路作為一項技術被髮明,社會必須根據文化決定論的概念,要求其發展。連線的概念並不新鮮,而且它也沒有以網際網路的形式實現:甚至自亞歷山大·格雷厄姆·貝爾發明電話以來,技術就被引入以改善當代社會的生活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是為了在一個城市、工業和海外帝國野心迅速擴張的世界中促進一種更快的長途通訊方式。在更現代的意義上,表明推動網際網路誕生的社會因素的證據包括計算機技術在消費和專業模型中越來越多的可用性,以及對改進現有通訊方法的渴望。此外,創造網際網路最早形式的最初研究 - ARPANET - 是美國國防部高階研究計劃局(或 DARPA)調查可能的技術的直接結果,這些技術能夠在電話系統遭受外國攻擊的情況下實現緊急通訊。[52]
結論
[edit | edit source]在文化決定論中,技術的使用和利用方式與它所處的社會和文化息息相關。如上所示,技術並不決定周圍的人,而是技術進步服務於人和文化,並滿足他們的需求。人們有能力提出替代用途,並同時將同一個平臺用於多種用途。一個常見的例子是 Twitter,一個媒體平臺,可以用來與朋友保持聯絡、閱讀新聞、參與線上行動主義和推廣產品,僅舉幾個例子。
反對
[edit | edit source]多年來,技術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都遇到了許多理論家的反對或反對。本節將涵蓋一些對每種理論持不同意見的更著名的理論家,以及他們的個人論點和衝突觀點。
反對技術決定論的論點
[edit | edit source]許多反對技術決定論的理論家反而支援文化決定論,認為技術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是交織在一起的,或者提出他們自己關於技術在社會中的地位和發展的替代理論。許多圍繞技術和/或社會展開研究領域的教授和學者都對技術決定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雖然有些人同意並認可該理論,但其他人則用自己的觀點和想法反駁和反對它。
莉莉婭·格林
[edit | edit source]珀斯伊迪絲·科萬大學高階講師,莉莉婭·格林認為,技術決定論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它違背了整個社會是 有偏見的觀念。在她看來,為了讓技術決定論起作用,它將需要社會具有中立的性質,而不是像現實中那樣擁有偏見。 [53]
格林對技術決定論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反對意見之一是他們聲稱的思維方式 "'你無法阻止進步','你無法倒退' 和 '技術失控的巨輪'",據格林說,“所有這些都暗示著我們無法控制技術”。 [53] 格林堅信,人類——因此是社會——控制著他們開發的技術,而不是技術發展社會。
朗頓·溫納
[edit | edit source]
朗頓·溫納是一位以其關於技術和社會的著作而聞名的教授;他提出了一個與技術決定論相矛盾的觀點。在他的其中一篇名為《技術作為生活方式》的論文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技術夢遊理論——這個理論表明,作為一種物種,我們在面對技術時處於“夢遊”狀態,由於我們對如何與技術互動漠不關心,因此我們對技術發展的方向幾乎沒有控制權。他繼續闡述
技術帶來的大多數日常生活內容變化都可以被認為是早期模式的版本。父母總是不得不逗樂和指導孩子,並想辦法讓孩子們不要打擾他們。讓孩子們看幾個小時的電視卡通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只是處理這個古老任務的一種新方法,儘管“僅僅”並不無意義。 [54]
根據溫納的技術夢遊理論,這種“夢遊”狀態的原因之一是社會看待技術的方式;作為可以隨時放下和拿起的使用物件,因此我們不理解使用這些“物件”的長期影響(“確實,生活中反覆出現的活動模式(無論其起源如何)往往成為理所當然的無意識過程”)。[54] 在他的論文中,他還指出另一個促成因素是技術製造者和使用者之間的距離關係——這會導致人們對利用和開發這些技術的潛在後果缺乏意識或探索。溫納提出的關於這種現象發生的最後一個想法是,技術在我們周圍創造了一個不同的世界,而這個新世界是透過改變我們周圍的世界和物體的結構而創造的。
布萊恩·溫斯頓
[edit | edit source]媒體研究理論家 布萊恩·溫斯頓在其著作《誤解媒體》中提出了一個名為激進潛力壓制法則的概念。這個想法表明,基於通訊的技術發展受到現有制度和機制的影響而受到抑制。[55] 這一理論與技術決定論直接衝突,反而認為社會是控制和塑造新興技術的力量。溫斯頓說,雖然文化和社會需求是特定技術需求背後的驅動力,但激進潛力壓制法則阻止了相關技術對社會造成巨大破壞,反而使其成為最低程度問題的現狀。
在他另一本書《媒體、技術與社會:一部歷史——從電報到網際網路》中,他爭辯道
電力和電子通訊系統歷史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重大變革沒有得到既有社會形態的適應......這些不同的技術以及它們發展和傳播的兩個世紀中可以觀察到重複出現。 [56]
此外,在他的論文《媒體是如何誕生和發展的?》中,溫斯頓反對技術決定論,而是指出文化決定論是當今社會與技術關係中起主導作用的理論。[57]
| 安德魯·芬伯格 | |
|---|---|
 費恩伯格在加拿大溫哥華,2010年 | |
| 出生 | 1943年9月14日 |
| 職業 | 哲學家和作家 |
| 配偶 | 安妮-瑪麗·費恩伯格 |
安德魯·費恩伯格(73歲)是一位來自溫哥華的哲學家,在西蒙弗雷澤大學傳播學院擔任加拿大技術哲學研究主席。他以反對技術決定論的哲學而聞名。民主理性化是費恩伯格在其文章“顛覆性理性化:技術、權力與民主與技術”中使用的術語。“民主理性化挑戰了技術設計中根深蒂固的有害後果、非民主權力結構和溝通障礙。”(安德魯·費恩伯格)他認為技術決定論不是一個有根據的概念,他透過拆解決定論者理論的兩個支柱來證明這一點。他所確定的兩種理論是:
單線進步論點,即認為技術的發展在複雜性方面是可以預測的,並且每個階段都是任何進步都必須經歷的必要階段。
基礎決定論點,即任何新技術的出現都會導致社會發生改變,並重新組織自身以適應該技術。
費恩伯格認為,技術是社會演變的一個因素,但不是一個驅動因素。“限定因素在於技術的役割,我認為它既不是決定性的,也不是中立的。我將論證,現代形式的霸權是建立在技術媒介對各種社會活動(無論是生產還是醫學、教育還是軍事)的介入基礎上的,因此,我們社會的民主化需要激進的技術和政治變革。”
費恩伯格所有關於技術及其對我們社會的相關性的書籍,其中他闡述了自己的論點:
盧卡奇、馬克思與批判理論的源泉(羅曼與利特菲爾德,1981年;牛津大學出版社,1986年)
技術批判理論(牛津大學出版社,1991年),後來重新出版為轉型技術(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
另類現代性(加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
質疑技術(勞特利奇,1999年)。
轉型技術:批判理論再探(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
理性與經驗之間:技術與現代性論文集(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2010年)。
顛覆性理性化:技術、權力與民主與技術
安德魯·馬菲(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媒體與傳播高階講師)和約翰·波茨(來自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是2002年11月25日出版的《文化與技術》一書的作者。波茨和馬菲認為,社會的變化不僅僅是技術決定論造成的,文化決定論也塑造著社會。正是這兩者的結合才推動了我們的前進。在《文化與技術》一書中寫道:
“技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不能簡化為簡單的因果關係公式。相反,它是一種‘交織’,技術不會決定,而是‘在一個複雜的社會領域中運作,並受到其影響’。”(馬菲和波茨)
馬菲和波茨(2003年)描述了技術發展是進步,並將技術描述為“獨立因素”,具有其自身的“屬性”,他們還表示,技術發展是“脫離社會壓力,遵循其自身的邏輯或必然性”。
“這些技術的進步增強了連線性,進而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同質化。它們逐漸建立了新的數字社會,沒有遇到“阻力”——例如,手機最初只提供口頭和文字交流,如今它提供即時影片聊天、網際網路連線、照片交流等等,所有這些都在沒有“阻力”的情況下展開。”馬菲和波茨,2003年
文化決定論是一個有爭議的論點,許多關鍵理論家反對它,認為它在決定社會如何與媒體互動方面是最重要的。他們認為,不是文化影響技術進步,而是技術決定了人們將如何與媒體互動。許多反對這些理論的學者並沒有完全反對文化決定論,而是認為技術決定論在社會文化進步中具有更大的應用,而不是相反。這些理論家包括馬歇爾·麥克盧漢、尼爾·波茲曼、布魯斯·比姆伯和 R.L. 赫爾布魯納。
馬歇爾·麥克盧漢是一位加拿大教授,他關於數字媒體的研究在幫助論證文化決定論在社會變革中重要性較低方面仍然具有現實意義。麥克盧漢反對文化決定論的主要論點概括在他所著的《理解媒介》一書中。
“有時,讓人想起一個事實會讓人震驚,那就是在運作和實踐中,媒介即資訊。這僅僅是說,任何媒介(即我們自身任何擴充套件)的個人和社會後果,都來自我們自身每一種擴充套件(或任何新技術)引入我們事務中的新尺度。”[58]
這突出了麥克盧漢堅定地認為技術在社會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而不是文化決定論是最重要的因素。這是因為他認為,如果沒有媒介本身,社會將無法從媒介中獲取想要的東西,並將其適應以滿足文化需求。
波茲曼認為,當一項技術被髮明時,它可能存在與發明目的不一致的固有用途。他舉例說明道:
“一旦一項技術被接受,它就會發揮作用;它會做它被設計要做的。我們的任務是理解這種設計是什麼——也就是說,當我們將一項新技術引入文化時,我們必須睜大眼睛。”[59]
波茲曼提請注意,一項技術往往能夠被應用於遠遠超出其最初用途的範圍,正是這種應用推動了技術的發展。他認為,社會隨後可以考慮這種技術,並從現有的想法中衍生出其他用途,這些用途將與其激勵的技術相關聯,但同時又完全不同。他不是為技術建立特定的需求,而是認為技術本身就具有透過複合舊技術來改進自身的能力。因此,在這個過程結束時,技術可以得到改進,創造出越來越廣泛的可能性。
布魯斯·比姆伯是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政治學系的教授。他對技術決定論影響社會的重要性持強烈的觀點。因此,比姆伯不認為文化決定論是社會內部變化日益加快的主要原因。
在他發表的《技術決定論的三方面》一文中,他論證道:
''“技術發展在決定社會結果方面發揮著超乎人類控制的役割。”[60]
比姆伯認為,並非文化決定了社會的進步,而是技術具有獨特的能力,可以在社會意識到變化發生之前改變社會。他認為,技術決定論有三種變體:規範性、自然法則和意外後果論點。儘管有所不同,但這些版本都支援這樣的觀點,即文化決定論並非影響我們社會發生變化的最重要因素。
赫爾布魯納在其著作《機器創造歷史嗎?》中提出,技術進步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按照某種必要的順序進行的。他認為:
“在進入蒸汽磨時代之前,不可能進入手磨時代,反過來,在掌握蒸汽磨之前,不可能進入水力發電廠時代,在經歷電力時代之前,也不可能進入核能時代。”[61]
赫爾布魯納提出,對於文化來說,經歷技術進步的先前階段至關重要,也許更重要的是,在社會能夠繼續發展相關實踐之前,必須在應用這些進步方面達到精通。他認為,要實現技術進步,必須獲得大量廣泛的知識,這使得任何進步都依賴於現有的技術,而不是社會認為需要發明的技術。因此,原始技術的發展方向將與新型技術的發展方向相似,並且必須存在,新技術才能被創造出來。由此可見,赫爾布魯納的立場被證明是更加重視技術決定論的,儘管他謹慎地承認,在爭論的雙方都存在著許多獨立的因素在起作用。
單一的決定論無法完全解釋與人性和文化和技術相關的有影響力和不可分割的關係。一些論點甚至表明社會和文化決定論的思想結合。在現代技術與社會以及相關領域的理論研究早期,他們傾向於否認決定論者對人與技術之間關係的絕對看法。一群人更傾向於相對溫和的立場,這與 Murphie 和 Potts 提出的觀點較為接近,即“技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不能簡化為簡單的因果關係公式。相反,它是一種‘相互交織’的關係”,技術並非決定,而是“...在複雜社會領域中運作,並受到運作”。[62] 這與當今人們對技術與人類社會之間關係的認識相一致。
據亨特學院生物心理學家 Nigel Barber (2008) 說,[63] 社會科學的主流理論是文化決定論。然而,他說,作為科學理論,它缺乏可信度,而且往往無法檢驗。當被檢驗時,它經常失敗。這些失敗被廣泛忽略,因為社會科學家無法構想出可行的替代方案。因此,文化決定論的未來似乎是不確定的,其有效性已受到廣泛討論。加州大學名譽教授 Donald Brown (1991) [64] 指出,在所有已知的人類社會中,個人都努力獲得聲望和地位,存在社會等級制度、婚姻、嫉妒、按性別分工和性禁忌;男性比女性更具攻擊性,更有可能成為暴力犯罪者。觀察到道德情感、嫉妒、羞恥和自豪。人們相信超自然力量,相信運氣和命運,並普遍存在對死亡的恐懼。人們知道借代、比喻、諺語、音樂和藝術,以及基本的抽象概念和邏輯和數學概念。貪婪被忽視,而謀殺和強姦則受到嚴厲譴責。
神經科學家、遺傳學家、語言學家和進化生物學家進行的研究駁斥了文化決定論,並證實了 Brown 和社會生物學家的研究結果,他們認為存在著由基因與環境相互作用所引導的人性。 [65]
民族國家的模式意味著其人口構成一個民族,他們有著共同的血統、共同的語言和許多共同的文化形式。人們經常談論文化決定論,它假設個人的現實、行為和過程是由其所屬的文化決定的(對於移民來說,是其原籍文化)。有些人認為,這類理論不過是經典種族主義理論方法的演變,他們想用文化取代種族的概念。在隱含的統一性缺失的地方,民族國家經常試圖創造它,透過教育推廣統一的民族語言。
然而,McNeill (1986) 指出,這種基於種族同質性的民族統一模式只在 1750 年至 1920 年間的歐洲盛行。他還指出,納粹政權在德國的經歷使融入當地主流民族群體的理想失去了信譽。他還認為,民族統一理想的破壞也導致了民族少數群體對身份的重新主張,因為追求統一需要抹除區分性的文化差異。 [66]
關於民族構成變化對一個民族可能產生的文化影響,福山 (2007) 警告說,“相對主義的興起使得後現代人更難以宣揚積極價值觀,因此也使得他們對移民作為公民身份條件所要求的共同信仰更加難以接受”。[67] 因此,似乎當今在後現代國家,融入並不困難。
事實上,Vasta (2009) 指出,缺乏“強大、有目的和鼓舞人心”的國家認同,使得融入民族文化的益處對於移民和少數民族群體來說不那麼明顯。她認為,加拿大融合模式,即重視對多樣化的種族/文化/宗教身份及其對國家認同的象徵意義的包容,是更有希望的做法。 [68]
Modood (2007) 也認為,鼓勵強大的多元文化或少數民族認同和弱勢的共同或民族認同毫無意義。在他看來,維護社群傳統必須在一個強大的民族儀式和傳統框架內進行,這些儀式和傳統展示了少數民族社群對整體民族認同的貢獻。 [69]
因此,不同的文化可以在自己的傳統中共存。另一個應該考慮的方面是,從中期來看,不斷增長的種族多樣性對社群凝聚力的影響可能取決於經濟狀況。種族多樣性對社群凝聚力的影響是透過經濟繁榮來調節的。如果經濟復甦,少數民族和移民背景的人將有更多機會取得經濟成功。他們可能更有能力融入社會,並可以選擇搬到更繁榮的地區和位置,在那裡他們不會與種族鄰里直接競爭資源。如果大多數人口也有機會找到工作並改善其物質狀況,那麼與其他社群發生衝突的機會就會減少。然而,持續的經濟衰退狀況以及將移民與廉價勞動力聯絡在一起,可能會加劇社群之間的衝突。 [65]
相當多的理論思考將文化視為其他因素的驅動因素。這實際上是可以理解的,並且將在後面透過香港和希臘的案例得到支援。如上所述,文化是態度、習俗和信仰的總和,它將一群人與另一群人區分開來。用更簡單的語言來說,正如非學術性線上定義的那樣,它指的是知識、經驗、信念、價值觀、態度、意義、等級制度、宗教、時間觀念、角色、空間關係、宇宙概念以及物質物件和財產的累積沉澱。
一般來說,文化決定論在欠發達或發展中國家更為普遍,因為人們更容易接受而不加思考地接受,並透過一代又一代的交流和模仿在社會中流傳。 [70]
我們看到文化決定論在未來影響政治管理的方式,可以與以下例子相關。在許多民主國家,許多人將媒體視為第四種權力,它與典型的三權分立(立法、行政和司法)相一致(孟德斯鳩)。[71] 談談權力分立的歷史,[72] 它可以追溯到 1787 年新憲法的透過,美國新生政府的結構要求設立三個獨立的部門,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權力,以及一套權力制衡制度。這將確保任何一個部門都不會變得過於強大,因為其他部門將始終能夠制衡另外兩個部門的權力。這些部門共同努力管理國家,併為我們所有人都制定生活準則。
全世界都有案例證明,媒體可以透過引發公眾討論來改變政府在政策或政治安排上的決定。在社會和經濟發展方面,媒體與文化演進有著密切的聯絡,雖然不完全一致。例如,為了培養年輕一代的批判性思維,香港在強制性的12年免費教育制度下,將通識教育列為初中和高中的必修課程,這可以被視為社會發展。社會中批判性思維和討論文化的盛行程度也越來越高。因此,公眾在2012年反對政府的國民教育政策時,產生了顯著的影響[73]。我們看到了媒體在改變政治安排方面所發揮的非凡作用,即使將媒體置於其他文化形式之中,它們所講述的故事仍然相同。未來,這種影響力可能會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而更加盛行。
我們也可以從古希臘看到文化如何決定政治安排。當時,希臘人傾向於認為,只有懂他們語言的人才能瞭解政治安排,進行思想交流和交換。否則,他們會被視為野蠻人。這就是他們高度重視語言等文化因素的原因,因為這些因素可以讓人們展現他們的本性和思想。他們在文化認同方面有著明確的界限,並沒有屈服於技術決定論的觀點,即認為技術是決定其他因素的關鍵因素。 尼可洛·馬基雅維利 指出,文化的元素,特別是宗教,可以產生特定的政治安排,對擁有這些安排的人有利。
評論員 帕特·布坎南 和經濟學家 羅伯特·巴羅 也指出,文化規範會影響政府的政治安排。這在後代中尤為明顯。
壓制激進潛力的法律
[edit | edit source]壓制激進潛力的法律是一個與文化決定論相關的概念,它指出,任何新技術的創新潛力都會被有意地削減,以維持社會或企業的現狀。新技術並沒有帶來顛覆和變革,而是被納入現有結構中,成為其中的一部分。這個概念是由 布萊恩·溫斯頓 在他1986年的著作《誤解媒體》中提出的[74]。
雖然該法律在專案中早些時候有所描述,但它也與關於文化和技術決定論未來的討論有關。透過從該法律推斷,我們可以得出對未來的各種可能性,從憤世嫉俗到徹頭徹尾的烏托邦。麥克奎爾指出,“無論潛在的可能性如何,商業、工業、軍事和官僚機構的需求在推動發展和決定創新如何實際應用方面發揮了最大作用。”[75] 支援這一點的一個例子可能是民主與社交媒體之間的互動關係。
社交媒體有潛力支援民主制度的改革和革命。1991年,奈斯位元指出,“隨著資訊即時共享,我們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的瞭解與我們的代表一樣多,而且瞭解的速度也一樣快。事實上,我們已經超越了代議制民主的歷史效用。”[76] 更重要的是,這項技術還使得在沒有代表的情況下組織民主成為可能,這是以前在後勤上無法實現的。然而,在奈斯位元寫這本書後的二十五年中,英國的民主程序並沒有發生重大變化。正如壓制法律所暗示的那樣,新技術已經成為這一程序的一部分——例如,現在可以在網上登記投票——但代議制民主政府的更大結構沒有改變。曾經有過線上投票的嘗試,但都被取消了[77]。這表明,無論是在民主政府的例子中,還是在更廣泛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中,新技術所帶來的任何改變都將是漸進式的,而不是激進的。
我們可以看到壓制法律下歷史上的漸進式變化的例子,這些例子也指向未來。一個非常近期的例子是無人機技術。它最初是為戰爭而開發的,第一個動力 無人駕駛飛機 是在1916年製造的,但現在也被用於與戰爭幾乎完全相反的專案:野生動物保護[78]。
ConservationDrones.org 指出,當時的無人機成本過高,他們自己嘗試製造一臺無人機花費了2000美元,他們認為這是“低成本”;此後,無人機的價格已經下降,現在可以以50英鎊的價格購買一臺無人機。同樣,這也與壓制法律的概念有關。正是現有商業結構的參與,才使得這項技術的成本降低到足以讓那些將它用於開發者最初意圖之外的人能夠負擔得起。這在以前的技術中一直是一個可觀察到的模式。最初的商用計算機價格過高,但現在大多數人至少在家中擁有不止一臺計算機。這是一種在未來可能會隨著其他技術的出現而重複出現的模式。
技術決定論
[edit | edit source]未來工作效率
[edit | edit source]我們正處於技術革命的浪潮之中。技術徹底改變了人們工作和執行簡單任務的方式。近年來,自動化辦公系統[79]改變了辦公室的效率及其運營方式。計算機和技術使每個辦公室員工能夠比以前在沒有輔助的情況下完成更多工作。藉助新技術,計算機可以快速解讀資訊,並且資訊的傳輸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技術已經並且將繼續影響工作文化,因為它為辦公室提供了以下優勢:安全、電子郵件效率、更好的客戶服務、輕鬆儲存、自動審計跟蹤、節省時間、簡單、可訪問性、業務發展和投資回報[80]。所有這些因素都使公司能夠擴充套件業務,承接更多工作,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會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事實上,技術帶來的生產力提高可能會減少以前工人所需的體力勞動。我們已經看到技術改變了辦公室環境,實現了辦公自動化,但在未來,工廠自動化也將更加普遍[79]。

技術對未來就業的影響
[edit | edit source]關於技術將如何改變就業和勞動力的文化,仍然存在很多爭議。一些理論家認為,技術進步將在經濟的其他領域創造新的就業機會[79]。他們說,沒有理由認為技術發展不會像過去那樣增加就業和實際收入[81]。反對這一理論的主要論點之一是,技術創新可能會改變執行任務所需的技能組合。一個人可能需要更熟練才能勝過機器人。儘管如此,仍然會創造出幫助維護和設計未來技術/機器人的工作。其他人認為,技術可能會在未來對我們的文化和就業造成負面影響。他們認為,機器人和機器將消除對工人的需求,並且能夠以更高的效率執行相同的任務。新技術可能會讓失業者更難找到工作。技術創新提高了工人為了勝過計算機或機器人所需的技能。這些增強後的技能組合似乎與許多失業者的技能組合不匹配。相信這一點的理論家認為,隨著計算機成本的降低,公司將使用更多資本,更少勞動力來運營。他們認為,為了在未來為人類提供工作崗位,而不是機器人,經濟需要以更快的速度增長[79]。技術將繼續進步,改變商業和勞動力的文化,這種技術在未來的影響將繼續引發爭論。
人類交流
[edit | edit source]“如今,我們可以用Skype與不同大陸的同事進行視訊通話,用Twitter追蹤全球趨勢,用智慧手機管理多個電子郵件帳戶,在LinkedIn上與同行專業人士協調,在SnapChat和WhatsApp上分享昨晚的照片和故事,在Instagram上推出品牌,在Facebook上建立社群,收聽我們最喜歡的全球播客,從新聞應用程式獲取最新訊息,用Uber叫車去辦公室,用FitBit監控我們的日常卡路里消耗。而且我們可以在不離開床的情況下完成所有這些事情。” [14]
眾所周知,30 年前,人們不會發簡訊、視訊通話或網購等。那個時候的世界更簡單,科技也更少。然而,時代在變,現在用手機發簡訊已經比寫信更常見了。科技引領著我們走向未來,前途光明。最近的蓋洛普調查發現,大約 39% 的成年人認為“發簡訊、使用手機和傳送及閱讀電子郵件是使用最頻繁的非個人交流方式”。[15] 科技正在改變人們日常的溝通方式。文章還提到,年齡在溝通風格上造成了巨大差異。年輕一代更頻繁地使用手機,並嚴重依賴它們,而老一輩則不然。那麼,這對於未來意味著什麼呢?年輕一代與朋友和家人保持聯絡更加密切。隨著他們年齡的增長,這可能會創造一種始終需要與他人保持聯絡的氛圍。這也可能影響他們結婚的時間。隨著這一代人的老去,他們也會更容易獲得曾經無法獲得的東西,比如行動不便後需要的幫助。與如今許多情況下與世隔絕的老人不同,未來的老年人會繼續參與社會生活。 [16] 這種“永遠線上”的文化有很多好處,但也存在著一些負面影響。有可能人類會試圖發明更多溝通工具來指導我們的推理方式、行為方式,甚至感情表達方式。溝通不僅限於我們與他人的交流,也包括我們與自我的交流。 [17]
結論
[edit | edit source]因此,為了總結本華夏公益教科書,它包含了許多章節,涵蓋了文化決定論和技術決定論及其對媒體和社會的影響。如前所述,文化決定論和技術決定論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展,並且在當今世界仍在不斷發展。
在歷史章節中,概述了文化決定論和技術決定論是如何產生的,以及它們在歷史上是如何變化的。本章還重點介紹了文化決定論和技術決定論早期的一些主要理論家,他們對這兩大主題的現代觀點影響深遠。
在定義章節中,重點討論了這兩個術語的定義在過去幾年中是如何發生巨大變化的,包括新媒體形式的引入以及理論家之間的持續爭論。本節還深入探討並定義了“新媒體”一詞,因為它可以被多種方式解釋和理解,並由於其廣泛性而被深入探討。然後,它重點關注了這些巨大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可能帶來的擔憂,以及它們如何影響社會的觀點,同時討論了它在未來很可能如何進一步適應。
在下一章主要概念中,探討了技術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背後的主要理論,並透過應用於理論例項來將其置於背景中。
此外,正如反對章節所示,這兩個理論都遭到了社會學和技術領域的許多知名理論家的反對,雖然許多人贊成相反的理論,但也有少數人提出了他們自己獨特的見解。
最後,在未來,人類很有可能繼續發明自動化技術來完成我們自己不想做或覺得沒有意義的、或者用機器人制作成本更低的那些任務。文化決定論和技術決定論可能對我們的未來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想象未來,因為即使我們研究多年,也沒有任何東西能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未來會隨著我們文化和科技的不斷發展而不斷重塑和變化。
From our research, we can prove that it really is an Internet of Everything!
詞彙表
[edit | edit source]教條哲學。以專橫或傲慢的方式斷言或堅持觀點或原則,尤其是在未經證實或未經檢驗的情況下。
硬決定論關於自由意志的觀點,認為決定論是正確的,它與自由意志不相容,因此自由意志並不存在。
非教條哲學。從自然開始,並依附於自然,自然哲學。
本體。(在康德哲學中)事物本身,區別於事物透過現象屬性可被感官認知的狀態。
還原論。幾種相關的但不同的哲學立場,涉及現象或理論之間的聯絡,“將”一個還原為另一個,通常被認為是“更簡單”或“更基礎”的。
浪漫主義。一種藝術、文學和智力運動,起源於 18 世紀末的歐洲,並在大多數地區於 1800 年至 1850 年間的某個時期達到頂峰。
軟決定論。關於技術如何與社會政治形勢相互作用的一種被動觀點。
論點-反論點-綜合。論點是一個智力命題;反論點只是論點的否定,是對命題的反應;綜合透過調和論點和反論點的共同真理,形成一個新的論點,從而解決它們之間的衝突,重新開始這一過程。
參考文獻
[edit | edit source]- ↑ http://study.com/academy/lesson/cultural-determinism-definition-and-theory.html
- ↑ 文化決定論
- ↑ 技術決定論
- ↑ [1]
- ↑ http://www.buzzle.com/articles/cultural-determinism-meaning-and-examples.html
- ↑ Lister, M., Dovey, J., Giddings, S., Grant, I., & Kelly, K. (2008). 新媒體:批判性導論(第 2 版)。紐約,紐約:泰勒與弗朗西斯。
- ↑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schlegel/
- ↑ http://www.uh.edu/engines/romanticism/introduction.html
- ↑ Lister, M., Dovey, J., Giddings, S., Grant, I., & Kelly, K. (2008). 新媒體:批判性導論(第 2 版)。紐約,紐約:泰勒與弗朗西斯
- ↑ a b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johann-fichte/
- ↑ http://www.enotes.com/topics/johann-gottlieb-fichte/critical-essays
- ↑ http://www.tennesseeplayers.org/goethebyschweitz.html
- ↑ “非愛國保守主義者”大衛·弗魯姆,2003 年 4 月 7 日,國家評論,存檔於 2010 年 1 月 8 日,在 Wayback Machine。
- ↑ Marchand,P. (1998) 馬歇爾·麥克盧漢:媒介與使者(第 2 版)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
- ↑ http://www.southalabama.edu/coe/bset/surry/papers/dtit/dtit.htm
- ↑ http://www.medialit.org/sites/default/files/Global%20Local%20White%20Paper.pdf
- ↑ a b http://www.media-studies.ca/articles/innis.htm
- ↑ Ferguson, G. V., & Innis, H. A. (1950). 帝國與傳播。國際雜誌,6(1),55。doi:10.2307/40197684
- ↑ Innis, H. A. (1951). 溝通的偏見。多倫多:多倫多大學出版社。
- ↑ https://books.google.co.uk/books?id=lGNQ2gotOVkC&pg=PA52&lpg=PA52&dq=technological+determinism+leslie+white&source=bl&ots=7HaY_JHsFd&sig=pfNCuDXuT9zLHOv7I_lIPCFakI4&hl=en&sa=X&ved=0ahUKEwjw_5LDkKLLAhWFbhQKHSS3CHkQ6AEISzAJ#v=onepage&q=technological%20determinism%20leslie%20white&f=false
- ↑ https://books.google.co.uk/books?id=4zj8EwiqWIwC&pg=PA119&dq=leslie+white+energy+and+the+evolution+of+culture+1943&hl=en&sa=X&ved=0ahUKEwiA9sWOv6LLAhUBUBQKHb0XC1gQ6AEINTAD#v=onepage&q=leslie%20white%20energy%20and%20the%20evolution%20of%20culture%201943&f=false
- ↑ http://anthropology.ua.edu/cultures/cultures.php?culture=American%20Materialism
- ↑ http://muse.jhu.edu/login?auth=0&type=summary&url=/journals/technology_and_culture/v043/43.2molella.html
- ↑ http://wphna.org/wp-content/uploads/2014/06/2011-04-Book-Forum-Tom-Vanderbilt-Mechanization-TC.pdf
- ↑ Hall, Bert S. (1989). "Lynn Townsend White, Jr. (1907–1987)". Technology and Culture 30 (1): 194–213.
- ↑ Lynn Townsend White, Jr., Medieval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Collection of nineteen of his papers published elsewhere between 1940 and 1975.
- ↑ Cultural Visions: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Edited by Penny Schine Gold and Benjamin C. Sax Publication Date: January 2000
- ↑ Hartley, John. 1996. Popular reality: Journalism, modernity, popular culture. London: Arnold.
- ↑ Young, J. (2001). Henry Adams: The Historian as Political Theorist.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 ↑ Roe Smith, M.,& Marx, L. (Eds.). (1994). Does Technology Drive History? The Dilemma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Massachusett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 Chant, C.,& Goodman, D. (1999). Pre-Industrial Cities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Open University.
- ↑ Lister, M., Dovey, J., Giddings, S., Grant, I., Kelly, K. (2003). New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 Lister, M.L et al. (2003). New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st ed.). New York: Routledge.
- ↑ https://books.google.co.uk/books?hl=en&lr=&id=I8dPhB88Sx4C&oi=fnd&pg=PA107&dq=marshall+mcluhan+understanding+media&ots=CD0FqH8C9S&sig=CusXusEjJAGErJT1ETQoVscvCys#v=onepage&q=marshall%20mcluhan%20understanding%20media&f=false
- ↑ [2] McLuhan, M.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 ↑ [3]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MIT Press: Massachusetts
- ↑ [4] McLuhan, M. (1967).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 ↑ [5] McLuhan, Marshall. The Gutenberg Galaxy (Toronto, 1962) Pp.143 - 155
- ↑ [6] Rubin, Jared. 'Printing and protestants: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role of printing in the Reformation' i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ume 96, issue 2 (2014) Pp. 7-12
- ↑ [7] Atkinson, Benedict & Fitzgerald, Brian. 'Printing, Re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in A Short History of Copyright: The Genie of Information (Heidelberg, 2014) Pp. 15-16
- ↑ [McLuhan, Marshall. Understanding Media, London: Sphere, 1968]
- ↑ [8]
- ↑ a b http://web.mit.edu/allanmc/www/mcluhan.mediummessage.pdf
- ↑ a b c d [9] W. G. Bringmann (1969),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McLuhan's Ideas Concerning Effects of "Hot" and "Cool" Communications Media, Psychological Reports.
- ↑ a b D. A. Fishman (2006), Rethinking Marshall McLuhan: Reflections on a Media Theorist,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 ↑ a b M. McLuhan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 ↑ [10] Williams, R. (1974).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Collins: London
- ↑ [11] Williams, Raymond.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New York, 1975) Pp.14-19
- ↑ [12] Ibid.
- ↑ Adrian Athique, Digital Media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 ↑ http://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2/mar/28/uk-riots-twitter-facebook
- ↑ [13] DARPA Official Website
- ↑ a b Green, Lelia. Gree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 & Society. Sage, 2001. ISBN 9781446229057.
- ↑ a b Winner, Langdon. "Technology as Forms of Life".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David M. Kaplan.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ISBN 978-0742564015. 103-113
- ↑ Winston, Brian. Misunderstanding Med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ISBN 9780674576636
- ↑ Winston, Brian. Media,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 History - From the Telegraph to the Internet. Psychology Press, 1998, ISBN 978-0415142304. Pg 2
- ↑ Winston, Brian. "How are media born and developed?". Questioning the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Downing, Mohammadi, & Sreberny-Mohammadi (eds). Sage, Newbury Park, California, 1990, ISBN 0803936427. pp 55-72
- ↑ Understanding Media, McGraw-Hill, 1964 p.1
- ↑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Vintage Books, Toronto, 1993, p. 7
- ↑ Three Faces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in Does Technology Drive History?: The Dilemma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4, p. 85
- ↑ Do Machines Make History? in Does Technology Drive History?: The Dilemma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4, p. 55
- ↑ Murphie, Andrew. & Potts, John. (2003). Culture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 Palgrave, http://www.loc.gov/catdir/toc/hol031/2002074824.html
- ↑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experts/nigel-barber-phd
- ↑ http://www.pdfdrive.net/human-universals-human-nature-human-culture-e582591.html
- ↑ a b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75781/13-520-national-identities-change-as-ethnic-composition-changes.pdf
- ↑ McNeill, W.H. (1986) Polyethnicity and National Unity in World History,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 ↑ Fukuyama, F. (2007) ‘Identity and migration’, Prospect Magazine, February 25th 2007
- ↑ Vasta, E. (2009) ‘Accommodating diversity: understanding multiculturalism’, article on website, http://www.confluence.org.uk/2009/04/16/accommodating-diversityunderstanding-multiculturalism/
- ↑ Modood, T. (2007) Multiculturalism: A Civic Ide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 http://psychologydictionary.org/cultural-determinism/
- ↑ http://www.americassurvivalguide.com/montesquieu.php
- ↑ https://tw.voicetube.com/videos/6013
- ↑ https://cochina.co/2012/09/佔領十日——“反國民教育科”全記錄/
- ↑ Winston, B. (1986) Misunderstanding med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McQuail, D. (2010) 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SAGE publications. p.155.
- ↑ Naisbitt, J. (1991) Megatrends. London: Pan Macmillan.
- ↑ Wright, S. (2006) "Electrifying democracy? 10 years of policy and practice",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 59:2
- ↑ http://conservationdrones.org/our-story/
- ↑ a b c d Lewis D. Solomon, The Microelectronics Revolution, Job Displacement, and the Future of Work: A Policy Commentary, 63 Chi.-Kent. L. Rev. 65 (1987). Available at: http://scholarship.kentlaw.iit.edu/cklawreview/vol63/iss1/4
- ↑ Top 10 Benefits a Paperless Office Can Provide." 10 Benefits a Paperless Office Can Provide. Forum of Private Business, 2014. Web. 08 Mar. 2016. <https://www.fpb.org/business-support/top-10-benefits-paperless-office-can-provide>
- ↑ Bartlett, The Luddite Answer to Unemployment, Wall St. J., July 18, 1983, at 18, col. 3. See also N. GINGRICH, WINDOW OF OPPORTUNITY: A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88 (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