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戲劇史:17 世紀至今/美國二戰後
“美國劇作家...往往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表現出穩步下降的模式...他們的早期作品(通常是相當自傳的)是他們最好的作品,因此,他們的職業生涯並沒有表現出穩步的深化和成熟,而是經常變成一種相當悲傷的,通常是瘋狂的試圖重新捕捉第一件事的魔力與失去的純真” (Rosenberg, 1967 p 53)。

在二戰後的美國劇作家中,田納西·威廉姆斯(1911-1983)以“玻璃動物園”(1944 年),“慾望街車”(1947 年)和“夏日煙雲”(1948 年)而聞名。
“玻璃動物園”是一部“時間成為核心關注點的戲劇。因此,阿曼達的現在,她生活在社會邊緣,靠討好那些需要她支援的人來生存,與過去形成對比,在過去,至少在記憶和想象的層面上,她成為了關注的中心。勞拉固執地退回到她動物園的兒童世界,其令人悲傷的諷刺之處恰恰在於它是一種對自身成熟、對時間的否認。即使是她的‘紳士來訪者’也被迫短暫地面對他高中時代承諾(回憶學校年鑑中的照片)與他目前生活的現實之間的差異。時間已經開始打碎這些人,因為他們的幻想和夢想被經濟必要性和自然程序的現實事實所否認。勞拉透過退回到想象的永恆世界來尋求免受傷害,阿曼達透過退回到一個重新塑造以提供安慰的過去來尋求免受傷害。只有湯姆似乎逃脫了這些諷刺,代價是他拋棄了那些與他分享過生活的人。但戲劇本身就是他並沒有比他的家人更多地逃脫過去,因為為什麼他還要召喚這個世界存在,除了過去繼續發揮其力量,因為他拋棄的內疚將他拉回到那些他認為是他的自由的必要代價的人。 (Bigsby, 2005 p 268)。這部戲劇“將一個抑鬱症故事轉化為一個敏感的角色戲劇。它生動地體現了一個小型家庭徒勞的掙扎——一個迷糊的南方婦女,她依戀著美好歲月的記憶,她痛苦地害羞、殘疾的女兒,母親試圖為她找到‘紳士來訪者’,以及一個不安分的詩人兒子,他厭倦了無休止的嘮叨,在把一個已經訂婚的年輕人帶給他的姐姐的悲喜劇鬧劇之後,他離家出走” (Gassner, 1954a, pp 698-699)。Berkowitz (1992) 建議“與其拒絕阿曼達和勞拉為不適應者,不如將他們視為普通人的美麗替代品” (p 89)。然而,這種態度淡化了勞拉未能找到伴侶的內在悲傷。“勞拉退回到她的幻想世界,玻璃動物園象徵著她脆弱的靈魂。令人心碎的是,勞拉幾乎沒有機會過上獨立於她專橫的母親的生活,她沉浸在她青春時代的浪漫記憶中,那時她是眾多‘紳士來訪者’中的一位貴婦。這部戲被呈現為回憶,既有力又悲傷,捕捉了那些現在生活在貧困邊緣但曾經過上更美好生活的人的靈魂和渴望”(Schlueter, 2000, p 299)。“對人物的溫柔洞察,微妙的象徵主義,對環境的熟悉和持久的哀歌基調,如同對卓越戲劇的啟示”(Atkinson, 1974 pp 405-406)。“勞拉無法扮演美女的角色。她強烈的性挫折感加上父親的拋棄和母親的暴政,造成了如此脆弱的自我意識,以至於她完全無法進行阿曼達規定的那種風情萬種的行為...阿曼達理解他們世界的社會和經濟現實,透過模仿美女的角色,她試圖教會女兒一項重要的生存技能”(Hovis, 2011 p 179)。由於工作的乏味,湯姆拒絕“社會對勤勞、自力更生、向上流動年輕人的要求”,因此他為了自己的幸福拋棄了母親和姐姐(Greenfield, 1982 p 122)。這樣的評論家對吉姆的看法過於消極,認為“他的價值觀給人們帶來了對美好美國的虛假希望”(p 123),而他的價值觀對情節沒有任何直接影響。同樣地,Fleche (1997) 認為吉姆的聯想很有趣,因為他將知識等同於金錢和權力;此外,還擔心“科學的解釋意味著一種潛伏的征服意願”(p 85)。誠然,吉姆代表了溫菲爾德一家虛假的希望,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的想法,與勞拉的命運無關,是錯誤的。Krasner (2006) 對吉姆表達了積極的看法,認為吉姆“充滿樂觀”,“用他樂觀的情緒逗樂大家”,“相信未來”,“沒有讓大蕭條讓他感到沮喪”(p 32)。
"The shock of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when it was first staged lay in the fact that, outside of O’Neill’s work, this was the first American play in which sexuality was patently at the core of the lives of all its principal characters, a sexuality with the power to redeem or destroy, to compound or negate the forces which bore on those caught in a moment of social change” (Bigsby, 2005 p 277). The play is “a modern tragedy without a hero or a villain; each protagonist is also an antagonist, and so instead of a hero’s journey, we are offered rather a raw and painful view of human misunderstanding” (Keith, 2018 p 174). The play “placed in opposition to Stanley Kowalski at the beginning of play, [Blanche as] the aristocrat who condescends to the plebeian when she is not actually scorning him...Stella is fortunate...as ordinary people, who have an aptitude for the ‘blisses of the commonplace’, are fortunate. Blanche, on the contrary, cannot renounce her view of herself as a rare individual...One cannot help pitying [Blanche] and also laughing at her because the life she affects to despise seems so invincibly alive while her eyes are fixed on a decadent past. But pity claims priority because her helplessness is so palpable, and because she is so evidently concealing a wounded past” (Gassner, 1965 pp 375-381). “Her consuming need...is to make herself and others aware of her refinement. She is concealing her tawdry past of alcoholism, incontinence, and common prostitution” (Gassner, 1954b pp 355-356). "Before Blanche’s arrival, Stanley and Stella enjoyed, through compromise, an intimate, happy marriage, and in this could be said to have achieved a degree of civilization, of humanity, unequaled by the DuBoises of Belle Reve, a distortion of “beau rêve”, beautiful dream; before Blanche’s arrival, Stanley also enjoyed the best of friendships with Mitch, who in some ways is as sensitive and in need of understanding as Blanche" (Cardullo, 2016 p 90). When Blanche arrives via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Stanley immediately resents her presence, viewing her as a threat in reminding Stella "of their past prior refinement and sophistication" (Krasner, 2006 p 41). "Blanche stands for idealism, culture, purity, and the love of beauty, but also for falsehood, fantasy, weakness, and the rejection of unpleasant reality" (Berkowitz, 1992 p 90). Blanche is the southern belle clashing in the new south, a more hostile environment than the old south she is used to, when “ante-bellum days represent an ideal of gracious living, an ideal that includes a code of personal honor extending into every area of his experience...So Blanche appears high-strung and sensitive, on one hand, but exploiting the Kowalskis’ resources and willing to destroy her sister’s marriage, on the other. As in her youth, she plays the coquette, requesting Stanley to button up her dress, teaching Mitch how to present flowers by bowing first, dropping a French word or two. But when a tempting newsboy enters, coyness turns to downright kissing. Yet clinging to the old ways governs her mind when she refuses to bed with Mitch, disillusioned after Stanley’s report of her past conduct, even when pre-nuptial copulation appears as her last hope. The situation worsens when instead of submitting to Mitch’s love she is raped by Stanley, the opposite pole of southern gallantry. Nevertheless, at the end, the intruding imposter appears worthy of pity through accumulated maledictions: husband’s suicide, family deaths, loss of Belle Reve, job dismissal, and send-off to a psychiatric institution" (Porter, 1969, pp 154-173). The newsboy scene's "real poignancy, is its evocation of Blanche’s own lost innocence as well as her imagination and depth of feeling- an innocence or purity suggested by her very name (the feminine form of the adjective 'white' in French), which identifies her with the achromatic color white as opposed to Stanley’s primary colors and by her astrological sign, Virgo (for 'virgin'). We may see Blanche in the negative light of seductress here, but we should also see her in a positive light, as one who recognizes her own lost innocence (not accidentally, in the figure of a young man who recalls Allan Grey) and responds to it effusively. This is one way of explaining her turning to a seventeen-year-old boy for an affair in Laurel after her many 'intimacies' with men at the Hotel Flamingo: in turning to a boy, Blanche was attempting to return to her own youth when, with Allan, she 'made the discovery- love. All at once and much, much too completely” (Cardullo, 2016 p 100). "More than any major character in the early postwar years, Blanche embodies the conflicts of a changing world. A lover of poetry and music and ballroom taffeta, Blanche stands as a fading tribute to refined life unable to survive in Stanley Kowalski’s crude and raucous world. Herself a complicated woman, Blanche has memories of an ideal she may never herself have known and finds refuge in alcohol and lies" (Schlueter, 2000, p 300). “Stanley’s reference to Blanche as a ‘queen’...reveal that his resentment stems at least in part from class envy...In his relationships with both Blanche and Stella, Stanley longs to reduce them to his level, as his remark about dragging Stella ‘down off them columns’ indicates. Alternatively, Stanley posits himself as royalty” (Harrington, 2002 p 71). Mitch’s rejection of Blanche is a cruel counterpart of her rejection of her homosexual husband (Featherstone, 2008 p 265). “Blanche finds her own version of Stanley in Mitch, who, although of the same working-class background as Stanley, has ‘a sort of sensitive look’ and seems to her ‘superior’ to his other friends. Mitch becomes the ‘cleft in the rock of the world that I could hide in’, and Blanche admits to Stella that she wants ‘to deceive him enough to make him want me’. The deception involves her acting out the tradition, refusing any sexual activity beyond a kiss because, she tells Mitch, she has ‘old-fashioned ideals’. Williams makes sure that the audience is aware of Blanche’s acting, as she rolls her eyes when she says this, and, perhaps more dangerously, compares herself to the most famous courtesan in literature, Alexandre Dumas fils’s Camille, when she tells him ‘Je suis la Dame aux Camellias! Vous êtes Armand.’ and after Mitch assures her that he doesn’t understand French, asks him, 'Voulez-vous couchez avec moi ce soir?’ [Would you like to sleep with me this evening?], which it wouldn’t take a great knowledge of French for someone who frequents the French Quarter of New Orleans to understand. There is a dangerous flirtation with self-exposure in Blanche’s behavior with Mitch that is related to her guilt over her behavior with Allan and her reckless promiscuity subsequently. Nonetheless, she succeeds in deceiving Mitch until Stanley discovers her past, with its ‘intimacies with strangers’, and she is forced to admit it to Mitch, who finds her no longer ‘straight’ or ‘clean enough to bring in the house with [his] mother’ despite her plea, ‘I didn’t lie in my heart’” (Murphy, 2014 p 78). "There is a doubleness about Blanche’s involvement with Mitch. In each case, she seems less interested in the affair for its own sake than in the ritual of romance in its relation to her first love, the defining relationship of her life...Similarly, she recognizes the possibilities for imaginatively evoking the past when she flirts with the newspaper boy” (Hovis, 2011 pp 178-182). “Blanche...calculates the effect of her performance on her various audiences...By contrast, Stella dispenses with the role of belle and speaks candidly to her husband, trusting him to respect her openness with commensurate tenderness and honesty. Stella fled Belle Reve and the example of her older sister perhaps because she recognized the dangers of performance. Unfortunately, Stella fails to recognize the dangers of not performing. “The duality of Dionysius whose gift of wine can bring both pleasure and madness permeates this world. Similarly, the play’s Dionysian sexual passion leads both to ecstasy (desire) and destruction (cemeteries) while the inexorable passage of time juxtaposes Blanche’s poetic dream of Elysian Fields with the decay of the Quarter. The plot embodies the complex structure and climax of Aristotelian drama, but Williams alters its proportions to his own dramatic ends. While the play fits no standard definition of tragedy, Blanche’s struggle with Stanley endows her with the status of a tragic figure. Intro- duced as an unsympathetic and pretentious snob, she becomes more sympathetic as she mentally disintegrates over the play’s 11 scenes. Following the rising action of scenes 1–6, the brutal reversal stretches over scenes 7–9 culminating in the violent climax when Stanley rapes Blanche at the end of scene 10. The painful extended denouement of scene 11 reveals the irrevocable change in the lives of the central characters” (Berwind, 2015 p 242). Unlike Blanche’s, Stella’s passivity is real and Stanley takes advantage of it by intermittingly bullying her and by virtually denying her a voice in the affairs of their home. He invites his drinking buddies over for poker nights and ignores her objections. He physically and emotionally abuses her, even when she is pregnant- and afterward, to the chagrin of Blanche, Stella returns home to forgive and make love to her husband. When Stanley ultimately betrays Stella’s trust by raping her sister while Stella is in labor at the hospital, Stella passively accepts Stanley’s denial of Blanche’s report and even acquiesces to his demand that her sister be institutionalized for her delusions...Stella is confronted with the choice of choosing her husband or her sister. Stella chooses Stanley (Lewis, 1965 p 63). “Stella’s concern for her sister on the one hand and her content with her life with her loutish husband are objective and understanding” (Atkinson and Hirschfeld, 1973 p 194). "In contrast to her sister, Stella already has her man, a southern belle content to submit to her husband’s lack of manners and to attend to household affairs in a degraded context. Stanley’s crude taste for say-what-I-think behavior extends to mother-dominated Mitch, who when heading towards the bathroom hears his friend say: 'Hurry back and we’ll fix you a sugar-tit.' For entertainment, he wants sex and 'getting the colored lights going', akin to a people’s taste for fireworks and kaleidoscopes. There is ironic contrast between words and acts. While Stanley dirties his sister-in-law’s reputation, Blanche takes a bath" (Corrigan, 1987, p 31). "When Blanche leaves for the insane asylum, and the oblivion attending it, at the end of Scene 11, Stanley remains behind with Stella: his way of life thus appears to have won out over his sister-in-law’s. But it is not that simple. Life for the Kowalskis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fter Blanche’s departure, and Williams provides plenty of evidence for this conclusion in the final scene of the play— evidence that, once again, has hitherto mostly been ignored by critics. If the Mexican woman of scene 9 is the symbol of death, desire, and the past in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then the newborn child of Scene 11 is the play’s symbol of life, maternity, and the future for Stella, but not for the paternal Stanley. Stella’s absence from both scene 9 and Scene 10 while she is giving birth, coupled with her reappearance onstage in scene 11, serves to distance her in our minds from her husband and to pressure her relationship with him beyond the perimeters of the play. That Stella does not once speak to Stanley in the last scene of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even when addressed by him one time) is indicative of the essential silence that will permeate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together" (Cardullo, 2016 p 97).
"夏日與煙" 這個標題來自於 [哈特] 克萊恩的《行為的象徵》:“到那時,夏日與煙已過去 / 海豚仍在跳躍,拱起地平線 / 但僅僅是為了構建起對精神之門的回憶”。克萊恩作品中的這個標題喚起了對一個早已過了頂峰,正在衰落的世界的懷舊之情。在唯一一個迴響克萊恩短語的段落中,威廉姆斯明確的意圖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當阿爾瑪在戲劇的最後描述她之前的“清教徒”自我(以及暗示所有遵循這種準則的人)時,她說:“她死於去年夏天,被她內心燃燒的火焰的煙霧窒息了” (Debusscher, 2005 pp 75-76)。 “單獨考慮,故事情節顯示出威廉姆斯有潛力創作平庸的小說……《夏日與煙》的本質價值在於它作為一個戲劇的完整性。它是一個故事、情節、人物塑造、氛圍、情緒和悶熱諷刺態度的集合體” (Gassner, 1960 p 220)。阿爾瑪,她的名字喚起靈魂,拒絕肉體而選擇靈魂,而約翰則相反(Murphy, 2007 p 181)。“我更害怕你的靈魂,勝過你害怕我的肉體,”他坦白道。他們從未相遇,因為在阿爾瑪接受肉體的時刻,約翰已經接受了內莉,內莉似乎將肉體和靈魂融為一體。“這個戲劇揭示了阿爾瑪在愛人身上找不到性滿足和精神價值的失敗。她的愛人像她害怕他的肉體一樣害怕她的靈魂;他覺得不夠體面去觸碰她。由於她找不到真愛,她放棄了精神上的追求,把自己交給了第一個遇到的旅行推銷員” (Lumley, 1967 p 187)。加斯納(1954a)認為這部戲暗示阿爾瑪“因為過度挑剔而失去了愛情的機會……威廉姆斯的女主角被諷刺地失去了她一直刻意保持距離的男人,她被逼到絕望,和第一個遇到的閒散之人發生了約會。她的敏感和不幸的家庭生活帶來的痛苦挫折,讓這個理想主義的女孩踏上了一條充滿曲折但最終會導致她完全的道德和心理破產的道路” (p 741)。甘茨(1965)對阿爾瑪的結局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像布蘭奇[《慾望街車》中的杜波依斯]一樣,她註定要被她拒絕的衝動折磨,像布蘭奇一樣,她也轉向放蕩,但她對罪行的認識多少減輕了她的罪惡,在劇末,她暗示她選擇的那位旅行推銷員可能會帶領她走向救贖,而不是毀滅” (p 210)。 “不幸的是,[阿爾瑪]成長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大部分時間都和長輩在一起。多年來,沉悶的教堂娛樂活動和父親沉悶的佈道,讓阿爾瑪幾乎沒有機會接觸到光榮山那些不受約束的市民。由於她的狹隘訓練,她認為男人的本性會被動物性所粗化,只有精神才能控制這種動物性。事實上,她自己擁有真正深刻的性本能,它與她受保護的、乾涸的生活方式作鬥爭……對於約翰來說,他也面臨著毀滅性孤獨的困擾……在渴望與一位瞭解他真實性情、充滿熱情和激勵的愛人建立關係方面,他與阿爾瑪相似” (Herron, 1969 pp 363-364)。 “阿爾瑪……從她高雅的藝術、理想主義和歇斯底里的世界,走向一個更不理想的毒品和與旅行推銷員幽會的世界。與此同時,約翰朝著相反的方向前進,從月湖賭場的暴力陰影中的放縱,轉向努力工作、英勇的醫學和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當]阿爾瑪和約翰注視著永恆雕像時……雕像底部的文字被磨損了,無法辨認……是年幼的阿爾瑪將約翰引入到觸覺理解的肉體快樂中……威廉姆斯暗示我們與崇高無垠的相遇方式不是透過否定性慾,而是透過接受它……[在結尾]……約翰反抗了父權制,突然發現他的父權制衝動隨著父親的去世而變成了現實。此後,約翰承擔了父權制的地位,成為了一名好醫生、丈夫和模範公民,他拒絕了阿爾瑪[作為墮落女人]的追求” (Gross, 2002 pp 93-98)。在對結局的另一種解讀中,我們有“約翰與傳統的內莉結婚,阿爾瑪勾引了一名推銷員,暗示最終的贏家是保守的、以商業為中心的美國” (Abbotson, 2010 pp 50-51)。阿爾瑪“害怕承認她對布坎南的愛,因為她擔心僅僅表達這種愛就會摧毀它。但構建這個戲劇的諷刺之處在於,阿爾瑪開始確信有必要透過承認身體性慾的存在來完成她的生命,就在此時,布坎南瞭解到僅僅身體上的不足” (Bigsby, 1984 p 69)。“以一種圖解的方式,這兩個角色互換了位置,阿爾瑪意識到她對約翰的吸引力的性本質,而約翰開始意識到,儘管他的解剖圖中沒有“靈魂”,但阿爾瑪是對的,愛可以是超越性慾的東西,因為‘有些人……也能把他們的心帶到其中——也能把他們的靈魂帶到其中’。阿爾瑪最初拒絕了約翰的性挑逗,因為他‘不是一個紳士’,她堅持自己的理想,抵抗著他的感官慾望。但約翰在與阿爾瑪的關係中經歷了改變,儘管她最終發現‘那個說不的女孩……死於去年夏天——被她內心燃燒的火焰的煙霧窒息了’,她還發現‘局勢發生了報復性的轉變’,當他說他現在不能和她發生性關係時。他告訴她,‘我已經接受了你的想法,那裡還有其他東西,一種非物質的東西——像煙一樣薄……知道它的存在——那麼整個事情——這個——我們難以理解的經歷——就有了新的價值,就像某些——某些在實驗室裡進行的狂野浪漫的工作’。他意識到‘我真正想要的不是你肉體上的東西’,而是一種‘被誤認為是冰的火焰。我仍然不明白它。’當約翰拒絕了羅莎·岡薩雷斯,他對她只有純粹的性吸引力,並與阿爾瑪以前的學生內莉·埃威爾訂婚時,象徵體系和心理鬥爭匯聚到了一起,內莉是一位有點臭名昭著的女人,她在火車站接送推銷員的女兒。在戲劇的結尾,內莉逃離了她的母親,並在索菲·紐科姆學院接受了教育。她將直接、充滿活力和青春的性慾與對阿爾瑪小姐的敬畏結合在一起,她稱阿爾瑪為“慈悲的天使”,而阿爾瑪對她和約翰都產生了影響。約翰的未來看起來穩定而資產階級,這是一段傳統但充滿愛的婚姻,顯然會包括健康的性元素。另一方面,阿爾瑪的未來就不那麼傳統了。最後一幕,她在噴泉前搭訕了一位年輕的推銷員,更加耐人尋味。她服用了一片安眠藥,讓她感覺“像中國瀉湖裡的一朵睡蓮”,她準備和這位推銷員一起去月湖賭場,那裡是她之前拒絕了約翰的求愛的地方。很明顯,她這次有不同的意圖,但劇本結局的意義是模稜兩可的。一方面,她正走在埃威爾夫人的足跡上,很可能會被鎮上的人排斥。如果她繼續這樣下去,就像斯坦利·科瓦爾斯基對布蘭奇·杜波依斯說的那樣,她的未來“已經為她規劃好了”。另一方面,她已經接受了自身的一部分,而對這部分的否定使她陷入痛苦的孤獨、歇斯底里和令人衰弱的驚恐發作,現在她似乎第一次獲得了平靜。當她和年輕的推銷員開玩笑時,她“以一種她從未有過的方式笑著,帶著一絲疲倦,但很自然”。《夏日與煙》結尾的整體感覺是兩位痛苦的主角的整合與平靜,以及失去。按照威廉姆斯象徵體系的術語,他們之間燃燒的激烈精神和性張力的火焰被撲滅了,留下了煙霧” (Murphy, 2014 pp 70-71)。
總的來說,費拉諾(2007)將威廉姆斯的戲劇描述為“以人物驅動的戲劇,情節淹沒在人物生活中發生的累積事件之下。情節點突然出現,通常令人驚訝,揭示出人物內心運作中從未見過的部分。這種現實主義分支通常與契訶夫聯絡在一起……除了契訶夫式的結構之外,還有威廉姆斯的印記——對怪誕的浪漫吸引,醜陋身體中的美麗精神,對破碎、痛苦和畸形者的同情。這些戲劇既不是完全壓抑的黑暗,也不是受損的人物註定要滅亡,正如人們在薩特或熱內作品中所預期的那樣。這些戲劇暗示著一種模糊的希望,如果不是救贖的話,那麼就是來自人物苦難的結果” (pp 425-426)。
"玻璃動物園"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30年代。地點:美國聖路易斯。
文字地址:https://archive.org/details/dli.ernet.2826 https://archive.org/details/dli.ernet.234940 http://www.pval.org/cms/lib/NY19000481/Centricity/Domain/105/the_glass_menagerie_messy_full_text.pdf
在一個晚上,在家裡和她的兒子湯姆和女兒勞拉在一起,阿曼達·溫菲爾德回憶起她在南方藍山的青春時光,當時年輕女子知道如何說話,紳士求婚者也很多。她嘲笑女兒今晚沒有紳士求婚者。“什麼,一個都沒有嗎?”她反諷地問道。第二天,阿曼達驚訝、羞愧和羞辱地得知,勞拉一直被她認為是商學院的學生,一直在城裡到處走。勞拉在打字速度測試中嘔吐,再也沒有回來。湯姆則經常在倉庫裡辛苦工作了一整天后去看電影,以維持家庭生計。阿曼達讓他找一個他姐姐可以約會的男人。作為她的兄弟,他應該願意幫忙,因為勞拉似乎不適合工作,也不適合吸引男人的注意力。她似乎只對照料她的玻璃動物園和聽留聲機唱片感興趣。湯姆在倉庫找了一個裝貨員吉姆·奧康納,讓他來他家吃飯,卻沒有提到勞拉。吉姆的收入已經超過了他,而且似乎有一個美好的未來。阿曼達詢問了湯姆關於吉姆的習慣,並且最終感到滿意。在後巷的平臺上,阿曼達說“這是一個糟糕的陽臺”,她希望一切順利。在吉姆來吃飯之前,阿曼達試圖用“欺騙者”塞滿勞拉的胸部,但她拒絕使用它。一個不安的勞拉認出了吉姆是她高中時曾經愛過的男孩,從那以後她經常想起他。當他走進房子時,她驚慌失措,倉促地離開了房間。在整個晚上,阿曼達說的大部分話。她自己做了三文魚,卻假裝是勞拉做的。當勞拉被迫回來時,她感到暈倒,就躺在沙發上休息。突然,燈滅了,因為吉姆忘記支付電費了,而是把錢花在了船員工會會費上,這是他搬走的第一步,因為他不想像那些看電影而不是搬家的人一樣。晚餐後,勞拉獨自和吉姆在一起。吉姆對世界很放鬆,他認為勞拉明顯缺乏自信。勞拉給他看她的玻璃動物園。當他們聽到從後巷對面的舞廳傳來的音樂時,吉姆建議他們跳舞。當他們跳舞時,他不小心撞到了玻璃動物,把獨角獸撞到了地板上,折斷了它的角。吉姆非常抱歉,但勞拉說沒關係。“現在它就像其他的馬一樣,”她總結道。當他們越來越親近時,吉姆順帶透露了他已經訂婚了。得知此事後,阿曼達對兒子事先不知道吉姆的訂婚感到憤怒。離開家人後,湯姆記起了當晚的事件,他建議他想象中的勞拉吹滅她的蠟燭。
“慾望街車”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40年代。地點:美國新奧爾良。
文字在https://archive.org/details/in.ernet.dli.2015.86608 https://archive.org/details/twentyfivemodern001705mbp
布蘭奇·杜波依斯來到她已婚妹妹斯特拉·科瓦爾斯基的家中,說她失去了他們的祖傳房屋,因為抵押貸款,而且無處可去。斯特拉的丈夫斯坦利懷疑他的嫂子的說法,並承諾會調查。布蘭奇在撲克遊戲中遇到了斯坦利的一個單身朋友米奇,他們互相同情。在晚上,當女人們聽音樂時,醉醺醺的斯坦利把收音機扔到了街上,還打了他的妻子,她先是在一個鄰居那裡尋求庇護,然後,讓布蘭奇驚訝的是,又回到了他身邊。他發現布蘭奇是勞雷爾鎮的火烈鳥酒店的常客,一個妓院,他與布蘭奇對質,但隨後假裝相信他的告密者一定是弄錯了。布蘭奇獨自一人在公寓裡,她讓一個為報紙收錢的年輕人進來,並與他調情。儘管發生了這段插曲,但她和米奇還是彼此喜歡。她告訴他她年輕時的故事,當時她嫁給了一個男人,卻發現他是一個同性戀。他自殺身亡,她對這件事感到內疚。米奇需要一個人,因為他的心愛的母親快要死了,他再也沒有其他人了。在布蘭奇的生日那天,斯坦利告訴斯特拉她妹妹在勞雷爾的放蕩行為。斯特拉稱她只是“輕浮”並把男人們的行為歸咎於她的行為。斯坦利毫不氣餒,送給了布蘭奇一張單程車票作為生日禮物。從斯坦利那裡得知了布蘭奇的虛假陳述後,米奇一開始沒有出現在她的派對上。當米奇終於到達時,他試圖與她睡覺,這是他“整個夏天都在想念的東西”,但他粗暴的行為讓她哭喊,直到他離開。當他的妻子在醫院的病床上準備分娩時,斯坦利友善地與布蘭奇聊天,但隨後他的真實意圖變得清晰起來,因為他穿著絲綢睡衣走向她,把她帶到床上。科瓦爾斯基一家知道布蘭奇無處可去,便向精神病院通報了她的困境。一位醫生和一位護士趕來把她帶走。她迷茫無措,懇求同情。“我一直依靠陌生人的善良,”她在被帶走的時候斷言。斯特拉懷疑斯坦利強姦了她的妹妹,但她仍然選擇繼續和她的丈夫生活,而不是她的妹妹。
“夏日煙雲”
[edit | edit source]時間:1910-1920年代。地點:美國榮耀之丘。
文字在https://pdfcoffee.com/summer-and-smoke-by-tennessee-williams-pdf-free.html
艾爾瑪試圖吸引她的鄰居約翰,一個英俊的醫師,他剛從一所著名的大學畢業。她被她精神失常的母親嘲笑,她的母親在她面前跳舞並吟唱:“艾爾瑪戀愛了,戀愛了。”艾爾瑪設法讓約翰去一家文化俱樂部,但他只在俱樂部裡待了一會兒。由於難以入睡,她在凌晨兩點諮詢了約翰的父親布坎南醫生,但約翰阻止了她去看他,診斷她主要的問題是孤獨。有一天,這兩個朋友出去,靠近一家賭場,在那裡他建議他們兩人去一個出租的房間裡休息。但這個建議冒犯了她。“什麼讓你覺得我可能同意這樣的建議?”她冷冷地問道。她聽到一個傳言,說約翰打算娶賭場老闆的女兒羅莎·岡薩雷斯,因為他輸了很多錢,這是他恢復損失的唯一途徑。一個絕望的艾爾瑪打電話給布坎南醫生,警告他他兒子的意圖。結果,布坎南命令羅莎和她的父親離開他的房子,並侮辱了他們。岡薩雷斯失去控制,怒火中燒,開槍打死了他。艾爾瑪被內疚感折磨著,她向約翰承認,是她打的那通電話。雖然約翰認識到艾爾瑪愛他,但他還是拒絕了她,並指出在她看來,她“只不過是一些過時的觀念、態度和姿態”。他離開小鎮去從事醫學研究,並取得了重大發現。在他回來的時候,他與艾爾瑪的一名音樂學生內莉訂婚了。內莉感謝艾爾瑪,因為她未來的丈夫透露了她對他的有利影響。艾爾瑪再次找到了約翰,現在她願意體驗生活中的肉慾,因為她被提醒了,她曾經拒絕了他。“但我現在改變主意了,”她說,“或者說那個說‘不’的女孩已經不在了,她去年夏天就死了——被她內心燃燒的東西悶死了。” 但已經太遲了。當艾爾瑪接受了他的想法時,他也接受了她的想法。在一個冬天的公園裡,她主動與一個陌生人交談,他們一起走向賭場。
亞瑟·米勒
[edit | edit source]
亞瑟·米勒(1915-2005)憑藉《推銷員之死》(1949年)和《坩堝》(1952年)聲名鵲起。
要理解一部 1940 年代的戲劇,我們必須記住,“推銷員之死”的背景設定在一個“沒有工作保障、健康福利或退休金”的社會(Featherstone,2008 年,第 230 頁)。“推銷員之死”構思為一部表現主義戲劇……該劇的視角將從威利的內心出發 [當他回憶過去時](Gottfried,2003 年,第 122 頁)。威利可以被視為“金錢是美德的回報”這一觀念的受害者,正如牧師霍雷肖·阿爾傑(1832-1899)所表達的,他是新教倫理的焦點,以及“財富對文明發展至關重要”這一觀念,正如散文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1803-1882)所表達的。“在阿爾傑…成功的關鍵不是天才或高貴的出身,而是品格,使普通人能夠在這個生命和下一個生命中取得成功,以及如果他傳遞他的價值觀,他的孩子的生命也能取得成功。重要的是推銷員,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紐帶,必須受到歡迎,因為他必須銷售自己以及他的產品。他一直相信金融成功意識形態,他自殺是為了讓比夫有機會成功”(Porter,1969 年,第 130 頁)。“洛曼一直無法瞭解到,商業道德,他的工作社群的道德,與他認為仍然有效的傳統相矛盾:榮譽的個人倫理,一個基本上仁慈的社會和家庭的家長式本質,以及鄰里關係”(Mottram,1967 年,第 134 頁)。該劇的力量“繼續斷斷續續地抓住我們:一個賣東西但不製造東西的人,為其他東西付費卻並不真正擁有它們,他是商業社會中受到侮辱的產物,為了在陷入黑暗之前獲得一絲真實性而掙扎。並且在沒有真正的惡棍的情況下進行戰鬥。威利的老闆霍華德在解僱或退休威利以示其糟糕的表現時最接近那個角色,但霍華德的失敗不是冷酷無情;而是缺乏理解”(Cardullo,2016 年,第 163 頁)。“從他那困擾著他的大腦中不斷出現的相互衝突的成功形象中,威利產生了成為富人和成為被愛者的雙重野心。正如他對本說過的,‘這個國家的奇蹟在於一個人可以以被喜歡為基礎而擁有鑽石。’威利對個人魅力作為成功方式的魔力充滿信心,這使他超越了因果關係,達到了必然性;他認為成功不可避免地降臨在擁有正確微笑的人身上……威利‘經常將標籤與現實混淆。在他與兒子比夫的最後一場戲中,威利哭喊著:‘我不是一個廉價貨……’這種喊叫的強度和悲痛之處在於,威利仍然認為這個名字應該意味著什麼。它在劇中很有效,因為我們已經聽到他暗示沙袋很好,因為他這樣說:‘它有吉恩·圖尼的名字在上面。’”(Weales,1967a 年,第 87-88 頁)。威利“不僅以人們對他的看法來看待這個世界,而且以他兒子對他的看法來看待這個世界。他不僅渴望得到他兒子們的尊重,特別是未能如願的比夫,而且希望他們喜歡他。在他的世界觀中,受歡迎是最有價值的商品,它會導致自尊以及經濟和社會優勢。威利將受歡迎與自尊聯絡起來,在與比夫的交流中變得清晰,這導致了父親的自殺。在經歷了一天試圖確保他們未來經濟保障的失敗嘗試後,比夫向他的父親大發雷霆,關於偽裝和‘熱氣’如何彌補了真正的成功和真實的品格。‘我不是我的領導者,威利,你也不是,’比夫著名的評論道。‘你永遠只是一個努力工作的鼓手,像其他所有人一樣被扔進了垃圾桶。’(Robinson,2018 年,第 190 頁)。“威利·洛曼的親身經歷證明了……成功是……沒有保證給那些受歡迎的人,甚至沒有保證給那些努力工作的人……儘管他越來越意識到他不想要這個世界所稱的成功,但比夫只能稱呼自己是一個毫無價值的失敗者,因為他沒有實現它”(Berkowitz,1992 年,第 80 頁)。金錢作為美德的回報有時被稱為“威利的法則”。Driver(1966 年)抱怨說,威利的法則沒有被另一個代表某種“愛的法則”的角色所抵消(第 111 頁),因為比夫在試圖讓他的父親理解他的法則是錯誤的,而不是向他展示一個新的法則。同樣,伯納德對威利只有負面的建議:‘但有時,威利,一個男人最好離開。’洛曼…永遠不知道自己是誰。利爾知道”(Kitchin,1966 年,第 79 頁)。馮·斯澤利斯基(1971 年)批評了現代悲劇嘗試中與文藝復興時期相比微不足道的雄心和目標,諷刺地評論說,“‘無法離開’是米勒對悲劇的理解”(第 173 頁)。此外,在斯塔姆布斯基(1968 年)看來,威利·洛曼作為一個亞里士多德式的悲劇人物失敗了,因為他的情感地位低於所需地位,並且因為他不像比夫那樣喊出自己是“一個廉價貨”,他從未認識到自己的缺陷,將生活中的成功等同於獲得金錢的成功,並將同齡人中的受歡迎程度視為比親密關係的豐富性更重要(第 100 頁)。弗裡德曼(1971 年)同意洛曼從未發現他的缺陷是什麼。“威利·洛曼想要的只是中產階級的成功典範:抵押還清,汽車沒有債務,一臺正常工作的現代冰箱,偶爾的情婦,‘受歡迎’的兒子,即使他們沒有受過教育,漫無目的”(第 45 頁)。“推銷員之死”是“悲情和諷刺的完美融合……這部劇是非悲劇性的……僅僅是因為威利·洛曼缺乏悲劇必不可少的要素,即兇猛,以及因為他驅使的幻覺是我們不尊重的……他將成功等同於歡呼的人群……我們至少假裝蔑視。威利·洛曼喚起了同情……但他無法喚起恐懼”(Gascoigne,1970 年,第 177 頁)。其他評論家不同意。“威利·洛曼透過他豐富的承受痛苦的能力使自己成為某種悲劇英雄。他斷言一種悲劇性的或半悲劇性的尊嚴,他對自己受到的輕蔑充滿了憤怒,以及他對尊重的渴望,以及對自尊的渴望。他拒絕放棄對他的兒子們取得勝利的一切期望,從而要求獲得悲劇性的強度……米勒無法做到的一件事……就是賦予威利一顆有趣的心靈……以及相關的語言限制……這讓我思考使用“低階悲劇”這樣的詞語”(Gassner,1960 年,第 63-64 頁)。“基本啟迪必須是針對觀眾的,無論悲劇性人物是否為自己實現了它”(Gassner,1954b 年,第 74 頁)。“威利對工作的態度損害了他自我認知的能力……威利賣的是什麼從來沒有說過,所以他可以代表所有推銷員。對他來說,受歡迎是如此關鍵,以至於他不僅銷售產品,而且銷售他的靈魂。當房子已經付清了,而他只需要‘少許薪水’時,琳達對丈夫的自殺感到困惑;那是因為他屈服於工作壓力,這讓他成為一個失敗者。儘管威利希望他的兒子們效仿本的成功,但他卻舉棋不定,不確定如何教他的兒子們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在本的訪問期間,他們被發現與威利同意從建築工地偷木材”(Greenfield,1982 年,第 79、102-111、233-234 頁)。“威利關於美國偉大的愛國主義言論與他偶爾因對在他一生中苦苦追求並定義他生活的那些事物的固有冗餘而感到沮喪的憤怒相矛盾。然後是人類的冗餘,即個人對商業成功的渴望作為最高目標,與系統隨時準備吐出不再為全能的利潤動機服務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相矛盾。最重要的是,這部劇堅持認為,對如此定義的成功倫理的承諾掩蓋並顛覆了愛的基本價值,無論是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愛,還是在更大範圍內,作為一種真正的社會關聯感。儘管米勒讓威利至少部分認識到兒子比夫對他的愛,儘管發生了所有的事情,但這部劇以一種悲劇性的諷刺而結束,他只能想到透過將他對金融成功的承諾推進到荒謬的極端來促進他為他們實現的夢想,自殺是為了讓他的家人能夠索取保險金”(Crow,2015 年,第 172 頁)。這部劇“是集中諷刺和控制憤怒的傑作……固執的比夫以米勒最好的方式表達了他的叛逆,更多地是出於對父親不忠行為的厭惡,而不是出於對他的教誨的任何理性反對。沒有比對那個普遍的偶像,美國母親,的誹謗更能喚醒這個角色,使他擺脫精神上的昏睡”(Kitchin,1960 年,第 62 頁)。“威利有一個支援他的妻子,她讓丈夫的自我欺騙成為可能。她是一個愛著丈夫併為丈夫奉獻自己的女人,即使犧牲自己的個人尊嚴,她是滋養的母親妻子,沒有她,無論是家庭中的任何一方都無法生存……琳達用鼓勵的話語和讚美來加強威利,無論何時他的精神變得低落,她都會讓他的精神振作起來。當威利的佣金不像過去幾年那樣多時,琳達讓他假裝他賺的比實際更多,並稱贊他的成就。當威利告訴她他如何失去理智,在那個男人叫他海象時打了一個推銷員的臉時,琳達沒有責備他的行為,而是告訴他,對她來說,他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男人。當威利一直把車開出道路,儘管她知道他想要死亡,但她試圖為他的行為辯解,暗示他需要檢查眼睛或好好休息。即使琳達在閣樓裡發現橡膠軟管,藏在管道下面,為威利不能忍受的那一天準備著,忠誠的妻子既不面對他也不移開軟管,知道威利依賴她認為他的力量不會動搖”(Schlueter 和 Flanagan,1987 年,第 57-66 頁)。霍布森(1953 年)不同意批評者對該劇的普通言語的抱怨,他指出了最後一幕,當時困惑的琳達說她死去的丈夫“他只需要少許薪水”。“沒有人需要少許薪水,”查理回答道。“他是一個在那裡藍色天空中的男人,依靠微笑和擦鞋。當他們開始不回來的時候,那就是地震。”霍布森發現這種節奏“動人而真實”,對於查理關於人不能只靠麵包為生主題的評論,他寫道:“我從未在美國戲劇中聽到過如此明智、說得好或值得說的話”,以及琳達“觸及了悲傷的深處,達到了超越皇室和紫色言語的皇室高度”(Hobson,1948 年,第 122-123 頁)。“在威利·洛曼在他的腦海中創造的田園詩般的世界中,沒有真正的地方可以容納女性,恰恰是因為這是他父親和祖父的 19 世紀世界。因此,女性的附屬地位與其說是米勒能力不足的產物,不如說是對一個檢驗威利對現實理解不完善的戲劇的需要”(Bigsby,1985 年,第 421 頁)。“推銷員之死”“本來會是對制度的攻擊,而且是一個令人信服的攻擊——如果米勒先生選擇扭轉局面,讓查理成為中心人物,而伯納德成為失敗者”(Gardner,1965 年,第 125 頁)。
關於奇蹟和迷信,培根在《學術的進展》(1605) 中寫道:“我並不認為應該完全排除對奇蹟的記載,以及對巫術、魔法、夢境、占卜等迷信敘述的記載,只要事實有保證和明確的證據。因為尚不清楚在哪些情況下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歸因於迷信的效應參與了自然原因:因此,無論如何,對這類事情的實踐要予以譴責,但從它們的推測和思考中可以獲得啟示,不僅可以識別罪行,而且可以進一步揭示自然”(1957 年版,第 36 頁)。“熔爐” “是根據 1692 年馬薩諸塞州塞勒姆臭名昭著的巫術審判自由改編的,當時 19 名正直的公民因與魔鬼交易而被絞死,無數其他人被監禁,這場恐慌是由歇斯底里的年輕女孩引發的,她們作證說自己被鄰居的撒旦影響所控制……就純粹的殘忍和愚蠢而言,塞勒姆巫術審判必須躋身於明顯文明中最可恥的景象之列。米勒的強項在於他賦予了這些材料戲劇性的形式,並透過選擇三個關鍵人物(其中兩個是他虛構的,一個是邪惡的女孩阿比蓋爾·威廉姆斯——歷史人物)點燃了我們對主題和個人心理的興趣……驅魔、復興主義的歇斯底里、假裝被附身和盲目正義的混合,結合在一起,加劇了個人恩怨和公眾狂熱,編劇以精湛的技巧展現了這一切……語言具有聖經式的隱喻風格,生動地反映了那個時代;儘管劇本最後,與普羅克特的認罪,與《聖女貞德》非常接近,使我們意識到它的主要缺陷——蕭伯納對更廣泛問題的智力把握——但它的戲劇性影響,僅在此處失敗,已經產生並以不懈的力量維持”(威廉姆森,1956 年,第 54-55 頁)。歷史與劇本之間的差異包括兩個角色年齡的變化。“真正的阿比蓋爾·威廉姆斯當時 11 歲,約翰·普羅克特 60 多歲。米勒決定讓她 17 歲,普羅克特 30 歲左右”(戈特弗裡德,2003 年,第 199 頁),以引入她與他的浪漫元素,以及他對與她通姦的愧疚元素。“行動的激烈敘事快感取決於米勒對那個時代對話的精通。‘語言是過去和現在口語的豐富而適合舞臺的混合,暗示……在 17 世紀馬薩諸塞州的清教徒英語”(戈特弗裡德,2003 年,第 224 頁)。散文是扭曲的,像一塊拋光的橡木棍一樣光彩照人,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戲劇武器”(泰南,1961 年,第 254 頁)。“熔爐” 建立在斷言和否認、陳述和撤回的節奏之上。因此,瑪麗·沃倫先是控告者,然後承認真相,然後又撤回她的認罪。哈利牧師起初是激烈的檢察官,後來又成為絕望的辯護人。伊麗莎白·普羅克特起初私下堅持她丈夫的道德罪責,後來公開宣稱他的誠實;吉爾斯先是控告他的妻子,然後又撤回指控;普羅克特先是簽署了認罪書,然後又撕毀了它”(比格斯比,1984 年,第 198 頁)。“哈利如此害怕被認為不夠虔誠,以至於他躲在書後面,而不是毫不猶豫地宣稱他真正相信的東西。丹福斯如此害怕被認為對被告不夠報復,以至於他躲在長袍後面,而不是要求控告者提供實質性證據。帕特南如此害怕被認為不夠富裕,以至於他陰謀竊取不屬於他的東西。伊麗莎白如此害怕激情,以至於她躲在她的批判性的冷淡背後,同時假裝說她不能評判,這僅僅意味著她不能愛。真正是她害怕愛‘會凍結啤酒’。‘熔爐’ 是一部戲劇,戲劇化地展現了當人類迷失方向時產生的恐懼表現,因為他們失去了彼此”(利夫塞,2012 年,第 12 頁)。“最初提供美國主要氣質的清教徒,這種氣質延續至今,確立了經濟和宗教民主的原則。但政治異議的適當氛圍(在英國如此顯著)和道德自由的氛圍(美國因此而既羨慕又譴責法國)在開始時是缺失的”(戈德斯通,1969 年,第 19 頁)。“劇中的人物,包括牧師、臨時法庭的法官和巫術方面的權威人士,都致力於壓制和維護塞勒姆的神權統治”(羅賓遜,2018 年,第 194 頁)。“清教徒神權統治和行政當局的既得利益……由懷恨在心、扭曲或心胸狹隘的人代表:好爭吵的帕里斯……哈利牧師……他為緩和局勢做出的努力……被他自己的搖擺不定而挫敗……易受欺騙的丹福斯州長……在他主持特別法庭的行為中笨手笨腳,威廉·哈索恩法官,為良心問題和清教徒對所有反對意見的壓制而擔憂”(赫倫,1969 年,第 34 頁)。“與那些過早妥協的人形成對比,與拒絕妥協的麗貝卡·納斯並列,普羅克特成為少數幾個經歷了熔爐考驗而倖存的人之一,儘管他為此付出了生命”(施盧特和弗拉納根,1987 年,第 69 頁)。“普羅克特拒絕屈服於那些認定他與魔鬼有染的人。儘管他在臨死之前簽署了認罪書,後來又撤回,但他拒絕說出名字,最終,他將自己的名字的榮譽視為自己的最高價值。相比之下,社群中被指控的其他人被說服認罪是唯一的救贖希望,他們輪流承認共謀並指認他人”(施盧特,2000 年,第 303 頁)。“阿比蓋爾受對普羅克特的報復和害怕因跳舞而受到懲罰的驅使。為了實現她的目標,她願意讓城裡的人被殺,並‘顛覆法律的功能’……‘帕特南一家受貪婪的驅使,帕里斯和奇弗受權力的驅使。丹福斯最終面臨困境。12 人被處決……赦免其他人就等於承認司法錯誤,因此他為了更大的利益犧牲了他們,因為附近的一個城鎮正在發生叛亂,混亂威脅著神權統治”(波特,1969 年,第 188-195 頁)。“‘熔爐’ 在普羅克特的悲慘困境的個人層面上達到了頂峰,但……社會和個人緊密交織在一起……米勒採用了易卜生的片段揭示方法,在整部劇中逐漸補充過去細節”(加斯科因,1970 年,第 179-180 頁)。“‘熔爐’ 的最佳版本不會將其角色劃分為觀眾認同的英雄‘我們’和邪惡的‘他們’。我們必須感覺到,我們都有可能成為‘他們’中的一員。米勒的每一部戲都浸透了罪惡感,這種罪惡感玷汙了每一個角色;他們都發生在‘墮落之後’。普羅克特痛苦地知道,他的一次婚外情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激發了塞勒姆發生的恐怖事件。就在他被處決之前,他考慮認罪,以保住性命……在我理想的‘熔爐’ 中,觀眾不會離開劇院,只認同普羅克特。我們的一部分必須知道,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很可能也會像帕里斯、阿比蓋爾,甚至是一個假設的普羅克特一樣,他在最後一刻選擇了森林裡另一條更安全的道路”(布蘭特利,2012 年,第 2-3 頁)。“約翰·普羅克特是一個完美的角色,因為他知道自己並不完美。這就是我們對他感興趣的原因,他帶著所有的缺點走向絞刑架。在整部劇中,普羅克特開始明白,生活可以不完美,可以犯罪,但仍然擁有善良。他的救贖在於絞索的收緊和繩索的斷裂”(馬裡諾,2012 年,第 13 頁)。“與喬·凱勒和威利·洛曼不同,普羅克特最終關心的不僅僅是他自己的尊嚴。他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也為了維護其他所有清教徒法庭殘酷虛偽的無辜受害者的尊嚴而死。這賦予他的悲劇比米勒早期戲劇中英雄的衰落更廣闊的維度”(馬裡諾,2018 年,第 94 頁)。“‘熔爐’ 以及它對導致、允許和維持政治邪惡的無知發出的有力譴責,是正義的引擎”(戈特弗裡德,2003 年,第 225 頁)。“有趣的是,在處決 20 年後,政府承認發生了司法錯誤,並對仍在世的受害者進行了賠償……[最值得] 稱讚的是米勒信念的廣度,他信仰的力量和主題的緊迫性”(朗姆利,1967 年,第 195 頁)。
"推銷員之死"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40 年代。地點:美國。
文字見 https://archive.org/details/in.ernet.dli.2015.86608 https://archive.org/details/dli.ernet.505675 https://archive.org/details/twentyfivemodern001705mbp http://www.pelister.org/literature/ArthurMiller
在一次令人失望的推銷員商務旅行後,感覺自己老了的威利·洛曼回到了家,他的妻子琳達建議他應該請求老闆讓他在本地工作。他同意了。儘管他們的兒子比夫和哈皮在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了希望,但在威利看來,他們還沒有在經濟上取得成功,而這在威利看來是至關重要的。反過來,他們的兒子也擔心他們父親的精神狀況。他經常自言自語,並且表現出可能存在自殺想法的跡象。當威利指責他的兒子們無所事事時,他們告訴他比夫即將獲得一個有利可圖的商業機會。威利不僅無法說服他的老闆讓他在總部工作,而且還丟掉了工作,這一切都是三十多年前第一個僱傭他的那個人的兒子一手造成的。與此同時,比夫也無法從一位 supposed friend那裡得到一份工作。在沮喪之下,他偷走了那人的昂貴鋼筆。威利遇到了比夫的童年朋友伯納德,伯納德告訴他,比夫在年輕時去波士頓後就再也不一樣了。威利知道為什麼。就是在那裡,他失意的兒子在一家酒店裡看到他與一位陌生的女人在一起。在經歷了一天折磨之後,威利在一家餐館裡遇到了他的兒子們,想聽聽訊息,也許慶祝一下。他們不願意聽到任何關於比夫的壞訊息,兄弟倆感到被迫對比夫的成功撒謊。當威利在餐廳洗手間洗漱時,比夫突然離開了,他的兄弟也離開了,去追求兩個不知名女人的吸引力。琳達在得知她兒子在餐廳的行為後,憤怒地指責她的兒子們無情。當一個沮喪的威利得知關於比夫被拒絕的真相時,他指責比夫是出於惡意而失敗的。比夫憤怒地向他展示了威利之前自殺時使用的電線,問他是否是為了博取同情。威利假裝不知道。比夫透露他因盜竊罪入獄幾個月,並因此失去了其他工作,這是因為他無法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因為他的父親總是誇大自己的重要性。“我是一個不值錢的人,你也是,”他喊道。“我是威利·洛曼,你是比夫·洛曼,”威利反駁道,他仍然相信,既然他是洛曼,他必然會成功。他意識到自己精神狀況的不斷惡化,但他仍然開車離開,發生了一起致命的交通事故,這是他為了家庭的福祉而做出的自殺式犧牲。在葬禮上,比夫拒絕接受人壽保險金來創業,但哈皮決定他會追隨他父親的願望。
“坩堝”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690年代。地點:馬薩諸塞州塞勒姆。
文字:https://archive.org/details/TheCrucible https://archive.org/details/dli.ernet.505675 https://pdfcoffee.com/the-crucible-pdf-free.html
帕里斯牧師的女兒貝蒂,在他發現她和朋友們在森林裡跳舞后,一直躺在床上沒有反應。她害怕懲罰,而他害怕他的敵人會利用這件事把他拉下臺,如果女孩們召喚了靈魂。他詢問他的侄女阿比蓋爾關於這件事,阿比蓋爾只承認跳舞。但托馬斯和安·普特南確信這裡存在巫術,因為他們的女兒露絲患有與貝蒂一樣的病。“那是死亡,你知道,那是死亡被逼到他們身上,用叉子和蹄子,”安說道。她確信一個黑奴提圖巴與死者交談,以找出是誰謀殺了她在分娩時死去的七個嬰兒。海爾牧師從外地趕來調查關於巫術的傳聞。阿比蓋爾抓住這個機會指控提圖巴施法。在持續的調查中,吉爾斯·科裡透露他的妻子晚上讀書。“我不是說她接觸了魔鬼,但我真的很想知道她讀了什麼書,以及為什麼她把書藏起來,”他說道。調查越深入,嫌疑人的人數就越多。約翰和伊麗莎白·普羅克特從他們的女僕瑪麗那裡得知,有34名婦女被捕,至少一名男子奧斯本被判處絞刑,指控者是他的女僕,她在向奧斯本乞討麵包時被拒絕了。由於不聽話地離開房子,約翰舉起手要抽打瑪麗。為了保護自己,她大聲喊叫說,她是在被他們以前的女僕阿比蓋爾指控後,從阿比蓋爾的指控中拯救了她的妻子,因為,根據伊麗莎白的描述,阿比蓋爾希望取代她的位置成為約翰的妻子。更多的官員趕到,伊麗莎白最終被指控犯有巫術,因為在她房間裡發現了一個裝著針的玩偶,而阿比蓋爾當晚的肚子就被針紮了一下。在塞勒姆法院,科裡在副總督丹佛斯面前為自己辯護,為被控巫術的妻子辯護,這與他的初衷大相徑庭,因為他只是想找到他妻子讀書的原因。科裡、約翰和弗朗西斯·納斯,這三個人,他們的妻子都被指控犯有巫術,根據瑪麗的供詞,指控阿比蓋爾、貝蒂、露絲和其他人都犯有欺詐罪。帕里斯立即不相信瑪麗的說法,因為他害怕他的女兒和自己會發生什麼。儘管海爾已經簽署了72份死刑令,但他還是緊張地希望認真審查這一指控,但丹佛斯拒絕了,因此瑪麗的說法不被相信。當丹佛斯審查伊麗莎白的案子時,普羅克特夫婦自相矛盾,他承認與阿比蓋爾發生了性關係,她為了維護他的名譽,發誓他沒有。結果,她被判處死刑。一個陷入困境的瑪麗現在指著約翰說他是“魔鬼的人”,並加入她的朋友們,繼續大聲指控。後來,丹佛斯得知阿比蓋爾和默西·劉易斯搶劫了帕里斯,並乘坐一艘船從該地區逃跑了,深感不安。十二名女巫已經被絞死了,部分原因是根據他們的指控,但他決定繼續進行審訊。由於伊麗莎白懷孕了,她的判決被推遲了。她懇求她的丈夫承認他使用了巫術,但他拒絕了,被絞死了。
威廉·英吉
[edit | edit source]
除了米勒之外,威廉·英吉(1913-1973)的戲劇中也突出了間接的社會評論,尤其是“樓梯頂端的黑暗”(1957)。英吉還寫了“回來吧,小謝巴”(1950)和“野餐”(1953)。前者“揭示了對平凡生活的洞察力,以及將其轉化為令人消耗的悲劇的能力。該劇講述了一個出身名門望族的男子在婚姻中的失敗感,以及他在重新陷入悔恨的沉默之前爆發性的酗酒”(加斯納,1954a,第740頁)。
“樓梯頂端的黑暗” “讓一個年輕的家庭找到自己的方式,經歷各種情感危機,沒有戰勝任何困難,但卻在經歷所有困難之後倖存下來,這得益於他們對彼此依賴的承認”(伯科維茨,1997,第183頁)。“該劇的重點分化,[魯賓-科拉的衝突和薩米的自殺]讓一些評論家感到不安和分心……薩米的自殺讓科拉和瑞妮對生活的意義有了新的理解,也對她們自己有了更深的理解。當然,自殺是科拉和魯賓重聚的主要誘因……魯賓……害怕黑暗,因為它代表了在他面前伸展的不確定的未來。但就像科拉在第二幕結束時,陪著桑尼上樓去消除他對黑暗的恐懼一樣,她也在第三幕的幕布落下時,陪著魯賓上樓去消除他對黑暗未來的恐懼……魯賓離開科拉,因為他不想像他被妻子管束的姐夫莫里斯一樣。當他回到她身邊時,很明顯,他將會被馴服,就像莫里斯被馴服一樣。一夜夫妻,既不會改變弗洛茲夫婦婚姻的總體徒勞,也不會解決造成魯賓不安全感的那些問題……即使在劇本的最後,魯賓也無法與他的兒子交流……瑞妮與威廉姆斯在《玻璃動物園》(1945年)中的勞拉·溫菲爾德很像……瑞妮的羞怯間接導致了薩米自殺……[之後],瑞妮第一次不是將音樂作為一種逃避自己的方式,而是作為一種給別人帶來快樂的方式……薩米在第三幕的前半部分佔據主導地位,即使他已經死了”(舒曼,1989,第53-63頁)。
“在劇本結束時,家庭所有的恐懼,如孤立、聯絡、貧困和失去尊重,都變得可以管理,因為科拉走上樓梯去見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們開心地一起去看電影。透過愛和誠實,這個家庭以更積極的方式重新聯絡起來,而那些不在這個家庭圈子內的人,洛蒂、莫里斯和薩米,最終走向黑暗,因為洛蒂和莫里斯婚姻的膚淺性被揭露,薩米自殺。一旦他們放棄了瑣碎的分歧,弗洛德家的基礎就是愛,而這才是最重要的...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使這部劇本具有 1950 年代的特徵,包括一些笑話和對精神病學的引用,以及科拉的建議,孩子們不會以某種神奇的方式忘記事情。這些困擾有時會伴隨著孩子們,並在他們長大後影響他們的生活。此外,裡妮的校友弗利特關於她與父親意見分歧的評論,反映了那個年代不斷擴大的文化代溝...裡妮可能害羞,但她並不愚蠢。她知道弗利特只是在利用她,她對與薩米一起出去的疑慮並非因為他是個猶太人,而是因為她會對任何人都感到不舒服。雖然她可以理解地發現她脾氣暴躁的弟弟很煩人,但她卻是一個敏感的靈魂,愛著自己的家人。她擔心裙子的花費,也擔心父母吵架。裡妮和桑尼都與更廣泛的社會保持距離,但裡妮覺得這很嚇人,而桑尼似乎只是覺得這很令人厭惡,除了他理想化的電影明星...科拉比她丈夫更有教養,出身於富裕家庭,但她愛他。然而,她的愛可能對這個家庭所有人來說都窒息,因為它表現為一種對丈夫的貶低式的嫉妒,她試影像她欺負孩子一樣欺負他,當她不使用她使人無能為力的保護性來反對他們時。她嫉妒她更富有的朋友,這導致了她婚姻的破裂,但我們應該原諒她,因為她從小就被嬌慣,她的丈夫對她不夠坦誠,一旦他坦誠了,她便毫不抱怨地接受了現狀。儘管她最初對自己的家人不寬容,但在最後,她是這部劇本中最能體現包容性的人”(Abbotson,2018b pp 120-122)。
“在《樓梯頂端的黑暗》的第一幕中,“夫妻之間毫無根據的爭吵導致丈夫離家出走。緊張局勢源於丈夫無法向妻子表達自己的焦慮,以及妻子未能意識到這個表面上自信的男人對未來的恐懼...這部劇本有時偏向喜劇,有時偏向悲劇,在語氣上不一致...劇本的最後一幕,揮金如土的笨蛋把他的妻子召喚到樓上的床上,同時把孩子們趕出家門,我覺得這很生硬,很不和諧地喜劇。在目睹了孩子們遭受的苦難,以及經歷了上一幕的半明半暗的氛圍之後,我對喜劇已經沒有胃口了”(Gassner,1960 p 171)。
“事實上,正是科拉對孩子的興趣,以犧牲她與魯賓的關係為代價,導致了魯賓離開家。關於裡妮參加聚會服裝的爭吵,只是他們更深層次的婚姻問題的表現形式,而這些問題最終因科拉粉碎了桑尼對她依戀而得到解決,並且她把孩子們送到電影院,這樣她和魯賓就可以不受打擾地做愛。此外,到劇本結束時,孩子們之間的競爭減少了,可以推測桑尼也能夠克服他對父親的嫉妒。裡妮一直和魯賓最親近,因此她不喜歡桑尼的部分原因是這個男孩對父母永久分離的前景毫不掩飾地感到高興。桑尼自私地為他的競爭對手消失了而感到高興,因此,他可能會搬到一個新的城鎮,遠離他所在社群那些嘲笑他的男孩。當然,他的妹妹則完全相反...而科拉,在她的恐懼和擔心之中,沒有向那個年齡更大、可能更能理解局勢動態的女兒尋求幫助,而是向那個愛意像動物一樣強烈、毫無保留的孩子尋求幫助”(Mitchell,1978 pp 302-303)。
“洛蒂...努力地表現得外向,莫里斯·萊西,她敏感的丈夫,是一位牙醫,他帶著一種認命的沉重感,就像一個溫順而沮喪的男人回顧他的單身生活...薩米...一位猶太學員...既遭受過偏見,又缺乏父母的關愛...他們都害怕樓梯頂端的黑暗...一部感人、有洞察力、引人注目的戲劇,講述了 20 世紀 20 年代的變化時代對美國西南部城鎮居民的影響”(Herron,1969 pp 434-435)。“許多評論家認為[洛蒂]是一個可憐的生物,困在一個沒有孩子的婚姻中,她的丈夫毫無熱情...她的粗俗、偏執和自以為是,都是一種保護性人格的表現,類似於[1953 年《野餐》中的]羅絲瑪麗,她忙於保護自己免受必須創造身份的本質焦慮,而不是讓別人為她決定她的性格。洛蒂向科拉展示了一個自我,向莫里斯展示另一個自我,兩者相互矛盾。她比關心自己的缺點更關心別人的感受,讓科拉相信她嫉妒她那個毆打妻子、通姦的丈夫和她被寵壞的、脾氣暴躁的孩子,同時對莫里斯的情緒保持敏感,並讓他對她坦誠相待...[在劇本的結尾],沒有浪漫的頓悟的跡象,只有一位推銷員在兜售一個改進版的自己,以及一位願意忍受毆打和不忠的妻子,她為了穩定的擠壓和至少表面上穩定的家庭權威而忍受這一切”(Johnson,2005 pp 80-82)。布魯斯廷(1965)反感妻子的馴服男人:“在英格對家庭愛的頌歌之下,潛藏著這樣一種心理暗示,即婚姻需要英雄形象(也就是美國民間形象)的男性氣質的犧牲,以此來換取情感上的慰藉。他必須放棄他的侵略性、他的放蕩、他的勇敢、他對軟弱美德的蔑視,以及他對自己的身體和成就的自戀的驕傲,並承認自己迷路了,需要幫助。女人的工作是把這些叛逆者變成家養的動物。如果這需要(就像英格作品中總是那樣)與英雄上床,她會忍受;儘管她可能會指責她的丈夫...娶她是為了她懷孕了,但她還是設法讓英雄依賴她,從而確保他會留下來撫養家庭”(p 90)。其他評論家對結局持更積極的看法。“失去工作迫使魯賓承認他對妻子的弱點,他在一個經濟進步將他拋在身後的世界中,對妻子疏於照顧,在那裡,未來和他在其中的位置是未知的。黑暗在一定程度上象徵著對未知的恐懼。當魯賓赤裸地站在樓梯頂端...並示意科拉過來,他的赤裸表現出對脆弱的接受;現在,他毫不畏懼地向科拉展現自己的弱點和力量,他知道她會提供身體上的愛的保證,以增強他的自尊”(Adler,2007 p 166)。
“當田納西·威廉姆斯繼續描繪非傳統者悲慘的生活時,英格似乎描繪了同樣悲慘和孤獨的順從者的生活。英格展示了那些生活在主要城市地區之外的普通美國人的形象,並且透過他的肖像,他挑戰了對美國小鎮的舊的理想化形象,透過描繪這些地方充滿了挫折和限制。他的作品集中在中西部人身上,他們以前從未被認為是藝術的合適主題,但透過他們,他揭示了在一個承諾很多卻常常提供很少的國家裡生活和生存的困難”(Abbotson,2018a p 50)。“如果說在 50 年代,有一位劇作家與米勒和威廉姆斯一樣受人尊敬,不是因為他的形式創新,而是因為他對美國家庭的刻畫充滿敏感性,那麼他就是威廉·英格...在這組重要的劇本中,這些劇本在百老匯取得了不錯的成績,英格考察了一批龐大但典型的角色和關係,反覆創造出戲劇化生活細節的場景,這些生活麻木不仁,夢想因妥協而窒息,性被拒絕——這是美國小鎮生活的素材”(Schlueter,2000 p 307)。“英格最強大的描寫是女性角色,尤其是那些在性方面受到挫折,對自己的命運幾乎沒有控制權的女性。如果她們控制甚至有時削弱她們的男人,正如羅伯特·布魯斯廷(1958)所聲稱的那樣,她們這樣做是因為她們的男人需要被馴服。Jhunke(1986)反對這種刻畫,理由是很多喧鬧的男人在依附於一個女人後就會安定下來”(Shuman,1989 pp 147-148)。

時間:1920 年代。地點:美國俄克拉荷馬州。
文字見 https://pdfcoffee.com/qdownload/dark-at-the-top-of-the-stairs-inge-pdf-free.html
在成為一名旅行推銷員之前,魯賓發現他的妻子科拉給他們的女兒瑞妮買了一件他認為太貴的派對禮服。夫妻倆爭吵不休。他打了她,並威脅再也不回來。她考慮搬到她姐姐洛蒂那裡,但後者認為這種解決方案不切實際。洛蒂也有自己的麻煩,包括她與丈夫莫里斯已經三年沒有親熱,儘管承認這部分是她的錯。“我從不享受像一些女人說的那樣,”她承認道。瑞妮非常擔心要和一個陌生人薩米進行一場盲約會,以至於想到這件事就嘔吐。由於她的母親是電影演員,薩米從小就生活在軍事學校。他和瑞妮的哥哥索尼關係很好,他們一起參加了富有的拉爾森一家舉辦的派對。出門時,科拉叫兒子上樓,但他害怕黑暗,除非有人陪著他。第二天,瑞妮向她母親撒謊,說她離開派對是因為薩米去追求其他女孩了。當被問及她是否會像其他人一樣做時,她回答說薩米“不喜歡我那樣”。“我只是不像其他女孩那樣受歡迎,”她補充道。索尼興奮地衝進房間,宣佈他在茶話會上朗讀贏得了 5 美元。當他母親把錢放到他的儲錢罐裡時,他感到很生氣,說他恨她。當得知薩米自殺身亡的訊息後,全家人都驚呆了。科拉堅持讓女兒告訴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瑞妮連續三次和薩米跳舞,直到她因為沒有其他男孩邀請她跳舞而感到羞愧。“我只是不能忍受薩米認為沒有人喜歡我,”她坦白道。她把薩米介紹給這家主人的女兒,但拉爾森夫人打斷了他們的談話,大喊說她不會容忍任何猶太人跟她的女兒跳舞。魯賓回家說他失業了。他對打了妻子感到抱歉,但當她強烈建議他申請鎮上的職位而不是外出旅行時,他又變得不耐煩起來。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和好了。為了和妻子上床睡覺,魯賓給了兒子錢讓他去看電影。薩米對自己的自私行為感到羞愧,他砸碎了儲錢罐,帶妹妹去看電影。科拉在她丈夫在樓梯頂端等著她的時候,慢慢地走上去,好像她還是以前那個害羞的少女。
山姆·謝潑德
[edit | edit source]
山姆·謝潑德(1943-2017)憑藉《飢餓階級的詛咒》(1977 年)、《埋葬的孩子》(1978 年)、《愛之傻瓜》(1983 年)和《心之謊言》(1985 年)而聲名鵲起。
納什(1987)表明,《埋葬的孩子》反映了一種農業儀式,即在生命冬季殺死玉米之靈,正如詹姆斯·弗雷澤的《金枝》(1890 年)中所描述的那樣。“道奇代表了玉米之靈,他的死亡是玉米生長的必要條件。他希望自己的身體被燒燬,這與農民焚燒稻草人相似,也與生長所需的太陽相似。文斯可能代表被謀殺的兄弟安塞爾,或者代表被埋葬的孩子哈莉和蒂爾登亂倫後代的轉世。玉米田的真實狀況似乎令人懷疑。一方面,蒂爾登把玉米堆在道奇的腿上,好像是從他們田裡拿來的。另一方面,道奇和哈莉否認玉米田的生長,所以蒂爾登似乎要麼是買來的,要麼是偷來的,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索耶,2011 年,第 202-214 頁)。“只有在道奇死後,哈莉才看到玉米的生長,這表明了她精神上的盲目,因為她在道奇犯罪之前,不知何故無法看到玉米的生長。神奇的植被可以被看作是文斯從道奇那裡繼承的象徵”(馬蘭卡和達斯古普塔,1981 年,第 108 頁)。“這個家庭困擾著自己的家。從開場幕開始,佈景就暗示著是一座停屍房,年邁的道奇坐在一張破損的沙發上,裹著一條象徵性的,但仍然是俗氣的毯子,佔據著舞臺中央。36 我們似乎在地下(道奇稱自己為“一具屍體”),有一組樓梯通向無處,從沙發後面的前廊發出的幽靈般的光線與來自無所不在的電視機的閃爍藍光相呼應。雖然環境似乎,按照自然主義的傳統,是這些居住在空間中的破敗靈魂內心狀態的因果代理,但很快就會變得清晰的是,這個地方實際上是這個家庭道德狀態的外部化表現,這個家庭不是透過愛、歷史或共同的歡樂而結合在一起,而是透過一種集體罪惡而結合在一起,這種罪惡將他們束縛在一個共同的地獄裡,而道奇則是這個地獄的主宰……[文斯]猛烈地跨過家庭的門檻,用刀子割開紗門,跌跌撞撞地進入主房間。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自我誕生的形象,這個動作與之前關於謀殺和秘密埋葬孩子的對話產生了強烈的共鳴。看來,只有暴力才能確認一個人在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而文斯透過威脅強行奪取領土並控制家庭宅邸來揭示了他的遺產……人們可能會期待文斯扮演外部代理人的角色,他的到來引發了啟示的過程,而他自己可能會達到頂峰。文斯是這個家庭中唯一一個似乎事先不知道孩子黑暗秘密的人,當蒂爾登帶著孩子的遺體上樓去見哈莉時,他也看不到。文斯在試圖逃往艾奧瓦州邊境時,描述了他的家庭遺產的幻象的獨白,是整個戲劇中自我認同和家庭傳承的主要宣告,因此,如果有人能夠在家庭血統中建立新的、轉變後的秩序,那應該是他。但這種幻象以一切都消散而告終,文斯抹去了自己的出身,而不是深入到家庭神話的核心”(範登·赫維爾,2018 年,第 129-131 頁)。“文斯,未來的唯一可能性,在最後躺下了,姿勢與躺在沙發上的道奇完全一樣”(阿德勒,1987 年,第 108 頁)。“文斯安然地坐在了(現在已經死了)的祖父在家庭沙發上的位置。蒂爾登從“外面”回來,這次他抱著一個被埋葬的孩子屍體。從蒂爾登和道奇之前的供詞中,我們猜測這個孩子是文斯,是蒂爾登與母親哈莉亂倫的產物。因此,在劇本的結尾,似乎有兩個文斯,以及涉及他的兩種相互矛盾但同時發生的戲劇性行為”(西馬,1993 年,第 166 頁)。馬蘭卡和達斯古普塔批評了“不在場證明俱樂部”事件是“編造的”,而那些來炸掉家庭汽車的歹徒則是強加了“不適合該劇整體氛圍的卡通風格”(第 107 頁)。但批評家往往偏向於想要並接受從劇本的初始前提自然產生的可能事件,而現實生活中的事件有時是由不可能發生的事件組成的,這些事件不一定是過去事件的結果。謝潑德傾向於強調瘋狂作為主題:角色是瘋狂的,事件是瘋狂的,事件不一定是角色心理的反映。在這樣的戲劇中,最令人愉快的反應是坐下來思考,而不是向前傾斜,期待著事件會從角色的動機中發展出來。“當秘密的真正揭露神奇地使農場復興時,它的貧瘠土壤突然開始生產出各種各樣的蔬菜,並且數量驚人,該劇的警告很明確,對國家未來的希望只能透過無保留地接受過去,即使是可恥的過去才能實現”(伯科維茨,1997 年,第 164-166 頁)。
在《飢餓階層的詛咒》中,“儘管家庭成員聲稱不屬於飢餓階層,但他們確實如此,他們渴望身份和尊嚴。每個家庭成員不斷地開啟和關閉冰箱門。這個家庭深陷債務的詛咒,他們的家成了掠食者的獵物……在劇的結尾,母親和兒子吟誦了貓和鷹的寓言,在高空中互相抓撓……貪婪的美國已經抓住了自己的殺手”(科恩,1982 年,第 184 頁)。“這個家庭崩潰了,伸手去拿他們幾乎不需要的東西,卻對周圍人的需求視而不見”(比格斯比,1985 年,第 240 頁)。溫特斯(2017 年)批評了劇末爆炸的汽車,認為它是“諷刺的喜劇而不是悲劇”(第 206 頁)。但其他評論家認為這個場景與其他場景融為一體。“劇中一個令人吃驚的事件似乎超越了詛咒:艾瑪在汽車爆炸中喪生。謝潑德在她最後一次登臺亮相時讓她顯得相當不討人喜歡,而她前進而韋斯利後退(他有一次問她,“為什麼我後退?”)的想法很快就消失了,因為她最終死在埃默森和斯萊特的手中。在劇的結尾,那個剛開始瞭解月經的女孩已經長大到足以向她的獄卒(在她因向逍遙俱樂部開槍打穿許多洞而被捕後)進行性挑逗;[那個]曾經興高采烈地為她的 4-H 俱樂部演示繪製煎雞圖的人學會了看透每個人向世界展現的表象;[那個]想要成為一名機械師,旅行,也許還會寫作的人,偷走了她母親的錢(即使後者“偷”了她的煎雞),並決定過上犯罪生活……艾瑪在劇中的學習經歷無疑是消極的……韋斯頓和埃拉在《飢餓階層的詛咒》中的經歷也是消極的。他們長時間地躺在舞臺上,而劇中的行動在他們周圍繼續進行。韋斯頓在遠離家的一夜後喝得酩酊大醉,在第二幕中睡在了廚房桌上;埃拉在監獄裡照顧艾瑪一夜後筋疲力盡,在第三幕中睡在了同一張廚房桌上……他們在熟睡的人物周圍的喊叫和爭吵更加引人注目,因為他們都沒有醒來……他們對將對他們的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熟睡不醒”(卡杜洛,2016 年,第 114-115 頁)。“在《飢餓階層的詛咒》中,謝潑德……融入了儀式化的動作,彷彿要促使觀眾將劇中的元素與更宏大、更神話般的關注點和傳統聯絡起來。一隻羔羊,在亞伯拉罕宗教傳統和基督教中是無辜的象徵,被韋斯利在舞臺外屠宰了。當它被剝皮的屍體被搬到舞臺上時,來參觀這個家庭農場的人認為它是一隻死山羊,這明確地指的是早期希臘悲劇中的“山羊之歌”,是對劇中父親屠殺無辜的儀式化隱喻”(斯凱爾頓,2018 年,第 158 頁)。“當韋斯頓和埃拉把食物帶回家時,這就像是在恢復荒地的一次又一次的徒勞嘗試……韋斯利……並沒有超越英雄的地位……而是取代了他的父親,穿著他父親的髒衣服,被他的母親埃拉和兩個暴徒誤認為是韋斯頓……謝潑德進一步顛覆了韋斯利的重生,透過韋斯利屠殺羔羊來實現。在聖經傳說中,屠殺羔羊是為了淨化自我。然而,韋斯利屠殺羔羊並沒有幫助他或他的家人……相反,他屠殺了它,因為他餓了”(魏斯,2002 年,第 325-326 頁)。“活生生的羔羊在第一幕被搬到舞臺上,為了治療它的蛆蟲感染,最終在第三幕的開頭被韋斯頓治好了……韋斯利,最終為了食物而屠殺了羔羊,把自己投射到救世主的基督般角色中,卻發現這種救贖無法改變家庭的狀況……始終,人們都在談論潛在的個人滋養和轉變的時刻,但與謝潑德早期戲劇中潛在的轉化不同,這些時刻都被阻撓或嘲弄……第三幕有點突兀,將行動從自然主義提升到元素主義,幾乎拋棄了社會和經濟主題,幾乎完全集中在神話般的更新模式上……韋斯頓無法逃脫他自己的毒藥對韋斯利的影響,在韋斯利與他父親的最後一幕中,韋斯利站在他面前,穿著韋斯頓想象自己重生時扔掉的髒的、沾有尿液的衣服。此外,韋斯利顯然吸收了韋斯頓對男性生存的理解,認為生存與暴力和永不滿足的飢餓有關,因為他屠殺了韋斯頓聲稱他從感染中拯救了的羔羊……韋斯利承擔了暴力家長的角色,而韋斯頓微不足道的救贖和重生的嘗試未能解除家庭的詛咒。飢餓……在韋斯利隨後將冰箱裡的東西倒在地上,開始狼吞虎嚥地吃的時候,得到了鮮明的體現”(範登·休維爾,2018 年,第 123-126 頁)。
“第一堵牆是《為愛痴狂》中佈景的明星。當埃迪和梅伊把自己和對方撞向它時,當他們踢它、打它、沿著它爬行時,他們發現了它的堅不可摧……當梅伊和埃迪最終離開他們骯髒的汽車旅館房間時,他們沒有舉行儀式——他們從側門離開。但他們的離開並沒有帶來任何解決或結論的感覺。由於他們之間的紐帶是不可逃脫的,他們會回來的。從視覺上來說,他們的離開也沒有帶來任何解決。老頭依然佔據著舞臺。他指向空曠的空間,強迫觀眾看到不存在的東西:“你看到那邊的照片了嗎?你看到了嗎?你知道那是誰嗎?那是我的夢中情人。就是她。她是我的。她完全是我的”(津曼,1988 年,第 518 頁)。“老頭,既是埃迪和梅伊的父親,也許是一段記憶或一種罪惡感的投射。他神一般的存在,陰森森地籠罩著埃迪和梅伊亂倫的關係,喚起了奧尼爾式的戲劇:一個過去似乎控制著現在的世界”(潘納,2000 年,第 117-118 頁)。“老頭位於任何真即時間的表象之外:他的搖椅的移動將他鎖定在一個戲劇性的現在,這將抵制任何系統化的年代學嘗試”(布拉特,1998 年,第 24-25 頁)。“埃迪和梅伊講述的故事,導致了《為愛痴狂》的高潮,巧妙地融入了戲劇的動作,製造緊張氣氛,收集過去的資訊,並向老頭揭示了他們亂倫和重婚的家族樹的致命果實”(德羅茲,1984 年,第 101 頁)。
“為頭腦編造的謊言” “是謝潑德家庭戲劇的典型特徵,即暴力發生在荒謬的背景下,這種荒謬背景會淡化其造成的傷害(儘管貝絲的大腦損傷並非如此)。當弗蘭基充當傑克和貝絲之間的使者時,他被貝絲的父親打中了腿,隨後患上了敗血症,貝絲甜言蜜語地承認了他的痛苦,同時她脫衣服開始引誘他”(迪基,1988 年,第 543 頁)。“貝絲的演藝事業……挑戰了傑克對女性的刻板印象……貝絲試圖向他保證她的表演只是[假裝],但傑克不相信她……貝絲在獨立於男人和依賴男人之間搖擺不定……但到劇的結尾,貝絲穿上了所有女性刻板印象的裝飾:她穿著像妓女一樣,卻表現得像一個無辜的處女……傑克贏了:他把她變成了一個物體……貝勒……認為他的騾子比貝絲的傷勢更重要……他自私地想讓梅格和貝絲分開,因為他需要在車裡有人和他說話……梅格在整部劇的大部分時間裡都順從地忍受著他的虐待。直到劇的結尾,她才對性別問題得出了一些自己的結論。當貝勒試圖羞辱她和她的母親時,梅格回答說她不是一個“精神崩潰的人”,而是一個“女性”……佈景上散落著從未被吃掉的死鹿,她意識到男人只是為了殺戮而享受殺戮……洛林意識到,她也是另一個物體,她和莎莉點燃的篝火象徵著獨立,燒燬了囚禁她的房子”(霍爾,1993 年,第 110-114 頁),以及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樣具有破壞性,但方式更狡猾。“貝絲的大腦損傷導致了她斷斷續續的言語,這與所有角色以不同方式承受的更大的傷害相呼應,每個人都受到了心靈的傷害,沒有人能夠逃脫內心 festering的謊言”(鄧肯-瓊斯,2001 年,第 45 頁)。“受損的貝絲試圖透過嘗試穿上男式襯衫來重組自己的生活,彷彿在嘗試新的身份選擇,從而展現出某種賦權的男性氣質,同時轉向弗蘭基,將他視為她丈夫、他暴力的兄弟傑克的溫和版本”(博特姆,2015 年,第 208 頁)。“在整部劇的三分之二的時間裡,傑克認為自己殺死了貝絲,貝絲認為自己要麼死了,要麼精神上殘疾得無法修復。他們都確信這次他們走得太遠了。他們已經無法救贖了……傑克在劇中的追求是尋找幻影的源頭,像神秘主義者一樣看待,也就是說,召喚出已經死去、活著、被殺害的貝絲,來完成他,讓他成為‘一個整體’,並讓她離開……對傑克和貝絲來說,最大的恐懼是失去對方”(羅森,1998 年,第 34-35 頁)。“幾乎從我們第一次在舞臺上看到她開始,[貝絲]就堅定地抵制著來自邁克、她意志堅定、思想狹隘的哥哥的男性統治,並且在劇的程序中,她一次又一次地反擊他試圖壓制她的意志的行為。她也有能力對另一個有權勢的男性人物、她的父親貝勒做出毀滅性的批評,貝勒顯然已經失去了所有的愛。然而,貝絲將保持她的愛,這將是對一個理想男人的愛,一個沒有暴力的傑克”(懷廷,1990 年,第 499 頁)。
在“像……《埋葬的孩子》中的文斯、《為愛痴狂》中的埃迪、《飢餓階層的詛咒》中的韋斯這樣的角色中,謝潑德創造了一個新的美國反英雄:一個被剝奪權利的牛仔,徒勞地尋找早已消失的牧場,一個拒絕中產階級、公司化的美國方形洞的圓形釘子,最後一個真正的偶像破壞者,拒絕資產階級價值觀……獨自在西部流浪,卻自力更生……埃迪符合最浪漫的傳統,當謝潑德故意將他與可怕的沉悶、單色的馬丁對比時,他的吸引力就更加明顯了,上帝保佑,馬丁居然允許女人選擇電影。哪個人物更能引起普通觀眾的共鳴——暴力的、瘋狂的、不負責任的埃迪,還是懦弱的馬丁?這個問題幾乎是修辭性的……女人發現他粗獷的脆弱具有吸引力,男人則把自己想象成這個自力更生的孤獨者的形象,他打破了資產階級順從的枷鎖”(舒勒,1990 年,第 221-222 頁)。
“埋葬的孩子”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70 年代。地點:美國伊利諾伊州。
文字在 http://www.aaronbooth.info/uploads/7/5/6/9/7569212/buried_child.pdf
在一個被忽視的農舍裡,蒂爾登驚訝地向他父親道奇展示了他們田裡的玉米可以被收割,儘管幾年來沒有人種植任何玉米。雖然道奇整天無所事事,除了喝酒,他卻抱怨蒂爾登的無所事事,蒂爾登靠他生活。道奇的妻子海莉為他們的另一個兒子布拉德利辯護,因為他對布拉德利進行了侮辱。道奇沒有直接回答她,而是指著田地說:“我的血肉在後院。”當道奇睡著後,布拉德利用他的一條木腿走過來,在他沒有醒來的時候剪掉了他的頭髮,導致了割傷和傷疤。蒂爾登的兒子文斯在離開六年後突然到來,還有他的女朋友雪莉。讓雪莉越來越擔心的是,道奇把文斯錯認成了年輕的蒂爾登。當蒂爾登拿著一堆從未種過的胡蘿蔔進來時,田野的秘密變得更加深奧了。雪莉更加焦慮,因為蒂爾登一言不發地盯著他的兒子。道奇讓文斯給他買一瓶酒,但蒂爾登沒有承認他的存在。“我曾經有一個兒子,但我們把他埋了。”蒂爾登說,對此道奇斥責了他。雪莉主動幫忙蒂爾登準備和烹飪胡蘿蔔,但文斯認為這是在分散注意力。為了喚起道奇對他的記憶,文斯用指甲敲打牙齒,但沒有效果。當道奇呆呆地看電視時,蒂爾登撫摸著雪莉的外套,然後把它穿在自己身上。最終,道奇開始擔心蒂爾登和雪莉之間不斷增長的關係。“不要告訴她任何事,”他建議道,“她是個局外人。”第二天早上,雪莉似乎準備接管女主人,給道奇送來了牛肉湯。走進房子,不知道雪莉是誰,海莉擔心蒂爾登在哪裡。雪莉頑皮地從布拉德利那裡拿走了他的木腿。她覺得家裡的秘密應該被揭露。布拉德利試圖安慰她。“這裡一切都好,”他說。但道奇不同意。他開始告訴她一個秘密,但海莉打斷了他的話。“如果你說出來,你對我來說就等於死了,”她警告道,但他還是繼續承認海莉曾經懷過另一個男孩,蒂爾登經常被看到在和他說話。“我把他淹死了,”道奇承認道。突然,一個喝醉的文斯從門廊的紗門衝了進來,把房間裡的瓶子打碎了。他開始掌控局面,並比雪莉更進一步,不斷把布拉德利的木腿推到他夠不著的地方。道奇突然感到身體不適,口頭宣佈了他的遺囑並去世了。“蒂爾登關於玉米的說法是對的,”海莉承認道,當她看到他帶著一個埋葬已久屍體的骨頭走進房子。
"飢餓階級的詛咒"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70年代。地點:美國。
文字位於 https://pdfcoffee.com/curse-of-the-starving-class-script-pdf-free.html
前一天,一個憤怒的韋斯頓把他的前門拆了,強行闖入,威脅他的妻子艾拉,但沒有傷害她,就離開了。他的兒子韋斯利清理了碎片。韋斯利的妹妹艾瑪進來檢視冰箱,因為沒有找到要用來演示在4-H課堂上正確切雞肉方法的雞而感到惱火,很可能是她母親把雞吃掉了。韋斯利認為這樣的課程毫無用處,就對著她的解剖圖撒尿。他對母親抱怨肚子餓。“沒有人捱餓,”她堅定地指出。“我們不屬於飢餓階層。”儘管如此,為了改善他們的狀況,她僱了一位律師泰勒,在沒有徵求丈夫同意的情況下,出售房子、牲畜、拖拉機和土地。韋斯利指出抵押貸款還沒有償還。艾瑪也餓了,她盯著冰箱。“裡面有玉米鬆餅嗎?”她絕望地問道。韋斯利試圖救一隻被蛆蟲感染的羔羊,把它抱進廚房,而韋斯頓則從外面抱進來一袋雜貨。然而,裡面只有一堆沙漠朝鮮薊和髒衣服。第二天,韋斯頓得知衣服沒有洗,因為他的妻子沒有留宿。他告訴兒子和女兒,他已經賣掉了房子和土地。艾瑪對這些訊息感到震驚,突然離家出走。韋斯利告訴父親,艾拉也有同樣的想法,為此她與她的律師離開了。韋斯頓威脅要殺死妻子和律師。韋斯頓認為,鑑於他欠了錢,並打算帶著新獲得的現金逃往墨西哥,這種行動方式是合理的。然後他狂躁不安,昏倒在廚房的桌子上。艾拉帶著她自己的雜貨袋回來了,把朝鮮薊從冰箱裡扔了出去。韋斯利發現他母親的律師是同一個曾經賣給他父親無用沙漠土地的人。他斷言她的計劃是徒勞的,因為她的丈夫已經賣掉了房子和土地。買主埃利斯帶著一筆足以償還韋斯頓債務的錢進來了。在他後面是泰勒,他拿著他和艾拉協議的最終草案。他們被一名警官打斷了,警官告訴他們關於艾瑪的令人震驚的訊息。“看來她騎著馬穿過市中心的酒吧,用步槍把那裡打得千瘡百孔,”他說。艾瑪發狂的酒吧正是埃利斯的。為了彌補艾瑪的暴行,埃利斯從韋斯利手中奪走了錢,匆匆離去,而泰勒則偷偷溜走了。艾拉跟著警官去把女兒從監獄裡救出來,之後韋斯頓醒了過來,精神煥發,又有了新的所有權意識。他不再對出售自己的財產感興趣。韋斯利試圖進入他父親的情緒,但無法做到。在飢餓的痛苦中,韋斯利宰殺了羔羊,貪婪地吃著他母親的雜貨,懇求父親逃跑,害怕他的債主想要殺了他,但他無視了這些警告。艾瑪透過與負責的警官調情獲得了釋放,並向她的哥哥宣佈,她打算過上犯罪的生活,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回報。韋斯利對他父親債務的擔憂完全是合理的,因為他們聽到外面傳來巨大的爆炸聲:他們的汽車被債主的打手炸燬了,他們帶走了艾瑪和韋斯利原本打算吃的羔羊。
"愛之愚人"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80年代。地點:美國莫哈維沙漠附近。
文字位於 https://pdfcoffee.com/fool-for-love-sam-shepard-pdf-free.html
在一個簡陋的汽車旅館裡,梅接到了她舊情人埃迪的來訪。雖然他的手指聞起來像是女人的陰道,但她還是讓他留下來。他立刻威脅要“用鋒利的刀子系統地”刺傷她和他自己。她顯然溫柔地擁抱了他,然後踢了他的胯部。從疼痛中恢復過來後,他也選擇留下來,儘管只有一晚。然而,當得知她期待另一個男人馬丁的來訪時,他的怒火被激發了出來。在等待馬丁的時候,埃迪從他的馬拖車裡拿出一支獵槍,然後在房間裡練習套索技巧。突然,汽車的車燈出現在窗戶上。當梅看到車裡有一個女人時,他立刻倒在地上,警告她遠離門。從外面傳來一聲槍聲,接著是玻璃破碎的聲音和汽車喇叭的鳴笛聲。車燈咄咄逼人地再次出現,這對情侶躲到地板上。梅猜到朝他們開槍的女人是埃迪的舊情人,綽號“伯爵夫人”。梅在黑暗中朝她大喊,這時馬丁衝了進來。他以為她有危險,就攻擊埃迪,直到梅叫他住手。看到梅和埃迪之間奇怪的關係,馬丁感到不安,開始離開,但埃迪把他拉了回來。埃迪給他倒了一杯酒,同時也在他父親的杯子裡倒了一些酒,這個男人對除了埃迪以外的所有人來說都是隱形的。埃迪向馬丁解釋了他們的情況。他和梅是青梅竹馬的情人,儘管他的同父異母的姐姐,他們的父親以一種彼此都不知道的方式與兩個女人輪流生活。正是另外一個女人的家裡,他曾經跟著父親,第一次見到了她。埃迪的母親從未發現她丈夫的婚外情。“他會消失好幾個月,她從不問他去哪裡,”埃迪說。“他回來的時候,她總是很高興見到他。”梅補充說,她母親經常試圖追蹤他,甚至不惜從一個城鎮跑到另一個城鎮。最終,他離開了,再也沒有出現過。“我的母親就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盡了,”梅解釋道。“我一直看著她悲傷,就像有人死了一樣。她會蜷縮成一團,只是盯著地板看。”聽到這句話,父親對埃迪反駁道:“她在這裡越界了。”注意到她女兒對埃迪的迷戀,梅的母親懇求他不要再去看她,但他無視了她的願望。然後,她去埃迪的母親那裡,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在悲傷中,埃迪的母親開槍自殺身亡。不知道發生了這一切,老人震驚了。“代表我說句話,”他向埃迪哭喊。“現在沒有人能為我說話。站起來。”“是你的獵槍,”埃迪反駁道。當看到埃迪和梅以戀人的身份互相靠近時,老人更加震驚了。“離她遠點,”他警告道。“你在幹什麼?你們倆不能在一起。”儘管他極力勸阻,這對亂倫的情侶還是擁抱在一起。汽車的車燈再次從外面閃爍。傳來碰撞聲、爆炸聲和馬嘶鳴聲,接著是一場汽油火災。馬丁告訴埃迪他的馬拖車著火了,馬匹也跑掉了。埃迪迅速走出房間,而梅則收拾行李,確信她的情人會回到伯爵夫人那裡。
“心靈的謊言”
[edit | edit source]時間:1980年代。地點:蒙大拿州比林斯,以及美國另一個地區。
文字位於 https://pdfcoffee.com/a-lie-of-the-mindpdf-pdf-free.html
傑克在電話裡向他的兄弟弗蘭基承認,他認為自己殺害了妻子露絲。但露絲還活著,她頭部纏著繃帶在醫院,臉上傷痕累累。她很難和她的哥哥邁克說話,很難認出他,並且在他試圖安慰她的時候朝他吐口水。傑克向弗蘭基解釋說,他懷疑露絲在排練戲劇時與一名演員發生了關係。他突然感到頭暈,摔倒了。他也要求不要把他一個人留下。邁克試圖幫助露絲走路,並勸阻她不要想傑克。但她沒有配合。弗蘭基向他的母親洛林和妹妹莎莉解釋說,傑克可能殺害了他的妻子,這個訊息對洛林來說毫無意義,因為她不認識她兒子的妻子。她宣稱,“我不記得他的那些女人。”兩位女士都被傑克蒼白的臉色和凹陷、黑暗的眼睛嚇了一跳。他誤以為他的妹妹是貝絲,就抓住她,洛林用鞋打了他頭,弗蘭基試圖阻止她,又被她打了一下。弗蘭基建議兩位女士把傑克帶回家,直到他查明貝絲髮生了什麼事。儘管莎莉抗議,洛林還是把他帶回了家。邁克向他的父親貝勒和母親梅格解釋說,貝絲遭受了腦損傷。與洛林類似,梅格也認不出她女兒丈夫的名字。因為貝勒有牲畜要喂,他把妻子留給了兒子。儘管洛林試圖喂兒子湯,但他拒絕吃,反而把碗摔在床墊上,踩在湯上。與此同時,莎莉離開了家。冷靜下來後,他問母親關於父親遺體放在箱子裡的事,得知父親在被一輛過路卡車撞死時,他就在場,他感到震驚。一段時間後,貝絲恢復了健康,回到了她在蒙大拿州的父母家。她以為她聽到傑克的聲音在外面,但邁克解釋說那是弗蘭基。在打獵時,貝勒不小心從大腿射穿了弗蘭基,但沒有傷到骨頭。他鼓勵女兒在弗蘭基的腿下放一個腳凳,讓他休息。莎莉回到了洛林的家中,在那裡,傑克脖子上圍著國旗作為圍巾,這是軍隊在他父親去世時發給他的,他告訴莎莉,他再也不打算出門了。洛林擔心莎莉會對她的兒子產生不好的影響,想要女兒離開,但傑克更願意讓她待在他的房間裡。母親離開房間後,他懇求莎莉幫助他逃跑,以便他再次見到貝絲,現在他知道貝絲還活著。貝絲脫下襯衫,包紮弗蘭基受傷的腿。她擔心腿上有一條黑線,那是血液中毒的跡象。弗蘭基擔心貝絲沒有穿襯衫被家人找到。“你可以假裝愛我,穿我的襯衫,”她提議道。他把她推開,尋找離開的路。邁克回來了,手裡提著鹿的後腿。弗蘭基懇求邁克幫助他離開,但邁克、貝絲和梅格都沒有理會他。為了騙過母親,傑克把莎莉藏在床上的毯子裡,讓她以為他還在床上。莎莉接下來發現自己照顧著躺在傑克床上顫抖的洛林。洛林打掉了女兒手中的勺子。莎莉指責傑克是殺害父親的兇手,因為他鼓勵一個酒鬼喝酒,直到他在墨西哥被撞死。洛林否認傑克策劃了這件事,反而指責她的女兒。弗蘭基睡覺時,貝勒鼓勵梅格在他疼痛的腳上倒一些用於護理靴子而不是腳的油。弗蘭基的腿已經失去了知覺。當貝絲穿著奇裝異服進來宣佈:“這是我的男人。這是我的唯一。我們就要結婚了,爸爸。我已經決定了。”時,他用毯子裹住自己,避免被貝絲看到。一聲槍響傳來,不久之後,邁克進來說他已經嚇唬住了傑克,把他綁在了他們小屋外面的爐子上。貝勒對兒子和女兒的事情漠不關心,貝絲把頭靠在弗蘭基的肚子上,梅格考慮著婚禮計劃。傑克不在家後,洛林和莎莉準備搬到愛爾蘭,洛林的祖母住在那裡,她們把自己的廢棄物堆起來準備燒掉。讓女兒驚訝的是,洛林把房子連同廢棄物一起燒掉了。邁克手持步槍,牽著傑克,一邊發出咯咯的叫聲,好像是在牽著一匹嘴套是美國國旗的馬,然後把國旗取下來,走進屋裡去接貝絲,以便讓她丈夫為打她道歉。但在貝絲看來,傑克已經死了。她從哥哥身邊退開,弗蘭基在沙發上瑟瑟發抖。傑克沒有道歉,而是告訴貝絲:“我比這地球更愛你,”把妻子交給哥哥,然後離開了。儘管弗蘭基不想和她有任何瓜葛,但她還是把頭靠在他的胸口,貝勒和梅格對這件事漠不關心,他們搶走了國旗,成功地把它疊了起來。
大衛·馬梅特
[edit | edit source]
大衛·馬梅特(1947-?)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他創作了《芝加哥性變態》(1974年)、《美國水牛》(1975年)和《推銷員之死》(1984年)。語言粗俗,類似品特風格,角色毫無必要地重複自己,或者說話卻傳遞很少資訊;但即使是粗俗的語言在適當的戲劇環境下也能獲得一定程度的力量。
《芝加哥性變態》揭露了20世紀70年代艾滋病出現之前的性放縱氛圍,當時“開放式情侶發現,約會遊戲的性別角色實際上阻礙了任何愛情的可能性”(伯科維茨,1997年,第168頁)。科恩(1982年)認為,標題中的“性變態”指的是“拒絕在性關係中投入感情”(第43頁)。“在持續不斷的講話節奏和平行獨白的白噪音之下,存在一種沉默,角色試圖消除這種沉默。城市侵略,是戲劇中衝突的典型特徵,將角色推向更深的孤立。面具不僅掩蓋了自我,還取代了自我。主體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作為客體的身體。孤獨、痛苦、簡單的需要,只有透過它們被從一個以速度、反諷幽默和脆弱的能量取代任何更堅實的東西的世界中驅逐出來,才能得到暗示......只有商品價值似乎得以倖存,性窺視、性幻想和性佔有作為空洞的物質主義的對應物被提供。然而,戲劇的能量並非沒有吸引力,諷刺幽默也並非沒有吸引力”(比格斯比,1985年,第257頁)。赫爾曼(1987年)將該劇描述為“一場變質的誘惑儀式”,其中“對任何型別的感情都感到厭倦......較年長的夫婦代表了性別之間永久敵意的頑固態度,甚至年輕的夫婦也表現出彼此之間缺乏信任”(第132-133頁)。儘管充滿敵意,伯尼卻想著女人,想要女人。該劇“喚起了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侵略是一種交流方式,語言已經變質。它的主要貨幣是性,但性卻被貶值,偽造到它既不能帶來免受孤獨的免疫力,也不能滿足需求。單身酒吧成為一個有效的社會形象,在這個社會里,疏遠的人們推銷自己,尋求他們害怕的陪伴,用生活方式來代替生活”(比格斯比,1992年,第208頁)。“對於男人來說,這種關係是無菌的,而不是一種真正的導師-學徒關係,因為導師不能傳授任何關於如何與女人建立關係的真知灼見......對於女人來說,瓊無法對黛布試圖保持樂觀的態度表示真正的同情,並儘可能地貶低了她對鼓勵的需要......當伯尼和瓊在單身酒吧相遇時......它將一個想要女人然後又不想的女人和一個不想女人然後又想女人的男人聯絡起來......這在微觀層面上與丹和黛布之間中央關係的發展和消亡相平行......儘管丹和黛布可以拋棄為社會角色扮演而發展的語言武器庫,但他們沒有東西可以取代它。這裡的挑戰是找到超越性交的方式來互相交流”(卡羅爾,1987年,第56-57頁)。對於角色來說,“性真的已經成為一個髒字,一種對容易感到厭倦的人的偷笑消遣。與其履行其作為情感關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最初功能,性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是一種廉價的刺激,男人對女人“做”的事情,女人應該為此感到感激......《芝加哥性變態》中的角色與馬梅特戲劇中的許多其他人一樣,在一種二流被接受為常態的世界裡,情感上漂泊無定。他們偶爾會瞥見除了他們忍受的俗不可耐的生活之外的其他可能性,但這些轉瞬即逝的啟示沒有機會在他們存在的狂熱氛圍中紮根。由於沒有真正的道德基礎來支撐他們的想法,他們的生活是無形的、扭曲的、腐敗的......角色沉迷於瘋狂的語言爭吵,這是他們掩蓋其生活根源中存在的真空的方式;他們放任自在地互相丟擲俏皮話和老生常談,只是部分地掩蓋了他們的絕望......黛博拉和瓊在《芝加哥性變態》中......似乎是理想主義者,但隨著劇情的發展,她們對所獲得的東西的失望變得幾乎可以觸控。在作品的結尾,她們似乎已經得出結論,感情通常來自同性之間,而且更加真誠、更加自由地流露,而異性配對的整個結構就是一個騙局......瓊經常以隨意打斷的方式來削弱情況的嚴肅性,比如“你要吃你的麵包卷嗎?......這個麵包卷很好吃”(第20場,第38頁),等等。黛博拉只是斷斷續續、含糊地回應,兩次宣佈“我不同意你”,並說她要“搬到丹尼那裡”。因此,馬梅特使瓊的嚴重情緒在心理上值得懷疑;難道不能暗示她實際上嫉妒她朋友與丹尼的成功,以及她貶低異性戀只不過是怨恨嗎?黛博拉與她朋友的想法不一致也是基於模稜兩可的前提;她剛剛決定和丹尼住在一起,因此瓊對男女之間性關係基礎的批評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威脅。她朋友的譴責破壞了黛博拉的安全感和與情人住在一起的理由。因此,她應該重複說她不同意瓊並不奇怪——在她目前的情況下,她真的負擔不起這樣做”(迪恩,2005年,第126-141頁)。
“美國野牛” “展示了小偷試圖策劃搶劫,卻發現自己不斷地被需要在彼此面前建立和維持能力和尊嚴形象的需求,以及他們的角色強加於他們的禮儀和後勤細節所分心”(Berkowitz,1997 年,第 168 頁)。Demastes(1988)引用了幾位評論家,他們抱怨這出戲幾乎沒有發生任何事情(第 80 頁)。然而,這裡,就像在“等待戈多”(1953 年)和“哈姆雷特”(1600 年)中一樣,不行動與行動一樣戲劇性地緊張。其他評論家認為這出戲是對“美國商業道德的批判”(Herman,1987 年,第 141 頁),“弱肉強食的體系……商業忠誠會根據誰“掌握著牌”而搖擺不定”(Krasner,2006 年,第 104 頁),而它只是一個小偷扮演商人的妄想(Demastes,1988 年,第 82-83 頁)。事實上,Teach 將自己視為自由企業的代表,而不是自吹自擂的標誌(Haedicke,2007)。“‘沒有這個,我們只是荒野中的野蠻人’,他說。文明在 Teach 對邊疆神話的理解中,是由賺錢的機會所定義的,而他對個人的讚美,而不是對集體的讚美,則反映了美國夢的個人主義冷酷無情,一種人人為己的心態”(Saddik,2007 年,第 143 頁)。“這種立場的腐蝕性影響在 Don 的腐敗中顯露出來,Teach 脅迫他‘純粹作為一項商業提議’,從他們的‘事情’中剔除 Bob,即從那個‘他媽的水果’那裡搶走水牛鎳幣的荒謬計劃”(第 413 頁)。“角色們不斷地以‘商業’的必要性為由為他們的行為辯護,而這僅僅成為了一種自我辯護機制……角色們譴責了他們本身就是主要證據,並且是主要推動力的暴力和價值觀的腐敗……對 Teach 來說,為了搶劫而武裝自己,武器是‘必要的保護,以防某些瘋狂的瘋子’的住戶,他們可能不理性地將對他們財產的攻擊‘視為對他們個人領地的入侵’”(Bigsby,1985 年,第 262-264 頁)。“Mamet 在第一幕的早期就揭示了金錢帶來的哲學困境,這成為美國野牛的主要關注點,當時他的主角 Don 給 Bob 上了關於商業的課,這些課很好地突出了自然主義邏輯的核心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涉及許多評論家認為是文學自然主義的定義主題:個人自由意志與個人行為決定論之間的衝突。在討論 Fletcher 時——這出戲行動之前發生的紙牌遊戲贏家,也是 Mamet 眾多類似戈多的角色之一,代表著舞臺之外強大的力量——Don 透過自己使用技能、才能和經驗等術語來表達人類自由的悖論。首先,Don 將 Fletcher 在紙牌中的成功歸因於‘[s]kill and talent and the balls to arrive at your own conclusions’,這暗示了學習經驗、天生的能力和獨立思考的混合……Don 給 Bob 的另一堂商業課是‘行動勝於雄辯’,換句話說就是行動說話,說話行動——行動就是說話,說話就是行動。這個看似矛盾的說法是這位劇作家和推銷員作品的核心真理……Don 意識到並被這種悖論所困擾,這一點從他反覆試圖控制劇中其他角色的言論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來。當 Teach 試圖取代 Bob 成為 Don 在計劃中的搶劫中的同夥時,含蓄地提到了 Bob 的海洛因癮,Don 插話道,‘我不希望你提到這件事’,幾行後又說,‘我不希望談論這件事’……更難解釋的是 Don 與構成其職業本質的東西之間的關係:買賣。在這出戲中,我們從未看到這個推銷員賣出任何東西。事實上,我們被告知他賣出的唯一一件物品——在戲劇行動之前賣掉的水牛鎳幣——Don 在整齣戲中都在試圖拿回來。這個計劃搶劫的動機不是金錢……是名譽上的損失,而不是對金錢的渴望,促使了 Don 的行動。事實上,當 Teach 談到他們想象中受害者所擁有的不同硬幣的價值時,Don 並不感興趣……搶劫有時被認為比交換更有尊嚴,因為它涉及個人參與和搶劫者承擔相當大的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說,Don 希望透過搶劫拿回他的鎳幣,顯然是由一種受損的自尊心而不是對金錢的渴望所驅使,這構成了對經濟交換的異化世界的拒絕……與 Don 和 Bob 不同,Teach 從來不把談話理解為‘只是談話’——一種友好的嘗試,一種建立社群的方式。在第一幕中,Don 關於 Teach 前一天晚上在撲克遊戲中表現如何的看似無辜的問題,被 Teach 解釋為一種攻擊。Don 不得不解釋‘我只是在說……隨便聊聊’。同樣,當 Don 試圖就天氣進行友好的閒聊時,Teach 對他的問題非常認真。Teach 只能把談話理解為操縱,在讓別人按照某種方式行動方面很有用。這就是為什麼當他得知這出戲結束時,他和 Don 一整天所做的一切計劃都是基於謊言時,他會感到如此震驚:Bob 聲稱他看到硬幣買家(他們意圖的受害者)帶著一個手提箱,顯然要旅行,但最終他透露他沒有”(Dietrick,2006 年,第 331-342 頁)。“Don 是一個現代版的金蟲……[指] 19 世紀末期支援由貴金屬(黃金或白銀)支撐的經濟的倡導者——[他們] 認為綠背貨幣經濟很危險,因為它依賴於貨幣,這些貨幣只能承諾價值。期票是一種不真實的、不自然的、不真實的貨幣形式,因為它只是模擬價值。只有貴金屬才是真正的貨幣,因為它們的價值自然地印刻在它們的物理形式中”(Little,2004 年,第 150 頁)。“Teach 利用語言進行操縱,其目的是說服、推銷和逃避真正的接觸。他的言語是誇誇其談、吹噓、自卑、虛偽的謙虛……他的策略都是表面的……這種膚淺暴露了他的深深的不安全感和脆弱性;他在忠誠問題上感到矛盾;他渴望得到 Don 的認可”(Krasner,2016 年,第 239 頁)。“儘管 Don 早些時候對 Bob 說過‘你在這種生活中沒有朋友’,但很明顯,他和 Bob 分享著一種友誼,並且他還是這個男孩的導師。這種培育關係通常透過停頓和柔和的節奏來暗示,這些節奏有時會掩蓋他們的表面含義。Teach 注意到了這一點——他關於‘商業’和‘自由企業’的貶低性言論顯然是為了破壞它。它們揭示了他自己希望取代 Bob 與 Don 形成積極關係的願望”(Carroll,1987 年,第 36 頁)。“Teach……成為 Donny 和 Bobby 之間的催化劑,幫助他們意識到彼此的重要性……美國野牛專注於小流氓的語言,並釋放出一場無情的粗俗髒話的暴風雨。這是一次荒謬的練習,其中沒有任何重要的事情發生。這出戲以背叛和未能執行搶劫而告終。這出戲闡述了價值觀衝突——友誼、忠誠和商業被定義為照顧好自己。這出戲還講述了在人際關係中缺乏信任所付出的代價。它談論了在爭奪彼此感情的男人之間滋生的愛、嫉妒和不信任”(Barnes,1983 年,第 444 頁)。“我們永遠不知道 Teach 是做什麼工作的。Bob,一個正在康復的癮君子,無法找到穩定的工作。只有 Don 有一個有形的,儘管很邊緣的生意,但正是他放棄了自己的道德立場。Don 背叛了他與 Bob 的友誼”(Roudané,2004 年,第 63 頁)。
“《推銷員之死》聚焦高壓推銷員的世界,發現他們的身份認同和男子氣概與工作緊密相連,以至於他們永遠無法停止推銷,即使是對彼此和自己。”(Berkowitz,1997年,第168頁)。“這些角色從他們的身份認同和價值感中獲得的技能和直覺也使他們變得殘疾,使他們無法做到誠實、正直,甚至無法進行簡單的、沒有預謀的對話。”(Berkowitz,1992年,第194頁)。“在這些推銷員喋喋不休的粗俗言語、不連貫的聲音、無休止的陳詞濫調以及充當交流的病態重疊的獨白背後,是一個空虛,一個世界,其存在只能從它被持續忽略的一致性中推斷出來。這個世界——一個充滿真情實感、人類需求和精神追求的世界——在這樣一個只由與私人生活或道德生存的必要性無關的完成定義的公共世界中找不到慰藉、表達或相關性。”(Bigsby,1985年,第286頁)。正如在《美國水牛》中一樣,赫爾曼(1987年)認為這部戲劇是對“美國商業道德的批判”(第141頁),而克拉斯納(2006年)則認為它是“商業世界的縮影”(第124頁)。考慮到謝莉的斷言“一個男人就是他的工作”,或許更有理由如此。 “這些角色中很少有人能夠達到,更不用說維持[頂尖職位]了,因此競爭確保了大多數人無法獲得被定義為陽剛的認同……正如利文對威廉姆森所說,‘一個男人就是他的工作’。明確的含義是,做一份工作就是成就一個人,就是賦予一個人作為男人的身份。利文繼續說,如果你‘沒有膽量’去做這份工作,那麼你就‘是秘書’——一項傳統上由女性擔任的工作。或者,正如羅瑪在威廉姆森搞砸一筆交易時對他說:‘你是在哪裡學的手藝?你個愚蠢的混蛋!你這白痴!是誰告訴你你可以和男人一起工作?’如果一份工作定義了一個男人,那麼在商業上的失敗就定義了非男人,也就是女人。正是這兩種位置的區別提供了任何身份認同感……在場景三中,羅瑪和林克之間生動展現了男人之間談話的同志情誼,但這種同志情誼被一種認識所破壞,即羅瑪分享的所有信心只不過是針對毫無戒心的林克的推銷策略的引子。林克渴望相信羅瑪的友誼,相信他們彼此理解和接受作為男人,即使羅瑪的騙局被揭穿。林克第二天回來拿回支票,但他明確表示,他是被妻子派來的,是妻子讓他們之間產生了隔閡。他告訴羅瑪,‘不是我,是我的妻子’迫使他要求拿回錢,而這個妻子剝奪了他的‘談判能力’。林克與妻子的關係顯然不反映陽剛的支配/陰柔的服從的二元論,也許他之所以被羅瑪吸引,正是因為羅瑪擁有權力:羅瑪作為頂尖推銷員的身份是穩固的。即使林克發現他的支票已經被兌現了,羅瑪顯然對他撒了謊,他仍然認為是自己,而不是羅瑪,在某種程度上失敗了。他用類似於鮑比在《美國水牛》結尾時的臺詞向羅瑪道歉:‘我知道我讓你失望了。對不起’……《推銷員之死》中男人的性別困惑,雖然沒有被女性的實際存在所複雜化,但在語言中不斷被喚醒。表現不佳的男人是‘秘書’或‘混蛋’。”(McDonough,1992年,第201-203頁)。“羅瑪的信條是一個純粹的理性主義和自私自利的信條;推銷員,像其他人一樣,必須像時代一樣,貪婪、粗俗、卑鄙,為了自己的安全而做任何事。”(Adler,1987年,第106頁)。在第一幕的推銷中,“羅瑪向他的目標物件發表了幾乎是一段獨白,他的目標物件只有六行對話,其中只有一句完整句(‘我不知道’)。羅瑪宣揚的具有誘惑力的哲學是一套流氓準則,給‘中產階級道德’蒙上了陰影,以及‘壞人是否下地獄’的問題,並對性冒險發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評論。羅瑪努力將自己塑造成無所畏懼的化身,同時將他的同伴納入他關於冒險、行動和積極生活的倫理。這種談話是如此熟悉和親切,以至於當羅瑪問他的同伴的名字時,這令人驚訝。羅瑪最終談到了土地,他用自己輕描淡寫的‘佛羅里達。廢話’來介紹這個推銷。羅瑪開始攻擊那個人,詹姆斯·林克,‘聽我說現在我要告訴你什麼’(Pressley,2018年,第55頁)。“幾乎是對林克的一段獨白,其中大部分內容似乎無關緊要,甚至有些內容很模糊,但這就是重點。他,羅瑪,顯然是在漫長的一天結束時放鬆身心,與一張友好的臉分享關於生活的隨意想法。直到最後,當他的獵物準備好被殺害時,他才進入推銷模式——而且是以一種(‘佛羅里達廢話。’‘也許確實如此’)的方式,暗示他並不特別感興趣進行推銷。他先發制人地預先駁斥了未來的反對意見,用奉承的語氣暗示林克會懷疑他嘗試進行推銷的任何行為。但這整個獨白實際上是有目的的。羅瑪似乎意識到了林克後來行為所證實的內容。他被動、壓抑,並且從根本上害怕他的妻子。無論如何,羅瑪都迎合了林克的內心,這部分並不完全被傳統的道德所嚇倒,也許會喜歡assert自己,甚至冒險。”(Nightingale,2004年,第99-100頁)。“利文作為推銷員和欺詐演員的表演構成了他的身份,但當他將這種幻想推得太遠,威脅到企業的盈利結構時,他的整個世界都坍塌了。”(Quinn,2005年,第198頁)。“語言的模糊性——省略、並列和隱藏(與闡述相反)——讓我們意識到語言作為行動,作為在修辭上發揮作用的東西,而不是作為清晰的傳播或交流媒介。因為推銷員是修辭學家,他們的工作取決於語言的力量、表達的行為、言語的舞臺。無論使用什麼詞語,節奏、語調、停頓、片段都是為了恐嚇、哄騙、前進、撤退、誘惑、留下深刻印象。”(Cardullo,2016年,第248頁)。
“馬梅特的世界是一個崩潰的世界。人際關係變得疏遠。沒有超然的東西,無論是世俗的還是宗教的。神話存在,但它們被掏空了。語言不再起作用,將人們聯絡在一起,形成一個共同的世界。幻想是唯一保留其力量的力量,以懷舊的形式存在,這種懷舊被剝奪了人類內容,或者以只能在不被執行的情況下才能被接受的野心而存在。”(Bigsby,1985年,第288頁)。

時間:20世紀70年代。地點:美國芝加哥。
伯尼告訴丹尼前一天晚上發生在他身上的事,當時他在一家煎餅屋裡,付了一包香菸給一個他以前不認識的二十歲的女孩。“來我房間,我會用香菸把你換回來,”她說。“不!”丹尼驚呼道,他對這個女孩如此急於邀請感到驚訝。洗完澡後,伯尼用毛巾猛擊了她,把收音機扔到她肩上,在她穿著舊的防彈背心時和她發生了性關係。在她把汽油罐扔到牆上並點燃後,他離開了。另一次,伯尼遇見了瓊,他剛認識她,並試圖誘姦她,但沒有成功。丹尼和瓊的室友黛博拉運氣更好。這對情侶繼續約會。有一次在床上,她描述了他們做愛時的想法。“我們上次做愛時,我幻想了其他女人,”她說,他回答說:“我上次自慰時,我想到的是我的左手。”在瓊工作的幼兒園,她發現兩個男孩在撫摸彼此的生殖器。伯尼和丹尼談論了他童年的經歷,有一次,一個男人在一家電影院裡伸手去夠另一個男人時,碰了他的陰莖。他認為那段經歷對他沒有影響。看到丹尼和黛博拉陷入長期關係,伯尼建議他甩掉她。但丹尼拒絕聽從這個建議,搬進了她的住所。“我給你兩個月,”瓊得知這個訊息後,諷刺地對黛博拉說。在和丹尼一起觀看色情電影時,伯尼警告他要提防其他顧客。“他們現在這裡有很多渣滓,”他評論道。隨著時間的推移,丹尼和黛博拉的關係開始惡化。在得知丹尼和黛博拉要分手後,伯尼建議他的朋友不要失去幽默感。回到瓊那裡住,黛博拉認為她和丹尼分手都是她的錯。瓊根本不相信。沒有女朋友,丹尼加入了伯尼,一起看著穿著泳衣的女人在海灘上散步。“我看不出繼續活著的理由,”突然感到沮喪的伯尼承認。“想想我看到了男人所能期望的最高的東西。”看著一個特定的女人,丹尼驚呼道:“我能看到她在**。”當伯尼向另一個女人打招呼時,她沉默地走開了。“聾子**,”丹尼評論道,這句評論配得上伯尼。

時間:20世紀70年代。地點:美國芝加哥。
文字在 https://kupdf.net/download/american-buffalo_5a2a25b3e2b6f5ae5d2b5db9_pdf
二手店老闆唐,請鮑勃監視一位顧客,因為他以一個令人驚訝的高價從唐那裡買了一枚古董鎳幣。鮑勃隨後告訴他,那個人帶著一個手提箱離開了家。唐的另一個朋友,提奇,告訴他可以安全地潛入那個人的家中,搶劫他的硬幣,為此,他不需要鮑勃。唐猶豫了,但最終同意了他的提議。當被問及他將如何潛入家中時,提奇的回答令人擔憂地含糊不清,因此唐要求一個名叫弗萊徹的人在搶劫時陪同他。就在那天晚上,鮑勃帶著一枚他認為很有價值的鎳幣來到唐的店裡,並提議賣給他。唐給了他一些錢,兩人同意稍後查閱目錄以確定其價值。提奇來得晚了,但在弗萊徹到來之前。他很不愉快地發現鮑勃在那裡,鮑勃一直在閒逛,最後離開了。唐和提奇緊張地等待著弗萊徹,卻無法透過電話聯絡到他。唐更加不安的是,他得知弗萊徹在前一天晚上在紙牌遊戲中欺騙了提奇。最後,鮑勃回來,帶來訊息說弗萊徹在被搶劫後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當唐打電話到鮑勃提到的醫院時,對方告訴他,沒有登記過這樣的病人。唐和提奇立即對鮑勃產生懷疑,鮑勃無法說出醫院的名字,對於他如何得到那枚有價值的鎳幣,他也含糊其辭。由於對這些答案感到惱火,並擔心他和弗萊徹可能已經搶劫了他們想要搶劫的受害者,提奇重重地擊打鮑勃的頭部,導致他的耳朵開始流血。他還瘋狂地揮舞著拳頭,破壞了唐店鋪裡的很多財產。然而,他們最終得知鮑勃關於弗萊徹的話是實話。提奇帶著鮑勃上了他的車,把他送往醫院,而唐則悲傷地看著他。
時間:1980 年代。地點:美國芝加哥。
文字於 https://pdfcoffee.com/glengarry-glen-ross-david-mamet-2-pdf-free.html
房地產經紀人謝利·萊文試圖說服他的辦公室經理約翰·威廉姆森,讓他為他們工作的公司格倫加里·格倫羅斯提供有希望客戶的線索(座標),以便銷售佛羅里達州的土地。約翰願意為謝利提供兩個線索,但要求作為交換,謝利需要支付 100 美元,而經紀人無法提供。另外兩位房地產經紀人戴夫·莫斯和喬治·阿羅諾抱怨管理層為取得成功而採用的施壓手段。戴夫感到沮喪,建議他們應該偷竊 5,000 條線索,並以 5,000 美元的價格賣給由傑瑞·格拉夫領導的競爭公司。由於戴夫過去經常抱怨公司的政策,並且承認自己“大嘴巴”,他覺得喬治應該進入辦公室並實施盜竊。喬治起初拒絕參與這個計劃,但當被告知如果戴夫被抓住,他將被視為盜竊案的同謀時,他便屈服了。房地產經紀人中最成功的裡基·羅馬與一位名叫詹姆斯的客戶達成了一筆交易,但由於盜竊案,他沮喪地得知自己一些未備案的線索被盜,因此現在他必須嘗試向“爛人”推銷。相反,謝利在剛剛完成了一筆以“爛人雜誌訂閱線索”為基礎的八個單位的交易後感到興奮。當戴夫詛咒指控他搶劫的偵探時,裡基指出,盜竊案對那些在上個月沒有完成任何好交易的人來說毫無影響。出乎意料的是,詹姆斯進入了辦公室。懷疑詹姆斯想要取消交易,裡基假裝謝利是他剛剛賣了五個農場給的客戶,說他必須和他一起出去。謝利配合著。當詹姆斯告訴他他的妻子想讓他取消交易時,裡基向他保證,這是一個對投資規模的“普遍反應”,這是一個“女性都會有的”謹慎反應。他試圖欺騙詹姆斯,但當約翰誤解了情況,試圖幫助裡基向客戶保證入室盜竊事件沒有影響他的支票時,他向客戶撒謊說支票已經寄給了銀行,而裡基之前告訴客戶支票無法傳送。當偵探繼續詢問每位保險經紀人關於入室盜竊事件時,輪到謝利誤解情況了。謝利詛咒約翰,因為他撒謊欺騙客戶毀了裡基的交易,而謝利無法知道約翰確實是撒謊,因為與他以往的習慣不同,約翰在前一天晚上盜竊案發生時把合同留在了他的辦公桌上。因此,約翰指責謝利對入室盜竊案負責,因為只有竊賊才知道合同在他的辦公桌上。當約翰威脅說如果謝利不告訴他偷來的線索在哪裡,他會向偵探透露他知道的事情,謝利感到恐慌,並透露格拉夫以 5,000 美元的價格從戴夫·莫斯那裡獲得了線索。當謝利試圖與約翰達成協議,給他一半的銷售額時,約翰告訴他他的八個單位的客戶是瘋子,所以他的支票毫無價值,然後走向偵探,透露他對謝利所知的一切。

憑藉《鋼琴課》(1987 年)和《喬·特納來了又去》(1988 年),奧古斯特·威爾遜(1945-2005)在美國戲劇界的地位得到確立。
在《鋼琴課》中,鋼琴代表著非洲的傳統(伊萊姆,2007)。特別是,“這架鋼琴體現了兩種文化中心的遺產:非洲和南方。伯尼斯反對出售鋼琴,因為這架樂器代表著非洲血統”,而男孩威利“想在南方的根基上播種…購買薩特曾經擁有的土地…拒絕南方就意味著不僅要拒絕黑人靈歌、布魯斯和口頭傳統,還要拒絕對土地的合法所有權。男孩威利想要獲得薩特財產的願望代表著黑人權利的倫理”(克拉斯納,2006 年,第 158-159 頁)。“透過在祖先被奴役的土地上謀生來實現經濟獨立,這是男孩威利設想的一種為家族歷史贖罪的方式。在他看來,出售一件已不再使用的木製遺物,以換取實現他夢想,從而紀念他的祖先,是一種小小的犧牲…在驅逐薩特的幽靈,從房子裡開始,可能意味著多種因素,從兄弟姐妹最終克服了他們之間的相互對抗,團結起來共同努力打敗他們的共同敵人,開始”(隆德雷,2007 年,第 116-118 頁)。伯尼斯被薩特的幽靈困擾,因為儘管她留著傳家寶,但她卻不彈奏它,因此與她的非洲血統隔絕(伊萊姆,2007 年,第 328 頁)。“伯尼斯在情感上受到傷害,充滿仇恨和憤怒;她無法接近她的傳家寶鋼琴,這架鋼琴充滿了她祖先的靈魂…威爾遜揭示了他對歷史的看法,歷史不是像伯尼斯最初認為的那樣是負擔,而是可以賦予整個非裔美國人社群力量的積極能量源泉”(赫林頓,2002 年,第 60-61 頁)。“多克爾在溫寧男孩的幫助下,證實了他的敘述的可信度,清楚地敘述了過去的創傷事件,即使他記得確切的日期和時間;例如,他準確地回憶起祖先家庭分裂的所有令人震驚的事件…多克爾的敘述證明創傷是令人難忘的,可以描述的,並且創傷增強了記憶,而不是抹去了它…男孩威利認為,通過出售鋼琴來擁有薩特家族的土地,是推翻困擾他們家族的奴隸制痛苦記憶的一種方式。他相信擁有土地將賦予他足夠的地位和自信,去與白人地主競爭;因此,他只是效仿了資本主義壓迫者的做法…伯尼斯透過藝術,請求祖先的幽靈幫助她驅逐薩特的幽靈…火車的響聲表明伯尼斯唱出了或敘述了她壓抑的過去對黃狗的創傷記憶。她終於表達了薩特的罪行,壓抑她家族心理的屈辱和創傷記憶,即他們受到的赤裸裸的壓迫…劇中的幽靈代表著侵入性的想法和反覆出現的噩夢,這些想法和噩夢困擾著創傷的受害者,而鋼琴則充當著非裔美國人過去歷史的構建記憶”(馬盧德和巴爾扎尼,2020 年,第 111-121 頁)。“正是音樂,哀求、總結和發展哀歌的音樂,驅逐了薩特的幽靈,離開了伯尼斯的房子。威爾遜賦予了伯尼斯對祖先的懇求之歌(“我希望你能幫助我”)以強大的力量,音樂既拯救了鋼琴,也拯救了理智”(海,1999 年,第 67 頁)。鋼琴的“力量…只有在演奏時才強大,因為即使薩特的幽靈也演奏鋼琴,試圖讓它成為他自己的旋律設計的樂器…儘管男孩威利回到南方沒有得到他需要的錢,但有跡象表明,他意識到透過磨難而癒合的親情紐帶比薩特的土地更重要”(楊,2004 年,第 140-141 頁)。“威爾遜將伯尼斯與白人壓迫勢力聯絡在一起,她阻止男孩威利拿走鋼琴;每當男孩威利試圖搬走鋼琴時,薩特的幽靈就會和伯尼斯一起變得激動…她打破了她 7 年的禁令,不再彈鋼琴…在目睹了伯尼斯母系力量的最終體現之後,男孩威利,以前是口若懸河的人,迅速離開了,沒有提出異議,把鋼琴留給了他的姐姐…黑人母系社會沉默了薩特的幽靈和男孩威利的爭論,並確保了它自己的未來”(馬拉,1994 年,第 144-147 頁)。
在“約瑟夫·特納來了又走了”中,“先驅者盧米斯來到寄宿公寓時感到困惑。為了繼續前進,他必須解決“與妻子的未完成事務”,因為被不公正的監禁判決而被強行切斷。當先驅者盧米斯觀察到非洲節奏的歌聲和舞蹈時,他抗拒音樂,卻被他不理解的音樂扔到地上。他的幻象結合了靈性主義的兩個基本原則:非洲中心主義和基督教”,第一個是奴隸從海里升起,第二個是復活和洗禮”(Krasner,2006 年第 135-136 頁)或耶穌在水上行走。“當盧米斯聽到這首歌時,他強烈地反對它。這首歌具有明確的政治和社會含義,充當了變革的有力媒介。在神秘而強大的拜納姆(一名巫師,也是寄宿公寓的居民)的幫助下,盧米斯開始理解他的探索,將其視為一種精神和實踐的追求,以找到他的歌,與過去建立聯絡,而這段過去在被約瑟夫·特納奴役時已經丟失。他踏上了自我認知、精神和心理解放的旅程”(Elam,2007 年第 326 頁),這種解放形式拒絕了基督教,而拜納姆贊成。“威爾遜創造了拜納姆作為一個人形合唱團,……這是一種將活人和死人的社群人格化的方式,……它將象徵著……確保人們遵守祖先傳統的集體非洲祖先”(Hay,2007 年第 95 頁)。“非洲人來到美國後被強加給他們的宗教和他們在中世紀航行中倖存下來的信仰體系之間的緊張局勢驅動了《約瑟夫·特納來了又走了》的衝突,揭示了寄宿公寓社群和盧米斯自己婚姻中的深刻裂痕。透過將非洲靈性主義的各個方面以及在中世紀航行中倖存下來的各種習俗與截然不同的儀式、習俗和宗教信仰並置,《約瑟夫·特納》捕捉到了非洲人所遭受的文化扼殺的本質……這部戲劇對新世界基督教發出了尖銳的指控,並似乎贊成人類對自我決定的傾向。奴隸主基督教與非洲靈性之間的摩擦產生了火花,這些火花吸引了人們對這部戲劇關於完全抹去一個人文化方面並用另一種文化取代它們所帶來的危險以及本質上的不可能性的主要資訊。霍利寄宿公寓的常駐巫師拜納姆·沃克,最能捕捉到反對為了團結而進行的文化抹去的反應:“我是一個粘附物的束縛者,”他指出。“你必須先弄清楚它們是否粘附。你不能束縛那些不粘附的東西。”威爾遜戲劇中的每一個延伸都是對基督教作為他非裔美國人生活中積極力量的憤世嫉俗的看法。在盧米斯的情況下,給一個所謂的“尋人者”的一美元鈔票代替了可能對上帝的幫助的熱切祈禱。此外,對宗教虔誠的表現充滿了尖刻的憤世嫉俗和褻瀆。例如,在懷疑的盧米斯和被拯救的瑪莎最終面對彼此的場景中,他透露,對他來說,耶穌基督已經變成了一個“大個子的白人”……先驅者盧米斯,曾經是約瑟夫·特納連鎖幫的成員,也是基督教教堂的執事,直接拒絕了他妻子對宗教的熱情,他揮舞著刀子,在自己的身上劃了一道口子,這個動作反映了耶穌基督的釘十字架。他戲劇性的自我傷害,再加上他與上帝的突然的陰莖對峙——“為什麼上帝必須如此巨大。為什麼他必須比我大?你想多大了?”——表明盧米斯不願意接受這種新的、陌生的宗教的程度。事實上,他評論的嘲諷語氣以及他對上帝無所不能的公開挑戰,再加上他在劇本的最後一幕中願意在自己的身上劃一道口子,都反映了非裔美國人戲劇中相對較新的絕望程度”(Shannon,2018 年第 146-147 頁)。“幾乎劇中的每個人都在尋找某個人,他們向兩種奇妙的神話型別尋求幫助——在許多方面類似於易卜生的《小艾爾夫》中的老鼠妻子——尋人者和粘附物的束縛者”(Shafer,1995 年第 274 頁)。“先驅者盧米斯對角色參與舞蹈的感到不安的是那種社群感、團結感、非洲的返祖遺產以及戰後一代意識中依然存在的奴役感,所有這些都與他渴望自治形成鮮明對比……沃克的目的,他的歌,都包含在他的名字中:“拜納姆”,將人們束縛在一起,讓他們在內心發現一種真理感;“沃克”,漫遊者,尋求者……劇中必須有一個反派,諷刺的是,反派是主角,一個名叫先驅者盧米斯的假釋犯。他將成為先驅,閃耀的人,那個知道所有之前發生過的事情的人,就像沃克父親的鬼魂所預言的那樣”(Bogumil,2011 年第 61-70 頁)。“在救贖自己時,[盧米斯]必須克服他對一個偏袒上帝的盲目屈服,這個上帝存在是為了促進奴隸制體系的利益……從本質上講,他意識到自己必須重生,但不是以新約基督教的典型意義……盧米斯,儘管他拒絕了“耶穌基督先生”,因為他無法將他與約瑟夫·特納區分開來,但他仍然擁有自己的舊約式的景象,並在劇本的結尾切開自己,用自己的鮮血淨化了自己的存在”(Young,2004 年第 132-135 頁)。“盧米斯的憤怒是積極的,因為如果它不是由他被迫的苦役引發的,他就永遠不會意識到自己與非洲的聯絡……[當他看到朱巴時],盧米斯以這種方式做出反應,因為他與任何型別的精神都沒有聯絡,無論是基督教還是非洲……拜納姆將盧米斯與過去聯絡起來的第二種方式是演唱與約瑟夫·特納有關的歌曲。為了讓盧米斯知道自己要去哪裡,他必須承認自己從哪裡來……[盧米斯變得憤怒,因為] 他認為他只需要瑪莎……他不需要瑪莎,也不必躲避特納……盧米斯意識到他在被囚禁之前所信仰的基督教讓他失望了;因此,他回到了非洲傳統宗教……盧米斯需要找到瑪莎,以便在世界上獲得立足之地……透過將她與特納等同起來,阻礙了他的生活,盧米斯喚起了與理查德·賴特作品中的人物(如比格·托馬斯和西拉斯)的比較;兩者都指責黑人女性造成了他們的困境,並且兩者都將黑人女性與一個陰謀的白人壓迫體系聯絡起來”(Harris,1994 年,第 56 頁)。“雖然瑪莎為自己的行為提供了合法的自我保護理由,但在先驅者的腦海中,她拋棄了他,為自己建立了一個新的生活,為白人上帝服務。背叛是如此嚴重,以至於他無法回到她身邊,也無法回到她的教堂。在將女兒歸還母親時,先驅放棄了他與根植於白人統治的宗教和家庭過去的聯絡……雖然劇作家賦予了他的英雄重新創造自己的自由,但他將這個主要女性角色不可磨滅地刻在了壓迫性的刻板印象中”(Marra,1994 年第 137-138 頁)。雖然瑪蒂可能是在劇中的整個過程中尋找她的丈夫,但她真正尋找的是什麼,根據伯莎和拜納姆的說法,是一個發現了自己的男人”(Tyndall,2004 年第 160-171 頁)。

時間:1936 年。地點:美國匹茲堡。
男孩威利和萊蒙來到鎮上出售一大車西瓜。男孩威利還想和姐姐伯尼斯一起出售他擁有的鋼琴,以購買一個最近去世的人(薩特)的兄弟擁有的農場,而薩特曾經是他們祖父母的奴隸主。儘管她已經很多年沒有彈過這架鋼琴了,但伯尼斯拒絕出售,因為她認為這架樂器是家族傳家寶,他們的祖父在木頭上雕刻了他們家族歷史的照片。男孩威利和伯尼斯的父親認為,只要薩特擁有這架鋼琴,他們就仍然是他的奴隸,於是他們連同男孩查爾斯一起從他那裡偷走了這架鋼琴。當薩特發現盜竊行為時,他非常憤怒,燒掉了父親的房子。他在一輛貨車裡發現了他,和他一起的還有四個流浪漢,他與警長一起點燃了貨車,將他們燒死在裡面。在多年的時間裡,一些參與謀殺的人被扔進井裡喪生,根據傳說,這是黃狗鬼魂的功勞,這個名字來源於火車,因為它的汽笛聲和貨車的黃色。伯尼斯懷疑是男孩威利自己把薩特推進了井裡。這就是她、她的女兒以及她已故丈夫的兄弟杜阿克被薩特的鬼魂纏身的假定原因。在賣掉了大部分西瓜後,男孩威利和萊蒙慶祝。深夜,男孩威利帶著一個新交的女朋友回到了姐姐家,但伯尼斯把他們趕走了,並拒絕了萊蒙的性侵犯。第二天,男孩威利和萊蒙感到困惑,因為他們無法再移動鋼琴了。他們使用了帶輪的木板和繩子,但伯尼斯打斷了他們的努力。一個沮喪的男孩威利覺得擁有農場將使他和白人平等。他一生都感到處處不受歡迎。“這個世界不想擁有我的一部分,”他宣稱。但是,當他試圖在伯尼斯威脅和知道姐姐帶著槍的情況下移動鋼琴時,他莫名其妙地被彈回去了。對這種結果感到滿意,她坐下來彈奏它。

時間:1911 年。地點:美國匹茲堡。
文字位於 https://pdfcoffee.com/joe-turner-s-come-and-gone-august-wilson-pdf-free.html https://www.hackensackschools.org/site/handlers/filedownload.ashx?moduleinstanceid=925&dataid=7635&FileName=august%20wilson%20joe%20turner_s%20come%20and%20gone.pdf
魯弗斯帶來了一塊金屬板,以便塞斯能為他製作簸箕。拜納姆,塞斯寄宿公寓裡的房客,問魯弗斯,因為他是一個“人肉搜尋器”,他是否見過他的“閃光人”,一個“身上發出光芒”的人,曾經帶他走過一條通往所有事物都更大的道路。“他說他一直在想我,”拜納姆談到那個人時說道,“他很傷心看到我帶著別人的歌曲而沒有自己的歌曲。”魯弗斯沒有見過他。塞斯訓斥了另一位房客傑里米,因為他因醉酒行為被捕。但傑里米否認自己和朋友喝了半品脫酒,當白人出現逮捕他和罰款他兩美元時,他甚至沒有喝過一口。“他們抓住我們是為了得到那兩美元,”傑里米解釋道。之後,赫拉德·盧米斯帶著他的11歲女兒佐尼亞出現了,他們正在尋找一個住處,同時想要找到他離開自己的妻子。塞斯同意讓他們住下,按照妻子的建議,允許佐尼亞透過幫忙做家務來支付房租。僅僅是看著佐尼亞的臉,塞斯就知道母親是誰,一個當地名叫瑪莎的女人,但他沒有向看起來可疑的赫拉德透露這個資訊,據說是教堂的執事。之後,馬蒂出現了,她也想找回她的配偶。她請求拜納姆的幫助,一個以能將人綁在一起而聞名的人,但他拒絕了,理由是當她的兩個嬰兒死去時,她的丈夫離開了,這表明他應該離開。馬蒂的外表很快吸引了傑里米,他邀請她去公共場所聽他彈吉他。她答應了。聽到魯弗斯作為“人肉搜尋器”的聲譽,赫拉德僱傭他尋找他的妻子。傑里米比以往更加愛慕馬蒂,同意額外支付塞斯一筆錢,讓她住在他的房間裡。但當莫莉出現尋找房間時,傑里米仔細地看著她。一天晚上,當塞斯、拜納姆和傑里米一起演奏音樂,唱著非洲節奏的歌曲時,赫拉德打斷了他們,訓斥他們使用聖靈的名字,宣稱他有異象,開始脫衣服,最後被拜納姆安撫了下來,拜納姆問他關於他的異象。“我親眼看到骨頭從水中升起,升起來穿過水麵,骨頭走在水上。”赫拉德恢復後,憤怒的塞斯讓他離開這所房子。赫拉德已經付了錢,他只同意在這一週結束時離開。傑里米告訴塞斯,他因為拒絕向一個白人支付五角錢的保護費來保住工作而失去了工作,塞斯認為這是一個愚蠢的舉動。無論如何,傑里米想和莫莉搬走。“莫莉不會工作,”莫莉告訴他。他同意了。在玩多米諾骨牌時,拜納姆唱著“喬·特納來了又走了”。“我不喜歡那首歌,先生,”赫拉德警告道。“我的妻子瑪莎在喬·特納抓住我之後就離開了。”幾年前,他試圖說服一些人停止賭博,結果他和其他人一起被捕,並被判處7年監禁。魯弗斯找到了瑪莎,把她帶到赫拉德身邊,但是,儘管她已經努力尋找他多年,但她現在拒絕跟隨,只答應帶佐尼亞一起走。為了減輕他的失望,她鼓勵他擁抱為他流血的基督。“我不需要任何人為我流血,”他反駁道,然後離開了,“我可以為自己流血。”“赫拉德·盧米斯,你閃耀著,你閃耀得像新錢一樣,”拜納姆興奮地說。
TS 艾略特
[edit | edit source]
同樣令人感興趣的是社會諷刺劇《雞尾酒會》(1949年),作者托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1888-1965)。
在一封寫給露西·沃爾夫的信中,易卜生於1883年5月25日寫道,“詩歌對戲劇藝術最有害。一個以當代戲劇為領域的人物設計師應該不願意把詩歌放在嘴裡。詩歌不太可能在未來的戲劇中得到廣泛應用,未來的劇作家們幾乎肯定不會與詩歌相容。因此,詩歌註定要消失”(亨德森,1914,第192頁)。幸運的是,艾略特對戲劇藝術有不同的看法。然而,“艾略特憑藉《雞尾酒會》和《機密文員》試圖將他的戲劇詩歌儘可能地接近散文,結果過於成功”(加斯納,1960,第279頁)。
《雞尾酒會》“在它機智對話的輕鬆愉快的氣質中,在它自己的領域,打敗了諾埃爾·考沃德先生這樣的劇作家,在他最好的狀態下。與此同時,《雞尾酒會》有一個深刻的嚴肅的主題,即即使是在我們不安的社會中,即使是受過教育、友善和善意的人也傾向於沉迷於各種自我欺騙,就像沉迷於藥物一樣,以及自我欺騙如何阻止人們過上他們本該過上的生活,做他們本該做的事情,追隨他們真正的使命...很明顯...心理醫生不是一個純粹的心理醫生,而是一個群體中的一員——另外兩個人是一個愛說閒話的老婦人和一個愛開玩笑的城裡人——他們要麼承擔了,要麼以某種神秘的方式被賦予了他們圈子裡那些不那麼開明的人的精神監護人的角色。他們認為,一句話,他們的職責是幫助靈魂免於受苦;同樣,在實踐層面上,也要避免生活、有用的東西遭到破壞和浪費。如果丈夫和妻子被監護人引導到一個體面、普通的婚姻的軌道上,那麼那個曾經是丈夫情婦的女孩就是一個更加特殊的人,她逐漸被引導接受的職業是傳教士;一種職業,將在很短的時間內導致她在一個原始的國家殉道。那個愛她的年輕人,同時也是妻子的情人,有文學抱負,這些抱負還沒有完全消失,但他一直以一種誇大的自我為中心的觀念來思考自己的重要性和自己的才華;他被監護人送去從事更實際的工作,他將在那裡做得很好,同時擺脫一些自我中心,在好萊塢的電影行業工作。但這個年輕人也擁有很高的精神潛力,當他在最後一幕中得知他長期秘密愛慕的女孩殉道的訊息時,我們看到這個訊息在他體內引發了一種痛苦但健康的內心覺醒。然而,最後一幕主要關注的是丈夫和妻子——女孩的可怕死亡,自然,只是被報道,它不是舞臺上的行動的一部分——它表明,在接受了適合他們氣質的婚姻生活的秩序和侷限性之後,他們能夠從中創造出一些快樂和有創造力的東西。他們現在比以前更成熟、更討人喜歡。 ”(弗雷澤,1960,第156-158頁)。
《雞尾酒會》是一部“尖酸刻薄的世俗喜劇...[但]作為一部戲劇,它主要受到第三幕中最有趣的人物缺席以及她去非洲的故事被改編為報道的困擾。這部作品在頭兩幕中一直保持著緊張感,但在此之後就消失了,恰恰是在它應該達到高潮的時候。在第三幕中,重聚的錢伯萊恩夫婦表現出良好的教養和情感,但他們對重聚的理解並沒有太大的戲劇意義。他們後來的生活也沒有給亨利·哈考特-萊利爵士增光,他是一位非凡的心理醫生,也是哈利街的父親般的告解者。如果他所做的一切僅僅是雞尾酒會的現狀,那麼他神秘的地位就顯得不那麼令人印象深刻,而塞莉亞·科普爾斯坦的靈魂救贖卻發生在舞臺之外。幸運的是,第三幕的“高階喜劇”氛圍將我們帶回了第一幕的環境(雖然情緒有所加深)”(加斯納,1954a,第730-731頁)。“適合於似乎無限期持續的雞尾酒會,亞歷克斯的所有故事都是不完整的”(帕蒂,2012,第100頁)。“許多...20世紀的戲劇包含形式主義的元素。《雞尾酒會》的高潮是第二幕,在這一幕中,心理醫生兼監護人萊利博士以及他的助手茱莉亞和亞歷克斯承擔了宗教職能。他們用雞尾酒杯進行了一種類似於彌撒的儀式”(加斯納,1956,第169頁)。“艾略特先生在以心理分析師為主導的場景中表現得最出色,而在試圖描寫客廳裡脆弱的閒聊時,他卻顯得最不機智,最乏味。當他的筆觸既尖刻又嚴肅時,他的思想的活力和他對語言的精確控制最為強烈”(布朗,1963,第194-195頁)。
寫宗教劇的英國劇作家“似乎只與撒旦有點頭之交,而且他們沒有什麼可懺悔或超越的東西值得展現給公眾...我們在這類戲劇結束時所知道的是,作者反對罪惡和錯誤,”這與充滿活力的蒙泰朗的《亡國皇后》(1942年)和《聖地亞哥的主人》(1948年)不同”(第430頁)。艾略特提出“人類錯誤的無必要性和透過社會啟蒙來糾正錯誤的可能性...艾略特從一開始就預言了失敗:沒有救贖的生活就是生活在原罪的陰影下,即使是自己沒有聖化就過上滿意的生活,也只不過是把一個糟糕的交易做到最好,這就是世俗的錢伯萊恩夫婦的命運...艾略特將雞尾酒會變成了一部既沒有狂喜的道德劇——儘管第一幕和第三幕有世俗喜劇,也沒有理性主義——儘管亨利·哈考特-萊利爵士作為心理分析師的角色。他角色的獨特之處在於,他的病人期望他在他的辦公室裡接受理性主義或科學治療,而他只提供道德和神秘的幫助”(加斯納,1954b,第269-277頁)。
“《雞尾酒會》,改編自歐里庇得斯的《阿爾凱斯提斯》,描繪了被近乎病態的猶豫不決困住的角色。他們迫切需要陪伴,卻註定要感到孤獨”(D’Monté,2015,第174頁)。“在歐里庇得斯的劇本中,阿爾凱斯提斯同意為了救丈夫的命而死,而總是熱衷於做好事的赫拉克勒斯決定將她從冥界帶回來。阿爾凱斯提斯對應著拉維尼亞和塞莉亞,也就是說,對應著女性氣質的兩個方面和一般生活中的兩個層次。拉維尼亞並沒有為了救丈夫而死;她只是把他獨自留下,以便讓他找到自己。當他們兩人在分別經過一段短暫的旅程——不是穿過沙漠,而是穿過生活——之後再次相遇時,他們都學會了避免過高的期望;他們現在都知道,他們彼此不理解,他們必須盡力過上平凡的生活。塞莉亞是犧牲自己的女人。她開始像拉維尼亞、愛德華和彼得·奎爾普一樣,生活在黑暗中,生活在一個盲目或部分盲目的世界裡,他們都必須從那裡走向一種光明。但一旦塞莉亞被恩典觸碰,並獲得了對真正生活的洞察,她就無法再接受妥協和平凡的生活,她成為了一個預定的殉道者”(齊亞里,1965,第96-97頁)。
波特 (1969) 指出,愛德華想要拉維尼亞回來,而彼得想要塞莉亞。愛德華-拉維尼亞這對夫婦的失敗本來可以被彼得-塞莉亞這對夫婦的成功所抵消,但塞莉亞的愛並沒有指向彼得(第 59 頁)。相反,她傾向於成為一個基督般的人物,她的死亡最終可能會鼓勵彼得放棄他虛假的生活,擁抱一個更真實的自己。在霍布森 (1953) 的觀點中,愛德華的困境是不愛任何人,因此他選擇了“一種平淡無奇的婚姻之路”(第 7 頁)。當諮詢雷利時,塞莉亞選擇贖罪而不是和解。關於她的暴力結局,威廉姆斯 (1965) 寫道:“人們經常說塞莉亞的動機沒有根據,這部戲劇沒有讓我們為她的決定做好準備。在我看來,這種批評是一種合理化,掩蓋了對她的經歷本質的根本反感。‘盡力而為’是一種常見的當代道德,戲劇的大部分內容都在這個可以接受的層面上進行。但艾略特似乎故意挑起了塞莉亞經歷、決定和死亡的震驚。透過讓雷利成為遵循兩種道路的人的守護者,他在最引人注目的方式實現了特定價值觀模式的實現”(第 242 頁)。布蘭特 (1962) 指出,愛德華的結論“地獄是自己,地獄是孤獨,其中的其他人物僅僅是投影”,與薩特 1942 年的《沒有出口》中加爾森的結論相反。
"雞尾酒會"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40 年代。地點:英格蘭。
文字位於 https://archive.org/details/in.ernet.dli.2015.97677 https://archive.org/details/in.ernet.dli.2015.525194 https://archive.org/details/dli.ernet.16283 https://archive.org/details/dli.ernet.528539 https://archive.org/details/dli.ernet.524184 https://archive.org/details/dli.ernet.526696 https://archive.org/details/dli.ernet.524620 https://kupdf.net/download/the-cocktail-party-pdf_5afbe151e2b6f500118749ae_pdf
拉維尼亞在她和愛德華家舉辦的雞尾酒會前夕離開了丈夫愛德華。一位不速之客出現並與他交談。“她不會回來的希望很大,”客人向他保證。“但我想要我的妻子回來,”愛德華抗議道,他覺得這種猜測很冒犯。“你不過是一套過時的反應,”客人反駁道。“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什麼也不做。等待。”但由於他不願意等待,客人承諾他的妻子將在一天內回來。愛德華的情人塞莉亞隨後也來了,她希望得到保證,他們的關係是穩定的。他退縮了。“這不能繼續下去,”他肯定地說。正如客人預測的那樣,拉維尼亞第二天確實回來了。夫妻倆立即開始相互抱怨。他指責她總是試圖把他變成她想要他成為的樣子,以至於他覺得自己的個性消失了。“地獄是自己,地獄是孤獨,其中的其他人物僅僅是投影,”他告訴她。反過來,她指責他從不費心去理解她。他同意諮詢精神科醫生亨利·哈科特-雷利博士,他就是那位不速之客。讓愛德華驚訝的是,拉維尼亞出現了,更讓他驚訝的是,她透露她也曾有過婚外情。在聽完他們的抱怨後,哈科特-雷利得出結論,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可以努力:他受苦於不愛任何人,而她受苦於不被愛。在他們之後,塞莉亞也進行了諮詢,她忍受著孤獨和可怕的空虛感。“我們只能愛我們自己想象出來的東西嗎?”她想知道。哈科特-雷利鼓勵她追求崇高的理想。“如果你有勇氣,還有另一種方式,”他說。“但這條路通往佔有 / 你在錯誤的地方尋找的東西。”“聽起來像是我的願望,”她宣佈。為了逃離她不幸的命運,她前往國外當護士,但在當地土著起義中成為受害者。
卡森·麥卡勒斯
[edit | edit source]
卡森·麥卡勒斯 (1917-1967) 的家庭劇《婚禮的成員》(1950) 動人地講述了女性青春期。對話的主要部分取自同名小說,但有一個重要的改動:弗蘭基和那個好色計程車兵之間沒有任何相遇。
阿特金森 (1974) 愚蠢地誤解了《婚禮的成員》,將其視為“一個青春期女孩愚蠢瑣事”的總和(第 410 頁)。相比之下,加斯納 (1954b) 寫道,這部戲劇“透過僅僅成為一個對一個女孩青春期(她從假小子階段成長起來)的細緻觀察,變得有說服力並具有啟發性。與這個描述平行的是另一條几乎沒有情節的興趣線索:一位照顧這個女孩的黑人女傭的生活”(第 78-79 頁)。
“通常被稱為一部一流的敏感喜劇,這部引人入勝的內向戲劇在很大程度上被構建為一個人物素描,或者說三個人物素描,而不是一個精心編排的敘事。劇中的行動是在兩個介紹性章節中發生,這兩章敏感地關注氛圍和人物以及情感的細微差別……弗蘭基對成年世界感到困惑和害怕,她衝動地在這兩種選擇之間反覆橫跳:逃避它,然後夢想,或者荒謬地計劃進入它……[麥卡勒斯] 將一個熟悉的家庭環境和普通人物……賦予了吸引人的溫暖”(赫倫,1969 年,第 398-400 頁)。
“這部戲劇的主題是……精神上的孤立——這種孤立導致壓抑的孤獨,渴望歸屬,而如果無法實現,就會產生逃避的需要……第一幕……是弗蘭基·亞當斯對其問題的客觀、內心強迫的分析——一個多方面的難題,她反覆地回到它,因為她在尋找一個解決方案,一個能夠減輕她精神孤立感的解決方案,並治癒她深深的孤獨。她尋求解決方案的兩極性成為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歸屬的必要性,否則就從她有限的世界逃到外部世界——在她看來,在第一幕的最後,她發現自己一直是一個“我”的人,而她是她認識的唯一一個不屬於“我們”的人。第二幕在很大程度上是貝勒尼斯為讓弗蘭基意識到現實而設計的一個關於愛情和死亡的怪誕寓言,為了帶她超越她的幻想,讓她明白一個人不能僅僅決定自己想做什麼,而不顧理智……在第三幕的最後一幕中,弗蘭基——現在更準確地被稱為弗朗西斯,就像她在小說中一樣,因為她現在正在發展一個適當的女性性別角色認同——從廚房獲得了自由。弗蘭基與瑪麗·利特爾約翰建立了親密、正常的青少年友誼。很有意義,象徵意義重大,弗蘭基和瑪麗在沃爾沃斯化妝品櫃檯前認識了彼此。弗蘭基對自己精神上的自我認知——一種精神上的現實,是她自我概念的核心——隨著她的女性認同的出現而逐漸改變,這種認同以化妝品櫃檯為象徵”(德德蒙德,1975 年,第 50-52 頁)。
“悲傷圍繞著貝勒尼斯,她哀悼她第一個(也是四個中的第四個)丈夫,他的死亡在她人生中開始前的 13 年前就留下了揮之不去的空虛……貝勒尼斯,就像廚房一樣,既提供庇護,也提供生計。她傾聽弗蘭基的煩惱;與兩個孩子玩紙牌;修改弗蘭基買來參加婚禮的裙子;做飯和招待客人;做婚禮蛋糕、餅乾和三明治;照顧孩子;洗碗。弗蘭基依靠貝勒尼斯尋求安慰,但也嘲笑她沒有能力理解任何事情,指責貝勒尼斯犯下的錯誤和限制。在一次特別對抗的時刻,弗蘭基用一把雕刻刀威脅貝勒尼斯”(陳思安,2015 年,第 158-160 頁)。
“麥卡勒斯將霍尼·布朗改寫為一個脾氣暴躁的格格不入者,公開反抗白人對服從的要求。在小說中,他只是太過敏感,無法安分守己地生活在糖果鎮,在劇中,他積極地反抗順從,當弗蘭基的父親堅持讓霍尼稱呼他為‘先生’時,他反抗了,並譴責了他的黑人朋友 TT 威廉姆斯為了順從而這樣做:“TT 對‘先生’這個詞的稱呼已經足夠一群黑鬼了,”霍尼指責道。“但對於那些叫我黑鬼的人,我有一把非常鋒利的黑鬼剃刀”(詹姆斯,2002 年,第 55 頁)。
"婚禮的成員"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45 年。地點:美國南部。
文字位於 https://archive.org/details/in.ernet.dli.2015.3318 https://archive.org/details/dli.ernet.235460 https://archive.org/details/in.ernet.dli.2015.60953
Jarvis,一名士兵,即將與Janice結婚。他 12 歲的妹妹 Frankie 對她懷有嫉妒之情。“我敢說他們每天每一分鐘都過得很開心,”她對 Berenice,他們的黑人女僕說道。Frankie 因為被拒絕加入一個女孩俱樂部而感到沮喪。當 Berenice 取笑她時,她拿起一把雕刻刀威脅她。他們的談話被打斷了,因為 Berenice 的追求者 T.T. 與她的養兄 Honey 一同到來,Honey 的頭部在與一名士兵發生爭執後被警察擊中。厭倦了住在父親家裡的 Frankie 想去與她的哥哥和他的新娘住在一起。“我非常愛他們兩個人,因為他們是‘我們’的一部分,”她向她 7 歲的朋友約翰·亨利傾訴道。為了婚禮,她給自己買了一件橙色的緞面連衣裙,配上銀色的長襪和鞋子。Berenice 和 T.T. 認為這太成熟了,但既然無法退貨,她就決心把它修好。Berenice 意識到 Frankie 對這對準夫妻太關注了,她告誡 Frankie 熱烈愛一個人是有危險的,就像她自己曾經對 Ludie 一樣,他是她的四個丈夫中的第一個。“我做的就是,只要遇到他們的一部分,我就把他們嫁出去,”她解釋說。“只是我的不幸,他們都是錯誤的部分。”在這次談話中,約翰·亨利開始感到不舒服,但兩人都忽略了他的抱怨。在婚禮儀式上,經過多次猶豫,Frankie 告訴她的哥哥她想追隨他和他妻子,但他拒絕了。心碎的 Frankie 帶著她父親的槍離開了家。她的父親和 T.T. 匆匆追趕,但找不到她。最後,她不知道該去哪裡,就獨自回到了家。Honey 也回來了,之前他與一名拒絕他在餐館招待他的白人發生了爭執。他拔出一把剃刀割傷了對方。儘管 Berenice 交了錢幫助他逃脫警方的追捕,但他還是被抓住了,並在牢房裡上吊自殺。約翰·亨利被診斷出患有腦膜炎並去世了。當 Frankie 的父親決定和他的姐姐搬到另一所房子時,Berenice 辭去了他的服務。雖然 Frankie 承諾會去看她,但 Berenice 懷疑她是否會去。
在家庭劇的領域中,羅伯特·安德森(1917-2009)的《茶與同情》(1953)也值得注意,這是一部“關於一名在私立學校被懷疑是同性戀的少年痛苦的感人戲劇”(阿特金森,1974 年,第 440 頁)。
“這是一部深刻的戲劇,它對愛情的不同態度進行了深刻而富有啟迪性的解讀。這部引人入勝的三幕劇講述了三個不安全的人的故事:一名 17 歲的學生,因為理想主義和敏感而被誤解;一名心腸善良、感情豐富的女校長妻子,她的情感戰勝了她的理智;以及她的運動員丈夫,因為他自己的不安全感而對他人缺乏同情,甚至冷酷無情。新英格蘭小鎮的一所精英且歷史悠久的男子學校為一系列尷尬的境況提供了有限的背景,這些境況構成了社群的糾葛”(赫倫,1969 年,第 460 頁)。“茶與同情”是一部關於受害者的研究,美國作家對此駕輕就熟,並經常描寫。在這部戲劇中,受害者是一名少年……[他的] 陷入絕望的境地加劇了來自他不理解的父親的輕率的激勵和來自他的舍監的冷酷敵意,舍監的咄咄逼人的男子氣概只是為了掩蓋長期壓抑的同性戀傾向。正是舍監的生活……透過與他上床來解決了男孩的疑問……而且……這個過程……往往非常感人”(泰南,1961 年,第 172 頁)。“安德森的《茶與同情》可以……像海爾曼的《孩子們的時刻》(1934 年)一樣,被視為對由於不經意地暗示而帶來的危險的警示,因為孩子們傳播著關於湯米和學校的一位老師的謠言……年輕的教職工妻子勞拉透過指出人們錯誤地將他們不喜歡的人作為攻擊目標來為湯米辯護,而沒有任何真正的證據反對他們,我們瞭解到這位老師也失去了職位,沒有任何聽證會或機會面對他的指控者”(阿博特森,2018 年,第 76 頁)。
“《茶與同情》和《寂靜之夜,孤獨之夜》(1959 年)表明,應該拋開傳統的道德規範,轉而及時對需要幫助的人做出回應……[在他的戲劇作品中],很少有角色能與勞拉·雷諾茲相比,她是《茶與同情》中溫柔、富有同情心的校長妻子,以及湯姆·李,一個敏感而被誤解的學童”(斯坦頓,1980 年,第 91-92 頁)。“勞拉理解……‘男子氣概……必須包括……溫柔、體貼、考慮周到’,這些品質……傳統上……被認為是女性氣質,而男性……則壓制了這些品質。安德森抨擊了這種人造的、文化強加的男性和女性原則之間的分界……它是一種扭曲的思維方式,產生了像赫布·李和比爾·雷諾茲這樣的人,他們摧毀了自己內心的情感生活,並壓制了其他人情感的發展……但如果勞拉再也不能幫助比爾,那麼她現在可以幫助湯姆……正如她所懷疑的那樣,湯姆在性事方面幼稚得不像他的年齡……因為他與父親的交流……幾乎不存在……最終促使湯姆去埃莉那裡的是勞拉的拒絕……後來,勞拉明白,促使她在內心有想法的情況下卻說‘不’的社會和道德約束是錯誤的,並且導致她在危機時刻讓另一個人失望……勞拉把自己交給湯姆……滿足了她被需要的需求,但除此之外,它還滿足了一個渴望性愛的女人的需求”(阿德勒,1978 年,第 74-80 頁)。然而,“自從最後的帷幕落下後,關於性治療是否會對這個男孩有效,我們真的無從得知”(科廷,1987 年,第 297 頁)。
劉易斯(1965 年)發現勞拉為湯姆解開襯衫釦子的結局場景“與故事情節的邏輯關係不大”(第 156 頁)。然而,當我們把它看作不是出於同情,而是出於對青年的自發愛和對不誠實的丈夫的怨恨時,它就合乎邏輯了,整個故事都突出了男孩和男人之間的對比。此外,由於性是問題的核心,因此也是解決方案的核心。阿德勒(2007 年)批評了同一場景,因為他認為“性行為”被呈現為“救贖的,是萬靈藥或對一個人疾病的輕而易舉的治癒方法”(第 167 頁),這是一種過於清教徒的觀點。相比之下,加斯納(1953 年)贊同結局,因為它講述了一個男孩“被學校和父母誤判為同性戀……故事本身很有吸引力,它展示了同學和長輩的遲鈍或冷酷如何毀掉一個男孩的生活。當校長妻子在湯米與當地一個隨便的女人發生性關係後,把自己給了這個男孩,以確保他對自己的男子氣概沒有疑問,故事情節就有了新奇而大膽的轉折,使《茶與同情》超出了學校戲劇的《年輕的伍德利》的範疇。然而,這不僅僅是一個故事情節的轉折,因為安德森先生已經將其與女人的家庭生活中存在的緊張關係聯絡起來,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行動心理上的可信度,並用任何人都可能希望的溫柔來處理男孩和已婚女人之間的和解”(第 353 頁)。

時間:1950 年代。地點:美國新英格蘭。
文字位於 https://archive.org/details/in.ernet.dli.2015.86608
勞拉是男子學校的一位舍監比爾·雷諾茲的妻子,她正在為湯姆準備一套戲服,湯姆是一位 17 歲的寄宿學生,住在他們家,即將在一部戲劇中扮演女性角色。他們的試裝被打斷了,因為老師大衛·哈里斯很擔心他的合同是否會被續簽,因為湯姆透露他們上週六晚上在沙丘上一起游泳。湯姆否認對院長說了什麼。不久之後,比爾告訴勞拉,兩名來自校隊的男孩看到了這個男人和這個男孩赤裸裸地躺在沙丘上。勞拉很沮喪,因為她與之交了朋友的湯姆可能會被開除。比爾回答說湯姆應該被開除,勞拉不應該與任何學生有感情上的牽扯,而應該像校長夫人建議的那樣,僅僅提供他們“茶與同情”。儘管沒有發生性交,但大衛還是被解僱了,但湯姆被假定無罪。然而,湯姆的父親赫布是比爾的老校友,他堅持要求湯姆放棄在戲劇中的角色,並且勞拉邀請一個女孩來,這樣她就可以代替她成為湯姆的舞伴。結果,湯姆感到困惑和受傷。壓力越來越大,因為當他在體育課和網球訓練後走進淋浴間時,男孩們從淋浴間走出來,而比爾則表現出冷淡、蔑視的態度。此外,湯姆的室友阿爾受到他父親的騷擾,搬到另一個房子,遠離他父親的影響。為了恢復名譽,阿爾建議湯姆去見埃莉,她是一家蘇打水店的侍應生,眾所周知,她對學生很隨便。湯姆在電話里約她週六晚上約會,勞拉聽到了他們的談話,她在那晚試圖透過拖延時間來阻止他們見面。當她教他跳舞時,他熱烈地吻了她。當她拒絕他時,湯姆逃到了埃莉的住處,但過度興奮的男孩無法勃起。在他的混亂狀態下,他試圖自殺,但埃莉阻止了他。然而,他們爭執的聲音引起了校園警察的注意,湯姆被開除了。勞拉對她的丈夫參與了對湯姆的折磨感到憤怒和受傷,她說她想離開他。“你有沒有想過,你在湯姆身上,那個在上面的男孩身上,你在他身上迫害了你害怕的自己?”她問他。聽到這個指控後,他想要她離開。當她走進湯姆的房間,想鼓勵他時,他仍然很沮喪,確信自己不是男人。但是,當她解開襯衫釦子時,他開始做出反應。“多年以後,當你談論這件事的時候——你會談論的——要善良,”她懇求道。

洛林·漢斯伯裡(1930-1965)在《陽光下的葡萄乾》(1959)中創作了一部優秀的家庭戲劇。該劇的標題取自朗斯頓·休斯(1902-1967)的一首名為《哈萊姆》的詩:被延遲的夢想會怎樣呢?/它會像陽光下的葡萄乾一樣乾枯嗎?/還是像潰爛一樣腐爛然後流淌?/它會像腐肉一樣臭嗎?還是像糖漿一樣結痂和變甜?/也許它只是像沉重的負擔一樣下垂。或者它會爆炸?
威爾克森(1986)介紹了20世紀50年代白人與黑人隔離的歷史背景。“在1955年……最高法院宣佈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是非法的,這標誌著數十年倡導和法律挑戰的高潮,但也開啟了新的抵抗階段。”這位評論家還指出了該劇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對中心人物的刻畫。“莉娜·揚格是一個強烈的認同點。她是每個人的媽媽——堅強、關愛、堅定,是維繫家庭的粘合劑。露絲的沉默力量和奉獻天性展現出妻子和母親的自我犧牲之愛。雖然沃爾特·李對白人觀眾來說是一種新的人物,漢斯伯裡有意將其塑造為‘貧民窟英雄’,但他與母親之間的代溝卻非常熟悉。對於黑人來說,沃爾特是對黑人鬥爭的緊迫性和力量的肯定,而他的妹妹貝內特則代表了黑人鬥爭的知識潛力……人物既沒有被情感化,也沒有被刻板化……然而,沃爾特·李的困境提出了以下問題:‘為了物質上的進步,楊格一家是否也必須變得物質主義?獲取、權力和地位的有利可圖的經濟價值與正直、正義和自由的‘無利可圖’的價值之間的矛盾在美國人的心理中根深蒂固”(第443-445頁)。
該劇的“行動從鬧鐘的鈴聲開始,這在作品的其餘部分中象徵性地迴響。的確是時候醒來了,這部劇實際上關注的是一個黑人家庭覺醒的意識,因為他們開始意識到將社會價值觀內化對自己感官和身份的影響。這筆遺產使他們第一次有能力挑戰那些將他們禁錮在貧民窟的明文和不成文的規則,他們的希望註定無法實現,這也迫使他們面對他們一直都知道但沒有必要承認的界限的現實”(Bigsby,1985 年第 381-382 頁)。
“媽媽的表達方式是她的家庭表演:照顧家庭的行為,產生了以警惕的母親試圖阻止入侵者進入家門,從而保護家人免受監視脆弱性的敘事。這種敘事透過媽媽對盆栽植物的依戀變得可見且引人注目……多次,媽媽將植物移進移出房子,尤其是在她孩子的未來岌岌可危的時候……媽媽明白,植物的生存,就像她孩子的生存一樣,直接與它從外部環境中獲得的東西有關。雖然她允許她的植物冒險到外面,但她就在那裡把它拉回來”(Kiser,2020 年第 446 頁)。
“與媽媽不同,媽媽將生活視為自由,沃爾特·李·揚格將自我表達等同於物質利益和財富,他的抱負反映了戰後黑人人口中的一部分,他們認為獲得資本將確保進入‘好’社會……雖然她不贊成沃爾特與威利和波波開一家酒館的計劃,但露絲同樣把自己安置在美國夢的門廊裡,因為她希望從家裡的南區‘老鼠陷阱’中逃脫出來。然而,露絲的夢想包含了從一個將努力工作和決心視為社會流動手段的資本主義版本中出現的顯著差異……漢斯伯裡透過貝內特·揚格探討了另外兩個可能成為抵抗和變革的場所:黑人民族主義和泛非主義”(馬修斯,2008 年第 559-562 頁)。
“雖然貝內特是一位 20 歲的醫科學生,但她行為上很青春期。她很新鮮,滿嘴說著約會和表達方式……一些奇妙的溫暖、幽默的場景涉及貝內特和她的非洲男朋友阿薩蓋”(Ambramson,1969 年第 245 頁)。這部劇“考察了農村老年黑人和城市年輕黑人之間的差異,受過教育的黑人和未受過教育的黑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它真實地描繪了黑人男性自我形象危機,社會學家告訴我們,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黑人男性在有意義的、高薪工作崗位中缺乏”。這位評論家批評該劇沒有回答它提出的經濟問題,並且該家庭拒絕林德納的計劃“似乎美化了它提出的非常嚴重的問題,變成了社會自豪感的振奮人心的戲劇”。(格林菲爾德,1982 年第 137 頁)。林德納事件得到解決,因為它與黑人特別相關,而這位評論家在上面提出的社會問題大多與所有窮人相關,這不是該劇的主題。
沃爾特·李是“一位黑人司機,他對美元哲學的唯一批評源於他討厭自己的僱主獲得更大的份額”(Kitchin,1960 年第 101 頁)。“應該賦予沃爾特·李角色尊嚴的積極品質,如他的鋼鐵意志,對他自己的高期望以及他成功決心,往往使他在與母親相比時淪為反派角色。她的形象可能更積極,但這歸因於她必須依靠沃爾特並與他鬥爭,使用她唯一可用的工具——耐心、理解、無私和愛——即使這些可能是,事實上是,她性格的真實表達……沃爾特在許多人看來似乎擁有過度的自尊,並且對他自己和他的家人要求過多,這可能更多地與觀眾的看法有關,而不是沃爾特自己的行為。如果一個人被條件化為期望很少,就像許多黑人透過種族主義所經歷的那樣,或者認為黑人應得的也只有很少,就像社會上有些人被引導去相信的那樣,那麼對這種‘條件化的少’之上的任何要求都將顯得過分。對於這樣的觀眾來說,莉娜·揚格的夢想顯得更‘正常’……因為他‘心胸高尚’,並且想‘有所作為’,沃爾特欣然接受了美國價值觀,這種價值觀認為擁有自己的企業是通往經濟成功和繁榮的主要途徑。他接受這種價值觀與莉娜對像她丈夫那樣辛苦的體力勞動的效力的信念形成對比……沃爾特成功的夢想是由一個年輕的白人男子培養的,他曾在城裡見過他並試圖效仿他……他認為自己可以像他們一樣做,並且他應該擁有他們擁有的東西……莉娜尋求的自由……是擺脫種族主義和歧視的自由……[而沃爾特尋求]一種更重要的自由,經濟自由……雖然該劇的結尾提供了沃爾特·李性格健全的決定性證據,因為他開始領會基於愛而不是權力的男子氣概的概念,並透過拒絕用金錢換取他家人的種族自豪感和尊嚴而接受了他行為的後果,但它並沒有解決這個家庭的經濟困境”(華盛頓,1988 年第 112-122 頁)。
"陽光下的葡萄乾"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20 世紀 50 年代。地點:美國芝加哥。
文字在https://archive.org/details/in.ernet.dli.2015.60953 https://pdfcoffee.com/the-odd-couple-pdf-free.html
父親去世後,楊格家的其他成員獲得了他的壽險金。母親莉娜想要買一棟房子來實現她以前與丈夫共同的夢想,但她兒子沃爾特·李寧願把它投資到一家酒館。沃爾特的妻子露絲同意她母親的意見,從而為他們的兒子提供一個更好的家。沃爾特·李的妹妹貝內特希望她母親隨心所欲地使用這筆錢。除了房子,莉娜決定用這筆錢支付貝內特的醫學院學費。露絲髮現自己懷孕了,擔心孩子會帶來的經濟壓力。當她考慮墮胎時,沃爾特·李沒有說任何話。莉娜很快就在一個完全是白人社群的街區付了新房子的首付。得知此事後,住在那個社群的白人派了一個叫林德納的人從改善協會過來,想把他們買出去。雖然沃爾特·李的一半錢被一個所謂的朋友偷走了,投資的錢也被偷走了,儘管猶豫不決,但楊格一家還是拒絕了林德納的提議。貝內特拒絕了她的追求者喬治,她認為喬治對黑人社群面臨的問題太過膚淺,反而對約瑟夫青睞有加,約瑟夫希望她獲得醫學學位並和他一起去非洲。楊格一家搬進了他們的新社群,實現了一部分夢想,儘管未來似乎很不確定。
威廉·吉布森
[edit | edit sourc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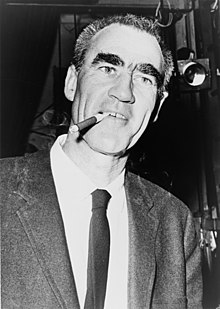
威廉·吉布森(1914-2008)在《奇蹟工作者》(1959)中深入探究了 19 世紀後期的歷史,這部作品以海倫·凱勒(1880-1936)和安妮·沙利文(1866-1936)的生活為基礎。
劉易斯 (1965) 抱怨說:“一部高效、情節緊湊、感傷、催淚的戲劇,掩蓋了人物的出現……同情,不是源於人類同情的深處,而是由戲劇性的操控所激發,就像年輕的海倫·凱勒掉下水壺,並被引導到水泵的場景一樣。發現詞語和物體之間關係的長途跋涉,變成了服從於外部的身體興奮”(第 155 頁)。有人可能會說,水泵的發現很好地說明了詞語與物體的識別,因此沒有戲劇性的操縱,而是一個對心理過程的說明性隱喻。“當海倫經歷了她頓悟的時刻,並憑藉安妮的耐心、寬容(和不寬容)、堅韌、專注,以及她蘇格拉底式的引導孩子說出已經存在於孩子內心的東西,以及之前所有的痛苦,她在水泵處作出了令人驚歎的發現,這些聯絡將成為她持續學習和交流的基礎,貫穿她的一生(現實中的海倫·凱勒繼續就讀拉德克利夫學院,1894-1904),我們作為觀眾也經歷了類似的狂喜和‘快感’。我們理解,剛剛發生的事情,這種頂點,以及這種新的開始,是安妮·沙利文幫助海倫·凱勒實現的,是深刻且不可逆轉的。有些事情永遠改變了”(Spitz,2020 年,第 114 頁)。
“吉布森創作了一個強大而吸引人的故事,以一個意志堅強的女人的性格為中心……他透過刻畫海倫的父母和年長的繼兄,給戲劇增添了一些有益的陰影……師生之間的衝突引人入勝。《奇蹟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引人入勝的戲劇”(Gassner,1960 年,第 216 頁)。這個故事“幾乎不可能更崇高,或更堅定地肯定了我們這顆迷途物種的尊嚴”(Tynan,1961 年,第 329 頁)。
“該劇集中在安妮和她學生身上。凱勒家的其他成員只是粗略地勾勒出來,除了那個無能、叛逆的同父異母兄弟詹姆斯·凱勒……他的性格和前景因海倫的悲劇所造成的家庭環境而受損;但似乎沒有人真正關心他。海倫的母親凱特,被描繪成一個慈愛但缺乏想象力的父母。當劇開始時,凱勒船長几乎放棄了對海倫做任何事情的希望,因此安妮·沙利文要面對母親的喜愛和父親的不信任,作為她幾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戰的背景……雖然該劇的主要興趣在於師生之間漫長的精神鬥爭——有時也是身體上的鬥爭——而學生不知道她是一個學生,但一個強大的輔助興趣是安妮·沙利文自身性格的展現,以及在她心中對那個最初只呈現出一個嚴峻智力挑戰的生物的愛不斷增長”(Stout,1962 年,第 125-126 頁)。
“奇蹟工作者”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890 年代。地點:美國阿拉巴馬州和馬薩諸塞州。
文字在 https://archive.org/details/the_miracle_worker_william_gibson https://pdfcoffee.com/the-miracle-worker-4-pdf-free.html
安妮·沙利文受聘於凱勒一家,幫助他們的孩子海倫,一個從出生起就聾啞的女孩。出於對她的狀況的同情,家人一直讓她隨心所欲,所以她經常表現得像個小野人。安妮用手指在她學生的手上寫下物體的名字,例如“蛋糕”和“洋娃娃”,作為獎勵,只要她模仿她自己手上的文字。當海倫拿到蛋糕時,她粗魯地塞進嘴裡。當她部分地拼寫出“洋娃娃”時,她意外地用它打了她的老師的臉,並將她鎖在房間裡。海倫的父親凱勒船長不得不使用梯子從窗戶裡救出老師。安妮接下來試圖改善海倫的餐桌禮儀,因為她習慣用手指從每個人的盤子裡拿食物。一場艱難的鬥爭隨之而來,但海倫最終用勺子從自己的盤子裡吃飯,並摺疊了餐巾。但為了達到更高的理解水平,安妮堅持要求獨自和海倫待在花園裡,遠離家人分散注意力的過度寬容的影響。海倫成功地模仿了 18 個名詞和 3 個動詞,但對她來說,這仍然是“手指遊戲”,而不理解每個事物都有一個名字的基本概念。在兩週結束時,海倫的母親無法忍受更長時間的分別。當海倫回到餐桌和家人一起吃飯時,她測試了他們的容忍度,用手指把食物塞進嘴裡,就像以前一樣,家人(除了安妮)傾向於容忍這是一種歸鄉。惱怒之下,海倫用一壺水澆了安妮。更惱怒的安妮拖著她骯髒的學生到水泵處,在那裡,後者抓住了手上的符號和手上的水之間的聯絡。她熱切地觸碰各種物體,要求安妮拼出所有東西。安妮在當天結束時,勝利地在海倫的手上拼寫出“老師”這個詞。
愛德華·奧爾比
[edit | edit source]
愛德華·奧爾比(1928-2016)在“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1962)中創造了一部強有力的家庭戲劇,這個標題指的是英國小說家弗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她遭受精神病發作,最終自殺。“這個標題是對‘誰害怕大灰狼’這首歌的雙關語,‘弗吉尼亞’這個名字暗示了一個女人對意識、解放或分離的追求。在結尾,‘瑪莎承認她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害怕拒絕現實而產生的瘋狂’”(Simard,1984 年,第 39 頁)。故事設定在新迦太基,這個名字指的是非洲城市迦太基的傳說,據說“羅馬人如此痛恨它,以至於在它被擊敗後,它的田野被……撒上鹽,這樣就不會有任何莊稼在那裡生長。這個名字讓人聯想到失敗、貧瘠和被貶低的偉大”(Shaw,2018 年,第 109 頁)。
“瑪莎已經懲罰喬治二十多年了,因為他固執地堅持自己,拒絕成為她野心的實現……瑪莎故意將自己的身份和自尊建立在她嫁的男人和為她丈夫規劃的職業上……她最關心的是與一個會讓她在其他人,尤其是她父親眼中顯得有趣和重要的丈夫的聯絡……她沒有做任何建設性的事情來幫助自己,使生活對她或喬治來說變得更美好。例如,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她曾經對家庭主婦感到自豪……在她第一次認真地進入幻想時,這位歷史副教授沒有明確的行動計劃,但他知道,一旦私人神話進入公共生活,它們就必須被摧毀”(Stenz,1978 年,第 40-50 頁)。“瑪莎將喬治在歷史系停滯不前的職位等同於失敗……她為了她丈夫的利益,將最糟糕的光芒投向雄心勃勃的妻子,將她的攻擊轉向他,將他視為一個‘失敗者’,是‘羞辱主人’遊戲的一部分,而喬治熟練地用‘獲取客人’遊戲取代了它。當瑪莎用‘強姦女主人’遊戲來反擊時,尼克從她的角度以及‘撫養孩子’的角度來看都失敗了,喬治用想象中的孩子的死亡結束了這一切。雖然批評家對職業、娛樂能力和婚姻方面的頭三個失敗感到有趣,但最後一個使他們‘在影響下不安’”(Porter,1969 年,第 228-239 頁),批評家不習慣將孩子的死亡視為即使是黑色幽默的主題。“這是一部關於一個厭惡世界的人的惡意戲劇。它以所有角色的精疲力盡和瑪莎屈服於她丈夫最殘酷的任性而告終”(Atkinson 和 Hirschfeld,1973 年,第 279 頁)。“理解孩子在戲劇中的位置的唯一途徑,是接受它是一種效果,而不是夫妻困境的原因”(Rutenberg,1969 年,第 104 頁)。從一種觀點來看,這個孩子“既不是自我欺騙的結果,也不是自我欺騙的手段,因為瑪莎和喬治完全意識到了他們的兒子是一個虛構的人物……我不能,無論奧爾比是想讓我這樣做還是不想讓我這樣做,接受人類可能會被他們知道是虛幻的幻覺所維持”(Chester,1963 年,第 299 頁)。但是,如果我們考慮遊戲方法,就可以接受它。
“在瑪莎試圖不忠之後,喬治離開家後又重新進入,手裡拿著一束金魚草,像長矛一樣扔向瑪莎和尼克:他優雅的象徵性報復的小陰莖。在這個場景中,喬治對虛構行為的執著完全顯露無疑”(Baxandall,1965 年,第 32-33 頁)。這部劇充滿了破壞性的遊戲和規則,例如“嘲弄客人”和“通姦”,只有“殺死孩子”才能改善狀況(Lewis,1965 年,第 92-94 頁)。“他們的遊戲試圖應對痛苦,要麼作為一種分散注意力的方式……要麼作為一種讓自己為戰鬥做好準備的方式……一個特別巧妙的打擊很可能會得到祝賀或相互慶祝,他們拒絕讓彼此放鬆和懈怠……虛構的兒子彌補了他們的不育,幫助他們保持團結,併為他們的生活提供了穩定的元素,但他已成為他們用來互相攻擊的武器,因此必須被犧牲”(Berkowitz,1992 年,第 149 頁)。“喬治和瑪莎透過一場儀式化的以羞辱和虐待為主、隨後是寬恕和和解的你爭我奪的遊戲來處理他們婚姻的失敗。他們生活的中心是一個虛構的兒子,他們為這個兒子編造了一系列故事,這些故事以挑釁和破壞性的方式與可能也可能沒有標記他們自身不健康和不快樂生活的事件相聯絡。觀眾所見證的“瓦爾普吉斯之夜”是由於一對年輕夫婦的拜訪而發生的;他是一位新任教員,她是牧師的女兒,她容易患歇斯底里的妊娠和酗酒,這促使她編造故事。在凌晨的幾個小時裡,瑪莎告訴這對夫婦關於他們的兒子,在這個過程中嘲弄她的丈夫,直到喬治決定採取終極行動結束他們的遊戲:在一個引人入勝且令人心碎的故事中,他在一場車禍中殺死了他們的兒子,希望在沒有幻想道具的情況下更新他和妻子之間的關係”(Schlueter,2000 年,第 310-311 頁)。“在孩子需要的關注和照顧中,父母自私而極具人性化的要求轉化為無私的奉獻……在這種轉變沒有發生的地方,性會尋求其他出口,尋找刺激,以各種變態的方式滿足對自我犧牲的正常渴望……兒子神話[在劇本中]是這種[傾向]的體現……瑪莎需要受害者,她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他們;但喬治是唯一一個每次她發怒時都會挺身而出的人。他們之間有一些秘密的默契;她用過度的要求和專橫的方式毀了他;但他並沒有被壓垮。他的力量讓她安心,即使她強迫自己反對它。喬治是她的良心和她的控告者……挫折是這部劇的戲劇衝動。邀請尼克和霍妮是一種透過一種狂歡來追求遺忘的瘋狂嘗試;言語上的衝突是溝通的挫折嘗試;這兩對夫婦的歷史是挫折之愛的故事;指責是對理解的挫折嘗試;一個沮喪的祈禱慶祝了噩夢的結束”(Paolucci,2000 年,第 47-54 頁)。最後,“修辭上的奉承和語言上的攻擊都沒有證據。這兩位語言決鬥的行家現在以簡單、直接的方式進行交流,沒有浪費任何情感。曾經因為他們詞彙的創造性,因為他們表演的表演性而被提升,賦予幻想以客觀現實的地位,喬治和瑪莎被拉到地面上,不僅僅是因為犧牲了這種激發了今晚行動的語言。遊戲現在結束了。代替了美化的俏皮話,我們聽到的是一種支離破碎的對話,一種雙重語,其語調強調了他們進入此時此刻和現實”(Roudané,2017 年,第 60-61 頁)。
“喬治失敗的地方,尼克可能會成功。他以一種瑣碎的方式固執己見,確切地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並且足夠冷酷地伸手去抓它。他的計劃清晰而可行。他比喬治更務實,不那麼理想主義,但缺乏喬治適應世界所謂的失敗的潛力……他無法分享妻子的恐懼和希望。他對她的情感需求絕對冷酷,為了得到他想要的東西而一味地順著她。 ”(Paolucci,2000 年,第 50 頁)。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人說出尼克的名字,他的妻子霍妮的名字可能只是一個例行公事般的暱稱。雖然這對老夫妻在精緻的幽默方面勝出,但他們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平行關係,因為喬治和瑪莎虛構了一個孩子,而尼克則是由於霍妮歇斯底里的懷孕而與她結婚的。作為文學愛好者,像劉易斯(1965 年)這樣的評論家往往對尼克抱有過於負面的看法,認為他是一個“沒有遠見的科學家”,“體制的一部分,新順從的人負責將世界轉變為未來機械化的非人性化”(第 91 頁),就好像他們相信喬治對尼克基因研究的評價一樣:“螞蟻將接管世界”。同樣,阿博特(1989 年)確信“尼克……這個沒有靈魂的年輕人……將透過‘耕耘相關的妻子’來升遷,作為一名生物學家,他將操縱染色體,使每個人都變得像他一樣”(阿博特,1989 年,第 175 頁)。其他人批評這對年輕夫婦過著“墮落和奉承的生活”(Krasner,2006 年,第 81-82 頁)。當尼克不再確定喬治和瑪莎是否在說真話時,喬治回答說:“你不應該知道。”“無法驗證現實不僅是奧爾比作品的核心,也是 20 世紀藝術的核心……喬治和瑪莎一次又一次地指責對方無法區分生活中的事實和幻想,其中最關鍵的是一個虛構的孩子,他一直生活在他們的婚姻中心……奧爾比是在向我們展示當現實太可怕時,我們就會退縮到幻想中嗎?還是在向我們展示當幻想和現實沒有區分時,絕望是必然的結果?……如果瑪莎憑藉她的地位成為新迦太基的女王,那麼她就是尼克的迪多,‘歷史必然性’,她的新羅馬代表著喬治所害怕的沒有靈魂的軍事化世界”(Zinman,2011 年,第 40-47 頁)。“對大學社群、對虔誠的資產階級美國教授的尖刻攻擊是一回事。教授已經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神,所以劇作家可以啄擊他。人們總是樂於聽到那些表面上明智、虔誠、富有、有才華、受過良好教育、成功或尊貴的人被揭穿”(Duprey,1967 年,第 214 頁)。
“當這些角色最野蠻時,他們就最有活力,他們對彼此的野蠻與一種情感上的依賴性相結合,無論多少失望都沒有成功地削弱這種依賴性……在掙扎之下,核心什麼都沒有,除了孤獨——因此,當他們沒有以傷害彼此的緊密接觸在一起時,他們就孤獨地在一起。在傷害的強烈擁抱之下,是他們存在的空虛——因此,當他們在一起時,他們就空虛地在一起。”(Gassner,1968 年,第 594 頁)。儘管這部劇公認力量強大,但馮·塞列斯基(1971 年)抱怨說,現代悲劇主角的野心過於狹隘。“現代悲劇嘗試中的野心和目標是什麼?在奧爾比的《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和《小艾麗斯》中,人物的戲劇性行動是為了保護自己免受空虛”(第 119 頁)。
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60 年代。地點:美國新英格蘭新迦太基。
喬治,一位大學教授,和他的妻子瑪莎(大學主席的女兒)從一個教師聚會回到他們的家中。“真是一堆垃圾!”她模仿電影場景說道。他們邀請了一對年輕夫婦尼克和霍妮。派對結束後,瑪莎嘲笑喬治的許多失敗,變得令人討厭。喬治離開,帶著一把槍回來,開槍了,但那只是一把舞臺槍,裡面彈出來一把傘。當言語虐待升級時,尼克和霍妮變得越來越不安。霍妮厭惡地跑到浴室嘔吐。男人們討論了他們的生活經歷,尼克談論了他妻子歇斯底里起源的虛假懷孕,喬治談論了一個朋友意外殺害了他的父親和母親。當女人們重新進入房間時,瑪莎提到了喬治未發表的自傳體小說,包括他剛剛講的故事。憤怒的喬治掐住了她的脖子,但隨後停了下來。他們都決定玩一個叫做“抓住客人”的遊戲。喬治講述了一個“老鼠”女人的故事,以此來羞辱尼克,而尼克正是用這個故事來講述他妻子的故事。霍妮再次感到噁心,衝了出去。瑪莎不雅地試圖在喬治面前勾引尼克,而喬治卻冷靜地一直在讀書。但當瑪莎和尼克走上樓時,喬治憤怒地扔下了書。後來,瑪莎獨自出現,朝其他人喊著要他們從藏身的地方出來。尼克加入了她,然後是喬治,手裡拿著鮮花,送給死者。瑪莎和喬治再次互相辱罵,但這次也包括尼克,他醉得無法與瑪莎發生性關係。他們玩的最後一個遊戲是“撫養孩子”,喬治和瑪莎談論了他們的兒子,瑪莎指責她的丈夫毀了他的兒子,而他則背誦了悼詞的一部分。然後,他告訴她,他收到了一份關於他們兒子死亡的電報,與他最早的故事相符。儘管瑪莎尖叫著倒在地上,但喬治向茫然無措的年輕夫婦解釋說,他們從未有過兒子。瑪莎恢復後,喬治唱道:“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瑪莎焦慮地回答說:“我怕,喬治……我怕。”
保羅·辛德爾
[edit | edit source]
1960 年代另一部值得紀念的戲劇是保羅·辛德爾(1936-2003 年)創作的《伽馬射線對月球上的金盞花的影響》(1964 年)。
“母親比阿特麗斯為了減輕將親生父親送進療養院的負罪感,照顧著患有老年痴呆的南希。南希“帶著半死不活的靈魂所發出的微笑”,以及“像滴答作響的時鐘般的晃動”,象徵著死亡,以及富裕的美國人……如何虐待年邁的父母。更令人信服的是,曾經井然有序的蔬菜店現在象徵性地反映了比阿特麗斯精神和情感生活的混亂和廢棄。秉持著“昨日種種”的座右銘,比阿特麗斯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憶中——高中科學展上,一塊顯眼的海報上寫著“本該如此”和“應該如此”。她的一生都在浪漫地夢想著和策劃著,但很少將計劃付諸實施,其中一些計劃,比如把破敗的商店改造成社群茶館,顯得有些荒誕。就像威利·洛曼一樣,比阿特麗斯傾向於將自己的失敗歸咎於外部因素,儘管她準確地評估了競爭性成功導向型社會如何試圖將每個人都強迫進入一個預定的模具,譴責缺乏包容性和降級到相同和平庸,這恰恰是美國製度的一部分……父母毀掉孩子的迴圈在比阿特麗斯與女兒們不穩定的關係中繼續上演,她們之間在同情和苦澀之間突然轉變——就像寵物兔子被輪流愛護和傷害一樣。比阿特麗斯的大女兒,精神失常的露絲,曾因接觸死亡和暴力而受到創傷,她編造故事,透過炫耀自己的性吸引力來渴望男人的關注,並且像她的母親一樣具有破壞性和報復性;當她得不到想要的東西時,她會毀掉所有人。小女兒蒂莉,以她的笨拙和不漂亮以及對現實的堅定把握,與露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並且是對一個人不需要被遺傳和環境決定的有力反駁。蒂莉在她的高中老師(不幸的是名叫古德曼先生)身上找到了一個急需的父親形象……宇宙中的一切,包括她自己,從創造的那一刻起就與其他所有事物緊密相連的觀念令她著迷;它提供了一個固定的參照點,以及一種重要的感覺”(阿德勒,1987 年,第 130-131 頁)。
這部戲劇以蒂莉從多個方面發出的希望資訊而告終,包括對科學的熱愛,這對於一般劇作家來說是一種不尋常的態度。這個學生“贏得了科學競賽,她關於該專案的敘述,以及該專案展示了外部的微妙、無形但強大的力量如何影響生物的演示,是對科學無法解釋的、受過訓練的智慧和善意在被剝奪了這些東西的環境中的年輕人身上表現出來的一個令人難忘的陳述”(菲爾諾,2007 年,第 426 頁)。“透過以蒂莉對生命的肯定作為結尾,津德爾告訴他的讀者和自己,不僅有可能生存,而且有可能克服母體有毒輻射”(福爾曼,1988 年,第 43 頁)。

時間:1960 年代。地點:美國。
在與老師通電話時,比阿特麗斯否認她想讓女兒蒂莉遠離學校,只是偶爾在家裡需要她的時候才會這樣做。比阿特麗斯抱怨在房子裡發現兔子糞便,這是蒂莉的寵物兔造成的。另一個女兒露絲告訴她母親,蒂莉因為在關於原子的學校演示中,頭髮豎起來,穿著“那件破舊的毛衣和破舊的襯裙”而被嘲笑。“瑪蒂爾達,如果你不能在去學校之前把自己打扮得體,你就永遠不會再去了,”憤怒的母親斷言。蒂莉並沒有因此氣餒,而是參加了一個科學競賽,她在橡樹嶺國家實驗室用鈷-60 放射性物質的伽馬射線將金盞花種子暴露在不同劑量的伽馬射線下。“如果你想知道半衰期是什麼,直接問我,”比阿特麗斯評論道。她緊張地諮詢學校當局,以確保植物的照射不會導致房屋居住者不育。這個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是照顧老年病人,目前是一個名叫南希的痴呆婦女。另一個難題是確保露絲的安全,她容易發生癲癇發作。雖然計劃最終開一家茶館,但比阿特麗斯經常感到絕望。“我還有什麼是留給我的?”她問露絲。有一天,因為家裡有兔子,她不安地對蒂莉說:“所以,到週末,你把那堆棉尾兔的堆肥處理掉,我們給你找個五美分和十美分商店的工作。”但露絲打斷了她的說話,宣佈蒂莉在科學競賽的五名決賽選手中被選中。比阿特麗斯對此不感興趣,她告訴校長,她不希望蒂莉參加,“因為她在家務方面沒有像她對待月球上的金盞花那樣細心”,但她最終還是同意了。在決賽當天,比阿特麗斯命令露絲和南希待在家裡。露絲憤怒地用她曾經在學校被稱為的名字叫她母親:“貝蒂,你這隻瘋子。”比阿特麗斯突然愣住了,決定自己待在家裡。女兒們不在家,她取消了與南希母親的協議,“年度職業女性”,並殺死了兔子。在她的演示中,蒂莉解釋說,金盞花的形狀不同,是因為它們暴露在不同劑量的放射性物質中而發生了突變。當露絲宣佈蒂莉獲得一等獎時,她看到了死兔子,開始抽搐。比阿特麗斯打算開一家茶館,拒絕叫醫生為女兒看病。“我們需要每一分錢來開這個地方,”她明確地說。蒂莉思考著她的專案的結論。“首先,”她想知道,“伽馬射線對月球上的金盞花的影響讓我對太陽和星星產生了好奇,因為宇宙本身一定就像一個巨大的原子世界——我想了解更多關於它……原子……原子……多麼美麗的詞語!”

馬特·克勞利(1935-2020)的《男孩們在樂隊裡》(1968)是一部布林瓦式的喜劇,它被改編成具有更深層次戲劇性的作品。
“作者用‘男孩們在樂隊裡’這個標題指的是 1940 年代音樂劇中的一個電影俗套,當時女歌手會對觀眾說:‘讓我們為樂隊裡的男孩們鼓掌’”(德雷瑟,1974 年,第 205 頁)。
《男孩們在樂隊裡》的重要性,“除了巧妙的對話和嫻熟的結構之外,還在於它大膽地處理了一個主題,這個主題在幾年前會讓觀眾感到臭名昭著——同性戀……對話中引發的一些笑聲是由於第一次遇到的意外衝擊……這部戲劇嚴肅地暗示了同性戀者幾乎總是憎恨自己。一種浮誇的傲慢,這有時是某些同性戀者的特點,是自我蔑視的面具。我相信,這在道德上是不幸的,也是不必要的,就像所有少數民族中的侵略性防禦一樣”(克魯曼,1972 年,第 19-20 頁)。
“當埃默裡,七個同性戀朋友中的一位,包括一個有吸引力的男性妓女和一個直男,聚在一起慶祝哈羅德的生日時,他探出窗外問道:‘你必須和誰上床才能在這裡喝到一杯酒?’他聲音很大,很自豪,但也符合對‘娘娘腔’同性戀男性的刻板印象。但讓當時的觀眾感到特別惱火,就像現在可能也會一樣,是派對演變成一場‘女王’之間的混戰,她們惡毒地攻擊對方,並在過程中暴露了她們對作為同性戀男性的自己毫不留情地憎恨”(塞爾,2018 年,第 81 頁)。“儘管這部戲具有開創性的地位,但《男孩們在樂隊裡》中對同性戀身份不利的刻畫——一群不快樂、自我毀滅的男性參加了一個醉酒的派對,最終以一場情感上的血腥結束——並沒有讓所有觀眾都感受到振奮人心的自由。像‘你給我找一個快樂的同性戀,我就給你找一個同性戀的屍體’這樣的臭名昭著的臺詞加劇了人們越來越懷疑這部戲劇,它並沒有賦予權力,而是暗示了同性戀身份不可能存在”(謝伊,1999 年,第 1 頁)。在斯基亞維(2001)看來,“這部戲劇需要作為現代同性戀男性戲劇的中心,也許還有其敏感性的中心進行研究”。但這位評論家指出了欣賞這部戲劇的障礙,他特別對戲劇角色的自我厭惡感到沮喪,認為他們是“一群令人作嘔的所謂朋友,容易陷入令人作嘔的自我憐憫”(第 81 頁)。同樣,多蘭(2007)抱怨這部戲劇包含“倒退的政治意義”(第 490 頁)。此外,柯蒂斯(1987)寫道,這部戲劇講述的是“一群自責、自嘲的同性戀朋友,他們在一次奇怪的生日派對上折磨著自己和彼此……即使是在最初發現它有趣和娛樂的許多人中,克勞利的戲劇性的負罪之旅最終也被譴責為對同性戀群體的另一個負面刻板印象”(第 327-328 頁),尤其是那些對歷史視而不見的希望者。在性別和性取向方面,一些評論家只在角色的正面形象突出時才會評價一部戲劇。在《男孩們在樂隊裡》的背景下,當面對周圍異性戀者的厭惡時,自我厭惡往往顯得正常。“透過分歧和自我貶低的幽默,劇中的人物互相需要。其中一個角色埃默裡,毫不掩飾地炫耀;其他人為了自我保護而發展出一種異性戀男性氣概的外表,只有在派對上,他們才能放下偽裝……這部戲劇的新古典主義結構經受住了考驗:一個連續的時間;一個地方(邁克爾的公寓……和一個行動,哈羅德的生日派對”(克拉茨納,2019 年,第 111 頁)。
《同窗會》以一種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主流舞臺上聞所未聞的方式,將“同性戀角色及其故事置於敘事中心”...《同窗會》基於舞臺上角色的多種型別,展現了對同性戀的看法。這種多元性,在種族和民族、職業、存在方式以及關係性質等方面,相當異質:有最好的朋友(邁克爾和哈羅德),前戀人(邁克爾和唐納德),前室友(邁克爾和艾倫),前偶然情人(唐納德和拉里),一個多角戀情侶(拉里和漢克),一個女性化的同性戀者(埃默裡),一個黑人同性戀者(伯納德),一個男性妓女(牛仔),一個模稜兩可的異性戀者(艾倫),當然,還有友誼圈本身 - 廣泛而多樣,但非常親密...除了性,宗教也是克勞利在其戲劇中探討的一個方面,特別是紐約的一家教堂出現在文字中。派對結束後,邁克爾通常被評論家認為去往一個與父權制、規範化和同性戀恐懼社會力量相一致的地方,這將強化他存在問題的同性戀規範特徵...然而,[邁克爾前往聖馬拉基教堂],一個和角色公寓一樣歡迎的空間。聖馬拉基羅馬天主教教堂成立於 1902 年,位於百老匯和第八大道之間的西 49 街。該教堂對其社群的服務與紐約市大多數其他天主教堂相似,直到 1920 年代中期。然後劇院區遷至其周圍,隨之而來的是演員、舞者、音樂家、工匠和遊客開始頻繁地光顧教堂。聖馬拉基的神父和領袖進行了調整,以滿足他們新教區居民的需求,包括根據劇院和夜總會的時間表進行調整,以適應觀眾。隨著 1920 年在主教堂下方建造了演員教堂,聖馬拉基成為與娛樂行業直接相關的社群的崇拜聖地”(Pereira,2021 年,第 27-45 頁)。
時間:1960 年代。地點:美國紐約。
文字在 https://kupdf.net/download/boys-in-the-band_5a6d2b20e2b6f516716cf39f_pdf
邁克爾失業,但很擅長躲避債權人。他的同性伴侶唐納德是一名維修工,並諮詢精神科醫生治療抑鬱症。這段經歷幫助他洞察了自己的心理狀況。每次他失敗,他母親都會充滿愛意地回應他,所以他將兩者聯絡在一起。“失敗是我唯一感到自在的事情,”他沮喪地總結道。在邁克爾的公寓裡,他們為哈羅德準備了一個生日派對,並邀請了兩對同性戀情侶:漢克和拉里以及埃默裡和伯納德。當幾個人盡情跳舞時,門鈴響了,漢克讓艾倫進來,艾倫是邁克爾的朋友,他一直試圖阻止邁克爾知道他的性取向。為了戲弄邁克爾,一個女性化的埃默裡極力表現出來。邁克爾知道艾倫很沮喪,於是帶著他退回到臥室,而唐納德和拉里在一次浴室相遇並睡在一起後,互相注視著對方,小聲地談論著。艾倫沒有透露他沮喪的原因,並準備離開。當埃默裡繼續模稜兩可地開玩笑時,一個惱怒的艾倫打了他嘴巴,埃默裡尖叫著,鮮血直流。嘔吐後錯過了晚餐和禮物分發,艾倫準備離開,但被邁克爾攔住了,邁克爾提議玩一個社交遊戲:“心事”,玩家必須打電話給“我們真正相信我們愛過的那個人”。漢克拒絕玩,但拉里堅持說他必須玩。伯納德緊張地給他的老情人打電話,但沒有打通。然而,他痛苦地後悔了那次未接電話,並試圖勸阻埃默裡不要這樣做。然而,埃默裡聯絡上了他的高中戀人,但沒有說出自己的名字。漢克從吉普賽舞步的拉里那裡接過電話,撥打了他們的答錄機。為了回饋,雖然人們理解他會不斷地尋找其他戀人,但拉里用公寓裡的另一部電話給漢克打電話。輪到艾倫了。邁克爾建議了一個朋友的名字,艾倫 12 年前曾與他發生過性關係,但他否認自己是同性戀,而是給他的疏遠妻子打電話。哈羅德厭倦了邁克爾,他知道他咄咄逼人的行為是源於他對身為同性戀的自厭。害怕驚恐發作,邁克爾離開去聽午夜彌撒。

20 世紀後期美國戲劇中值得注意的還有約瑟夫·A·沃克 (1935-2003) 的《尼日河》(1972)。
《尼日河》是一部“充滿活力的戲劇,對生活充滿熱情...一部樸實的戲劇,講述的是一位有教養的哲學家和一位文學家,他不得不以油漆工來維持生計。作者對家庭生活的洞察簡單、溫暖、幽默。一個愛喝酒的脾氣暴躁的祖母,她喝醉了就會唱《世紀磐石》,兒子和他的熱戀的未婚妻在半夜相遇後立即上床:所有這一切都平淡而辛辣”(Atkinson,1974 年,第 502 頁)。“約翰尼·威廉姆斯開始意識到,他已經取得了所有他可以合理地期望取得的成就。此外,他意識到自己的生命不多了。所以他犧牲自己來拯救他的兒子”(Molette,1985 年,第 460 頁)。
“我們發現約翰正在透過詩歌來反對這種對黑人男性的看法...這是一種戰場,它將允許他從自己的文化基礎上恢復尊嚴,並對他的人類產生積極的影響...瑪蒂...將自己和約翰的遺產的重擔轉向了自己;她責怪自己導致了約翰的心理閹割。約翰想上法學院,但瑪蒂讓她的親戚過分地干預了他們的關係,以至於約翰被迫放棄自己的職業目標,去做各種零工來養家餬口。她對約翰轉向酒精的內疚,加上她自己的乳房切除術,導致瑪蒂走向自我毀滅。她把自己塑造成殉道者,為約翰和母親的酗酒辯護。瑪蒂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她母親造成的,她是一個非常注重膚色的女人。瑪蒂的母親站在約翰和瑪蒂之間緊張關係的中點,因為她直接導致了約翰事業的夭折,以及瑪蒂未能找到女人的成就...瑪蒂和她母親所代表的力量威脅著將約翰拉回到黑人歷史的過去 - 陷入絕望和心理奴役。為了擺脫困境,約翰轉向透過他的兒子傑夫來實現自己的夢想...他沒有意識到傑夫拒絕他對他生活的干預...傑夫認為進入白人主導的世界不是成就,而是出賣。他寧願從黑人社群內部工作來實現社會變革。在拒絕了他父親的男子漢之路後,傑夫發現黑人社群也有自己的陷阱,那就是偽裝成革命組織的幫派”(Fontenot,1980 年,第 43-45 頁)。

時間:1970 年代。地點:美國紐約。
文字在 ?
約翰·威廉姆斯,一名油漆匠兼兼職詩人,和他的朋友達德利·斯坦頓醫生,一位執業醫師,對安妮的突然到來感到驚訝,安妮是約翰的兒子傑夫的未婚妻,傑夫是美國空軍中尉,即將跟隨他。約翰的妻子馬蒂友善地迎接了她,但她沒有迎接她酗酒的母親威爾赫米娜,威爾赫米娜認為安妮是一個厚顏無恥的女人。安妮最初來自南非,是來自加拿大魁北克的護士,在傑夫滑雪事故中摔斷腳踝後照料他。在門口,安妮與奇普斯打招呼,奇普斯是一名街頭幫派成員,想知道傑夫是否已經到達。他色迷迷地看著她,拍打她的臀部,在她打了他一巴掌後,用一把彈簧刀威脅她。幫派頭目莫帶著他的女朋友蓋爾以及另一名幫派成員艾爾走了進來。莫決心要等到傑夫到來才離開,但最終被約翰的 M1 卡賓槍說服,晚點再來。傑夫在夜裡沒有告訴任何人,就來到了安妮的房間。第二天早上,約翰和達德利偷偷地溜出去,躲避家務。馬蒂向安妮解釋說,她對約翰的失誤很縱容,因為約翰在幾年前收留了她的兩個姐妹和母親。她解釋說:“孩子,約翰一早就去刷房子,在郵局上夜班,而且還在休息日開出租車。”安妮獨自一人,艾爾和斯基特,另一名幫派成員,來詢問傑夫是否已經到達,安妮否認了。艾爾正在尋找殺害巴克利的人,巴克利是一名警察,他以性服務換取毒品,送給女學生。斯基特認為是幫派以外的人。在絕望的懇求後,斯基特鬆了一口氣,從艾爾那裡獲得了斯卡格(苯環己哌啶)。奇普斯加入了他們,急於哄騙安妮上床,直到被傑夫的突然出現嚇到。莫趕來保護奇普斯,但他未能說服傑夫加入他們的幫派。約翰和達德利喝醉了回來。約翰看到兒子很高興,但想看他穿制服的樣子。傑夫拒絕了。傑夫在關於這個話題的困擾下,終於承認自己從飛行員學校退學了。約翰失望了,獨自一人喝了六天。莫回來請傑夫幫忙:調查一個被竊聽的公共電話,該電話被他們幫派中的一名被懷疑是警察線人的成員使用。傑夫不情願地答應了。約翰回來後,才知道馬蒂得了癌症,三天後將被送往醫院。他非常沮喪,但為了馬蒂,他還是完成了關於尼日河的詩。莫和斯基特在去政府大樓安裝炸藥的路上遇到了阻礙,後者被一名警察命令停止。相反,他跑了,並受了槍傷。莫用兩根炸藥將警察擊倒後,將斯基特拖到威廉姆斯家,艾爾和奇普斯也加入了他們,但房子很快就被警察包圍了。傑夫指責艾爾就是他在公共電話上聽到的那個人,但艾爾否認了。為了誘使他承認,傑夫虛假地承認自己是巴克利的殺手。艾爾勃然大怒,掏出一把左輪手槍,而為了保護傑夫,莫、斯基特和奇普斯的團伙大聲喊著,說他們殺害了巴克利。當同樣手持槍支的約翰試圖干預時,艾爾轉過身,重傷了約翰,但在他還擊後立即死亡。為了保護兒子,約翰命令幫派成員在警察衝進屋子之前藏好槍,然後擦掉艾爾的槍,把他的指紋留在槍柄上,把罪責推到他身上。
隆恩·埃爾德三世
[edit | edit source]另一部關於黑人經歷的戲劇是隆恩·埃爾德三世 (1927-1996) 的“黑暗老人中的儀式”(1969),這部作品受到肖恩·奧凱西和讓·熱奈的啟發,是一部“對那些年老疲憊,不再夢想革命的城市黑人一代的平靜的悲劇研究”(伯科維茨,1997 年第 61 頁)。
“黑暗老人中的儀式是對受白色種族主義幽靈和生活在城市體系中的壓力的困擾的傳統黑人社會的發人深省的研究……拉塞爾·B·帕克對愛情的追求可能會讓一些讀者震驚。但它是其人物戲劇性發展的必要元素。帕克一家是真實的人,他們被他們無法解決的問題所困擾。拉塞爾·B·帕克真正的悲劇是他無法直面生活本身”(康納,1970 年第 593 頁)。這部戲劇的“主要人物是一個五十多歲的黑人,曾經是歌舞團的舞者,現在是一名沒有顧客的理髮師,而且沒有多少希望。他的妻子幾年前去世了,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先死了,因為他沒有在只有他會被提供的各種卑微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圍繞著這個中心人物,還有幾個孩子,現在已經長大成人,兩個無所事事的兒子無法像他們的父親一樣接受他們在社會中的位置,以及一個年長的女兒,這個衰敗家庭的支柱,她以作為這些在自尊心上受傷的男人的家長角色而典型。結果證明,唯一的出路通向災難……[這部戲劇] 足夠暗示性,令人難忘,在對父親的刻畫方面尤其如此”(朗,1969 年第 72 頁)。
“成功將兩兄弟分開。鮑比最近開始的偷竊生涯讓他獲得了新的獨立。西奧菲勒斯意識到自己的生意正在毀掉他的家庭,想要結束它,但為時已晚”(米勒,1971 年第 396 頁)。“鮑比在參與搶劫藍天堂幫派的嘗試中死亡,讓帕克先生和家人回到了道德世界,在那裡他們看到藍天堂的提議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而只是表面上的選擇。藍天堂只是顛倒了世界,顛覆了社會價值觀,不是為了整個黑人社群的利益,而是為了他自己的自私目的……藍天堂的人物塑造得如此鮮明,以至於他的存在主宰了整部戲劇……當戲劇結束時,仍然有一種感覺,藍天堂會回到理髮店來收錢,但會發現家人拒絕了他的生意,並摧毀了他的裝置”(豐特諾,1980 年第 47-48 頁)。
在“黑暗老人中的儀式”中,“埃爾德創造了一個代替母親的姐姐。阿黛爾工作很成功,精力充沛,卻很悲慘。她嘮叨,她威脅她的兄弟和父親。起初,她沒有意識到她所有的人性化衝動去滋養和支援都被貧民窟生活的經濟結構扭曲了。但她最終疲憊地承認,如果她不能從貧民窟拯救家裡的男人,那麼她一定不能參與他們的毀滅。如果她能做的事情很少,那麼她就必須盡力而為”(波特,1972 年第 252 頁)。
“黑暗老人中的儀式”
[edit | edit source]時間:1960 年代。地點:美國紐約哈萊姆區。
文字在 ?
在一個廢棄的理髮店裡,那裡是他們的家,由拉塞爾·帕克的女兒阿黛爾支付房租,他和他的朋友詹金斯習慣玩跳棋,前者三年來從未贏過一盤。拉塞爾的兒子西奧敦促他做點別的事情,不要玩跳棋,因為他的姐姐厭倦了為兩個兄弟和一個失業的父親支付生活費用。然而,拉塞爾想繼續玩他的遊戲,並說服詹金斯躲在床底下,因為阿黛爾來了,提醒她的父親,他應該出去找工作。西奧沒有這樣做,而是有了自己的想法:非法販賣玉米威士忌,令他父親驚訝的是,這種威士忌味道很好。由於他的父親給家人講了他過去生活的各種故事,西奧建議他的兄弟鮑比從一家商店裡偷一臺打字機作為生日禮物,這樣他就可以把這些故事寫下來,儘管他的父親不會打字。鮑比不情願地接受了。西奧接下來解釋了他與藍天堂的交往,藍天堂是一個盜竊團伙的首領,他們決心讓白人保險公司倒閉。這兩個人說服拉塞爾修好理髮店,作為威士忌銷售和賭博的幌子,最終將白人勢力趕出哈萊姆區。藍天堂在一塊板上放了一張白人的臉,讓顧客可以向它扔飛鏢。鮑比是一個能幹的小偷,他帶著打字機回來了。兩個月後,西奧抱怨說他是唯一一個工作的人。他為顧客準備威士忌,而拉塞爾和鮑比則出去享樂。拉塞爾也一直在貪汙公司的錢。阿黛爾警告西奧,與藍天堂交往很危險,因為藍天堂曾經在酒吧裡殺了一個人。經過兩天逍遙法外,拉塞爾帶著讓·熱奈的“小偷日記”回來了,這是一本商人的書。“這是我的邏輯,”他斷言,“你必須成為一個思想者,然後你才能成為一個騙子。”鮑比向他父親解釋說,藍天堂殺人是正當防衛,是為了報復一個侮辱他女友和孩子的男人,並且服了 2 年的刑期。“到處殺人,還逍遙法外!!”拉塞爾厭惡地驚呼道。“他以為他是誰,白人嗎?”西奧訓斥他的父親從他們的生意中偷走了 400 美元,並擔心他的姐姐每天晚上都和男朋友出去。他希望他的父親至少能待在店裡,這樣生意才能維持下去。詹金斯也參與了這項事業,他帶著他們的錢去尋找藍天堂,但拉塞爾說服他坐下來玩他們經常玩的跳棋遊戲,這次賭注是 20 美元,他確信詹金斯會在壓力下屈服。但詹金斯像往常一樣贏了。最後,藍天堂帶著他們的錢來了。詹金斯告訴他,他想要退出。儘管最近有兩家白人企業倒閉,但這並非由於商店的活動,而是由於鮑比參與的搶劫。拉塞爾堅持要了解更多關於這個組織的資訊。藍天堂同意了,甚至宣佈他可以被任命為主席。藍天堂質問西奧關於他的賬簿,立即發現錢被取走了。藍天堂還告訴他阿黛爾一直在和誰約會,一個叫威爾默的人,以及拉塞爾在追求一個男朋友一直在試圖破壞他生意的女孩。他承認允許鮑比和他的團伙一起搶劫。但當西奧試圖說服他的兄弟停止襲擊商店時,他拒絕了。拉塞爾邀請他的女朋友到店裡,把她拉到床邊。但她拒絕合作,帶著他的錢匆匆離開,這時西奧進來說她來了。“你也可以叫我傻瓜,”他的父親反駁道,“但我是一個燃燒的傻瓜。我要娶那個小姑娘。”西奧注意到阿黛爾走進來的步履蹣跚。她沒有喝醉,而是被威爾默毆打,因為她撒謊說她跟誰在一起。由於厭倦了這些複雜的事情,西奧想在詹金斯進來告訴鮑比在搶劫中被殺的時候退出藍天堂的生意。當這夥人猶豫著如何在把拉塞爾的 girlfriend 的公寓鎖起來之後,如何把這個訊息告訴拉塞爾時,他坐下來和詹金斯玩跳棋,並贏了。“詹金斯,你說過,我打敗你玩跳棋的那一天,”他宣佈道,“你說那將是我生命中最倒黴的一天。但經過今天發生的一切,我直挺挺的,感覺棒極了。”
萊斯利·李
[edit | edit source]另一部關於黑人社會問題的家庭劇是萊斯利·李 (1930-2014) 創作的“夏天的第一陣風”(1975 年)。
時間:1920年代-1970年代。地點:美國北卡羅來納州。
文字在 ?
因為魯克麗霞認為她父母會堅持讓她把那條珍珠項鍊還給山姆,所以山姆承認項鍊是假的,並且還進一步承認,他因為在火車站為一位黑人同事辯護而被解僱了。因為同事把他描述成一個不滿的員工,所以山姆找不到工作,不得不離開小鎮尋找新的工作,儘管他承諾會回來,尤其是在魯克麗霞懷孕的情況下。但他並沒有回來,所以魯克麗霞在羅阿諾克的一個富裕人家做女僕,但卻遭到繼子布里頓的騷擾。布里頓透過承諾和威脅,成功地讓她上了床。當布里頓發現魯克麗霞再次懷孕時,他想要離開這座房子,直到她決定替他離開,前往白巖鎮,在那裡,她帶著兩個孩子,試圖勾引哈珀,一個有機會成為格林斯伯勒教堂牧師的未成年人。哈珀對得到這份工作感到高興,在結婚前就和魯克麗霞發生了性關係,後來卻感到內疚,最終在發現魯克麗霞與山姆和布里頓未婚同居後,拒絕了這個孕婦。米爾頓和埃德娜的母親,分別是哈珀和布里頓的孩子,山姆的孩子已經去世,最終與她的兒子及其妻子哈蒂,以及他們的兒子內特和盧一起生活。為了進入醫學院,盧想要找到一份更適合自己志向的暑期工作,但他的父親禁止他這樣做,強迫他繼續做他的助手,與內特一起做泥瓦匠,內特為了這個目的放棄了自己的學業,放棄了自己成為教師的夢想。湯姆對被解僱感到不滿,朝米爾頓的住所窗戶扔了一塊石頭。米爾頓怒火中燒,準備攻擊湯姆,但格雷瑪·魯克麗霞說服他冷靜下來。她、米爾頓和哈蒂熱烈地回應了莫斯利牧師對生活的感激之情。令內特驚訝的是,盧也熱烈地回應了,儘管他的表達方式有些含糊不清。盧承認,他認為自己出了問題,尤其是當他提到一個事件時,一個女孩鼓勵他做愛時,他嘔吐了。內特對此不屑一顧,認為這只是一時的失誤,只要更多地嘗試就能克服。“只要不停地嘗試,”內特建議,“你就不會受傷。”當內特仔細查看了他父親裝修房子的費用估計時,他挑戰他的父親把收費從15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米爾頓不情願地同意了,但在面對喬·德雷克不願簽署合同時,米爾頓把金額降到了1600美元,這令內特感到厭惡。接下來,米爾頓面臨著與湯姆的妻子格洛麗亞對峙的挑戰,格洛麗亞要求他交出湯姆在最後幾周的工資。米爾頓否認欠湯姆任何拖欠的工資,並把格洛麗亞打發走了,但格雷瑪說服米爾頓給這個苦苦掙扎的家庭一點禮物。埃德娜對格雷瑪不再去看她感到沮喪,脫口而出說她是一個白人男人的孩子,這個訊息震驚了盧,他稱她為“黑鬼”,埃德娜倒在床上,病得很重。格雷瑪回應了盧持續的辱罵,鼓勵他與真正的感情聯絡,但這種努力卻導致了她的死亡,米爾頓把責任歸咎於他的兒子。當盧在門廊上哭喊時,內特把他打倒了。“我會讓你記住這個夜晚,黑鬼,”米爾頓大聲喊道。當哈蒂試圖平息盧混亂的悲傷和痛苦時,內特站起來,鬆了一口氣。“哦,天哪!”他驚呼道。“終於來了,終於來了。”隨著夏天的第一陣微風拂過他。
阿爾伯特·拉姆斯代爾·格尼 (1930 -2017) 在一部反映生活的戲劇《路邊汽車旅館》(1977) 中取得了成功。這部戲與施尼茨勒的《輪唱》(1897) 有相似之處,兩者都有十個角色,但後者是按順序排列的,而前者是同時發生的。格尼還創作了《我那個夏天干了什麼》(1983),講述了查理的故事,查理是一個青少年,他的家人,母親格雷斯,姐姐埃爾西,擔心安妮的影響,安妮被稱為“豬女人”,因為她接管了以前用作豬圈的一處房產。安妮試圖讓查理擺脫常見的庸俗的中產階級價值觀,但卻失敗了。

時間:1970年代。地點: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附近。
文字在 ?
在疲憊的駕車後,弗蘭克和傑西抵達了旅館,他比她更疲憊,因為他患有心臟病。與此同時,文斯帶著他的兒子馬克抵達,馬克是下一年秋季進入哈佛大學的候選人,父親比兒子更熱情,兒子一想到這個計劃就拉肚子。不久之後,菲爾帶著莎莉進來,他們是一對住在宿舍的年輕情侶,六個月沒有發生性關係,計劃在一個特別的地方睡在一起,他比她更熱情,她擔心菲爾在接待處給人的印象是她是個妓女。“我只是付了錢,薩爾,”菲爾反駁道。“只要你付錢,他們就不在乎。”“你告訴你的室友搬出去,好讓我搬進來嗎?”她問道。他沒有,所以她指責他“害怕個人承諾”。為了改善他兒子在哈佛大學校友比爾·鮑德溫面前的形象,他可能會幫助他的兒子進入大學,文斯給馬克買了一件襯衫。它是粉紅色的,馬克不喜歡,但被迫穿著。安迪,一位現在主要從事醫院行政管理工作的醫生,趕到並打電話給他的 estranged wife 魯思,以便解決他們離婚的物質細節。在感到被醫療職責、妻子和五個孩子困住後,他接受了匹茲堡的一份更好的工作,但魯思拒絕跟隨他。她同意過來。馬克仍然對襯衫感到惱火,想要休學一年,在一家汽車修理店工作。“我喜歡汽車,爸爸,”他說。“你會喜歡哈佛的,”文斯回答道。雷到達並打電話給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喜歡在他旅行時檢視他的情況。他接下來打電話給瑪琳,但發現他睡過的一個女人甚至不記得他,這讓他很生氣。傑西和莎莉一樣不喜歡旅館,建議她和弗蘭克再開五英里車,住在他們女兒家裡。但他太累了,所以她就獨自走了,焦急地想抱抱她女兒的嬰兒。當魯思到達時,她和安迪立刻為誰獲得傢俱和書籍而爭吵。他們離開去往房子,這樣他就可以“彌補”她在談論他的時候對他們的孩子造成的傷害。雷叫了客房服務,但當服務員莎朗穿著過時的、更新的清教徒制服,不斷批評她自己僱主提供的食物的質量時,他無法享用他的食物。他以前見過她,但記不起在哪裡。傑西走了以後,弗蘭克感到身體不適,在接待處詢問醫生,但安迪的電話響了,周圍沒有人接聽。在去見鮑德溫的路上,馬克用一件工人的藍色襯衫替換了粉紅色的襯衫,這讓文斯感到生氣。“當我介紹你的時候,我該怎麼說?我那個流氓的兒子,我那個做機械工的兒子?”他諷刺地問道,然後把襯衫撕開了。傑西無法正確地按照路標行駛,在收費公路附近被困住了,所以她被迫開車回去。當莎朗回來拿食物盤子時,雷突然想起他第一次在哪裡見過她,在一個抗議集會上,當時他正要參軍;她不記得他,但他們同意下班後見面。當弗蘭克透露他輕微的攻擊時,傑西打電話給他們的女兒,想聯絡醫生。魯思看到安迪擁有她認為屬於自己的相簿,感到憤怒。他們爭吵、為相簿爭吵,最後在撕碎的照片中緊緊地擁抱在一起。文斯對撕破的襯衫感到內疚,隨意敲了傑西的門,想找針線,偶然得到了它們。莎莉仍然沒有進入性活動的心情,走進浴缸洗澡;菲爾跟在她後面。在一位顧客舉報她對食物的負面評論後被解僱後,莎朗回到雷的房間,但他們無法決定去哪裡。安迪想和魯思待一會兒。“如果你想回家,安迪,”她警告道,“我想要的不止一個晚上。”他們一起出去。當雷承認自己有妻子時,莎朗猶豫了。“我恰好想要一段更私人的關係,”她在離開時宣佈道。在浴缸裡,莎莉咯咯地笑著,尖叫著,而文斯則得意洋洋地向馬克展示他縫好的襯衫。“你想帶它去給比爾·鮑德溫看看嗎?”馬克問道。“妙極了,老兄,”文斯回答道,然後他們一起出去。傑西告訴弗蘭克,他們的女兒和丈夫已經到達,要帶他去看醫生。菲爾和莎莉對他們在浴缸裡做到的感到高興,想要在床上做更多。傑西興高采烈地抱著一個嬰兒,而弗蘭克則因疼痛而癱瘓。
伯納德·波默蘭斯 (1940-?)憑藉其根據約瑟夫·梅里克 (1862-1890) 的生平改編的戲劇《象人》(1977) 獲得了讚譽。
這部“由21個短篇場景組成的戲劇,每個場景都包含著深刻的哲學或道德意義,揭示了社會中的異常現象,遠勝於我們中間的不正常先知。整部劇的主題是倫理,因為被排斥的主角學會了如何應對醫生清教徒世界的現實。文字簡潔,刪去了所有多餘的文字;問題被引入得恰到好處,引導我們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和自身。當病人審視夢遊的醫生時,情節發生了可預見的存在主義轉變,諷刺地將醫生自己的診斷話語反過來指向他,照亮了我們所謂的正常狀態的陰暗面,最終發現它很粗俗。也許我們才是那個馬戲團,而‘象人’依然只是一個配角,一個次要人物?而我們以為自己來劇院是為了……盯著怪人看”(布朗,1980年,第434頁)。
西蒙 (1979) 批評波默蘭斯,因為他“淡化或省略了現實生活中,即使是一些非常普通的人,對梅里克表現出的許多體面行為,他還幾乎將梅里克所有富裕的、地位顯赫的朋友和贊助人描繪成可疑的人物:要麼他們直接或間接地從象人身上獲利,要麼他們可以將自己的私人物理問題投射到他身上,並且看到他在逆境中依然樂觀,從而透過他來淨化自己……為了強調他反社會的立場,劇作家一開始就把特雷弗斯塑造得比現實生活中的特雷弗斯更加自鳴得意、更加維多利亞式的偽善,並且最後讓特雷弗斯充滿了懷疑,而現實生活中的特雷弗斯從未有過這種懷疑……隨著劇情的發展,特雷弗斯對社會成功的憎恨,以及對他自己的憎恨,變得越來越強烈,以至於在劇末,那個曾經教導梅里克我們應該遵循規則,而規則讓我們快樂的人,哀嘆道:‘我是一個非常成功且受人尊敬的英國人,生活在一個成功且受人尊敬的英國,而這個國家每天都透過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告訴我們,它想要死去。事實上,我感到絕望。’劇中發生了什麼事情才導致了這種態度的改變?幾乎沒有。在某個時刻,特雷弗斯似乎捲入了貴族約翰勳爵(顯然是虛構的人物)的陰暗的金融投機活動中,而約翰勳爵假裝對梅里克感興趣。所有這些都只是暗示,但它意味著特雷弗斯在某種程度上虐待了他的病人。此外,特雷弗斯召集的肯德爾夫人,想讓她的女性魅力彌補梅里克的不足,卻越來越喜歡那個有天賦的倒黴蛋。有一天,在她頻繁的、友好的探訪中,她對這個崇拜女性卻從未見過裸體女人的年輕人產生了強烈的感情,以至於她為梅里克解開了頭髮,脫掉了上衣。梅里克欣喜若狂,但特雷弗斯進來了,感到震驚,趕走了肯德爾夫人。我們不知道如果沒有這種干預會發生什麼;事實是,肯德爾夫人再也沒有回來,梅里克開始衰弱,最終沒有恢復……我們 simply don’t see the reasons for Treves’ moral and political change…梅里克開始用他對羅密歐與朱麗葉的評論贏得肯德爾夫人,因為他剛剛讀完這本書。如果他是羅密歐,約翰說,他不僅會對著朱麗葉的呼吸照鏡子。對此,經驗豐富的女演員肯德爾夫人,她曾經扮演過朱麗葉,回答說:“你是說朱麗葉看起來死了,他對著她的呼吸照鏡子那場戲嗎?”……莎士比亞的劇本中 nowhere does Romeo hold a mirror to Juliet’s breath, 而肯德爾夫人,她扮演過朱麗葉,顯然知道這一點”(第404-408頁)。
“特雷弗斯是善意的,但有點愚鈍。他代表了認真負責的維多利亞時代醫學文化的優點和侷限性。在幾個場景中,梅里克更坦誠和更清晰的邏輯戳穿了特雷弗斯的抑制和官方的虔誠”(凱蘭,1993年,第122頁)。
這部劇被很多人拙劣地模仿。“我們應該……打消認為病人比健康人更有趣的想法。認為變態或精神失常會自動讓一個角色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的假設,幾乎已經成為一種信仰”(加斯納,1960年,第163頁)。

時間:19世紀後期。地點:英格蘭和比利時。
文字在 ?
特雷弗斯博士,一位在倫敦一家醫院工作的外科醫生,去看了一場由“象人”約瑟夫·梅里克主演的畸形秀。他想要研究梅里克的病理,包括異常大的骨骼尺寸。演出主辦人羅斯同意將他的明星賣給他。經過檢查,梅里克回到舞臺,但被禁止在布魯塞爾演出,因為他的容貌被認為是下流的。羅斯把他送回倫敦,在那裡特雷弗斯可以進一步研究他。他正準備僱用一名護士,但當護士看到梅里克赤身裸體在浴缸裡時,便拒絕了這份工作。當霍華德主教得知梅里克的存在後,決定教他基督教。由於他在報紙上發表的信以及隨後的捐款,醫院管理人員卡爾-戈姆為梅里克獲得了終身保障。特雷弗斯以各種方式保護梅里克,包括解僱了一名窺探梅里克房間的看護人員。他僱用了肯德爾夫人,一位女演員,她比大多數人更擅長隱藏看到梅里克時產生的厭惡感,讓她陪伴梅里克聊天。肯德爾夫人很驚訝地聽到梅里克談論羅密歐與朱麗葉時充滿敏感,儘管他在愛情方面沒有任何實際經驗。在主教的影響下,梅里剋制作了一個教堂模型。但是,性問題再次出現。德里克告訴肯德爾夫人,他渴望有一個情婦。為了同情他的願望,但又不想和他睡覺,這位女演員脫掉了衣服,這樣梅里克至少可以第一次看到女人的裸體,但他們被震驚的特雷弗斯打斷了,特雷弗斯把她趕走了。羅斯想要梅里克回來,但梅里克的病情加重,無法跟隨。梅里克越是裝成正常人,他的病情就越嚴重,但他還是在臨死前完成了教堂模型。卡爾-戈姆給特雷弗斯讀了一封準備發給報紙的信,信中描述了梅里克在醫院的逗留和死亡。在問特雷弗斯是否有什麼要補充的之後,沮喪的特雷弗斯起初什麼都找不到。當他回來說他終於找到了一些東西時,信已經被寄出去了。
貝絲·亨利 (1952-?) 關於三個姐妹的戲劇《心碎俱樂部》(1979) 觸動了人們的心絃。
“《心碎俱樂部》源於深刻的南方傳統……讓人想起尤多拉·韋爾蒂和弗蘭納裡·奧康納,他們的長篇小說和短篇故事記錄了受挫生活中的怪誕……但亨利有她自己獨特的風格,將同情與黑色幽默融合在一起,三個姐妹坦然面對著內心的暴力”(古索,2006年,第48頁)。亨利“從一個儀式開始,也以一個儀式結束[這部劇];在開頭,孤獨的萊尼徒勞地試圖將一根蠟燭插進生日蛋糕;在結尾,三個姐妹一起為萊尼的出生跳舞,吃一個插滿蠟燭的大蛋糕。現在,她們不願意再傷害或評判彼此,她們相互依賴,互相支援”(阿德勒,1987年,第46頁)。
在該劇的大部分篇幅中,嚴肅和瑣碎交織在一起,就像當姐妹們輕浮的第一表兄奇克對貝布的罪行作出反應時:“太可怕了。我不知道我如何在社群中繼續昂首闊步。——你記得幫我買絲襪了嗎?”(德馬斯特,1988年,第136-139頁)。更嚴重的無情標誌著貝布提到她在開槍打死丈夫後給他倒了檸檬水這一事件,可能是因為他失血過多,看起來很渴,而且她有在餐桌上照顧他的習慣。在這兩種情況下,一個女人的願望(絲襪)或角色(在餐桌上服侍)出現在一個男人的痛苦中,就像一種針對罪犯的性別對立的黑色幽默。姐妹們對動物的命運比對男人的命運更感同身受,對貓或馬的死亡比對她們祖父的昏迷更感同身受,萊尼和貝布甚至對此一笑置之。在克雷格 (2004) 的觀點中,“到劇末,三姐妹重新團聚,成為三個更強大、更有活力的女性,她們重新建立了家庭。她們最後歡樂、金色的場景變成了一個集體的覺醒和宣洩”(第159頁)。“這部劇以一個慶祝的時刻結束,三個姐妹一起吃了一個巨大的生日蛋糕,為萊尼慶祝,幕布落下時,她們被困在一個轉瞬即逝的家庭紐帶和愛的瞬間中”(卡丘爾,1991年,第20-21頁)。在另一個觀點中,“亨利將三個姐妹留在一種模稜兩可的狀態中,拒絕恢復現狀”(古普頓,2002年,第134頁)。在其他評論家的眼中,“最後金色的場景”顯得更加瑣碎。“《心碎俱樂部》的基本玩笑是一種道德和情感上的錯位,這使得姐妹們對事件的反應總是有些偏離中心……這部劇以姐妹們笑著享受早餐時的生日蛋糕的快樂而結束,她們固有的天真保證了她們的幸福”(伯科維茨,1992年,第200頁),或者抵抗不快樂。“有瘋狂,赤裸裸的瘋狂;唯一能阻止這些角色進入精神病院(如果他們沒有被送進去的話)的因素就是他們對自己瘋狂的幽默感,這幾乎冷酷地轉化為我們把他們看作是滑稽可笑的”(考夫曼,2021年,第87-88頁)。
“萊尼認為自己正迅速步入老姑娘的行列。在她看來,她最大的缺陷是……她不能生育孩子……她的自我價值取決於她在男人眼中的價值,而這又取決於她的生育能力……美麗的梅格……一生都在努力取悅年邁的祖父……貝貝……也受到了父權社會的影響……(特別是),扎卡里……多年來在情感和身體上虐待了貝貝……最終,這部戲劇未能挑戰父權結構,甚至沒有承認父權結構一直是問題的根源……萊尼回到查理身邊,她發現查理也不想要孩子……梅格的突破是在她和多克共度一夜後,她開始再次唱歌……貝貝的狀況……得到了解決……她與她的年輕律師巴內特·勞埃德走到了一起”(波特,1999 年,第 197-198 頁)。“亨利利用家庭寫實主義,對美國家庭進行了性別化的解讀,即使女性想要扮演其他或更多的角色,而不是傳統規定的角色,美國家庭也仍然保持著其作為父權制度的身份。當然,風險在於把麥格拉思姐妹們斥為怪異和古怪,而不去提出全面解讀所要求的問題”(舒盧特,1999 年,第 15-16 頁)。
“梅格錯誤地將力量定義為能夠正面面對其他人類最血腥或最可憐的影像的能力”(奇里科,2005 年,第 6 頁)。“梅格的反應……導致了自戀型人格障礙……自戀者尋求被愛,而不是愛別人……梅格缺乏對他人同理心的第一個例子是,萊尼告訴她貝貝槍殺了扎卡里,梅格的反應是去喝蘇打水。當萊尼提到比利·博伊被閃電擊中時,梅格點了一根菸……萊尼的反應……是……抑鬱……戲劇以萊尼可悲地試圖將一根蠟燭插進她用餅乾代替蛋糕的碎裂餅乾中而開始……萊尼變得過度自我批評,並且對自己的缺點感到內疚,拒絕尋求愛情,因為她可能會被拒絕……貝貝也代表著……焦慮和痛苦……扎卡里在身體和精神上虐待了她,迫使貝貝與威利·傑伊建立了關係……因此,受虐待的女性……與……另一個被拋棄的人建立了聯絡。貝貝……是那個堅持要訂購最大的蛋糕……才能在她的生日那天治癒萊尼的孤獨的人”(普朗卡,2005 年,第 74-82 頁)。
"傷心太平洋"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59 年。地點:美國密西西比州哈茲勒赫斯特。
文字在 https://pdfcoffee.com/henley-beth-crimes-of-the-heart-pdf-free.html
貝貝在槍擊了她的丈夫,參議員扎卡里,並將他送往醫院後,正在保釋中。扎卡里現在情況危急。“別擔心,梅格,監獄對我來說是一種解脫,”她向她的姐姐保證。“我可以學會彈奏我的新薩克斯風。”貝貝還透露,她與一個 15 歲的黑人男孩威利·傑伊有染。她的丈夫在把男孩推下樓梯後,她開槍打了他,給自己做了一壺檸檬汁,還給他喝了一些,當時他正在流血。她最初想自殺,但後來想起了她的母親,她的母親在她父親離開家庭後,吊死了自己和家裡的貓。想到這些,貝貝剪下並貼上了關於她母親案件的報紙文章。當她從她的律師那裡得知,扎卡里的姐姐懷疑她,僱傭了一名私家偵探,拍下了她和威利·傑伊在她車庫裡的照片時,她非常沮喪,甚至開始用身體撞擊傢俱。然而,她的律師獲得了扎卡里婚外情的確鑿證據,並有信心達成協議,讓她可以用較輕的刑罰入獄。然而,威利·傑伊可能遭到白人種族主義者的暴力報復,所以必須離開城鎮。想到失去威利·傑伊,以及她的丈夫在當地醫院康復時,威脅要把她送進精神病院,足以讓她上吊自殺,但她用來上吊的繩子斷了。另一次自殺企圖也失敗了,因為梅格及時趕到,從開啟的燃氣烤箱裡救出了貝貝的頭部。加入這兩個姐妹的是大姐萊尼,她可能會和自己以前的情人重燃愛火。兩個姐妹給貝貝買了一個生日蛋糕,儘管晚了一天。儘管貝貝的最終命運尚不確定,但三個人還是享受著彼此的陪伴。
瑪莎·諾曼
[edit | edit source]
瑪莎·諾曼的《晚安,媽媽》(1982 年)的主題是女兒希望自殺的心理影響,以及這對自殺對女兒和母親的影響。
《晚安,媽媽》“探究了中西部和南部的哲學交叉點,儘管這些區域極點從未被如此認定,也從未在歷史或傳統中得到具體體現……就像許多中西部人物——從威廉·迪安·豪厄爾斯的作品中的那些人物到蘇珊·格拉斯佩爾和威廉·英奇,再到戴維·馬梅特以及之後的人物——傑西是一個“不太喜歡說話”的人。她緩慢而笨拙地開始說話。在試圖證明自己想要自殺的意圖時,她坦白說,“我不能說得更好”,彷彿是為了強調語言的不足,這是中西部文學和文化的一個共同特徵……相反,媽媽在明顯傳統意義上似乎是南方人。她“說話很快,喜歡說話”;“她喜歡聊天和打探訊息,這是她的家”。與傑西有時直言不諱的樸素話語不同,媽媽的話語掩蓋了現實——透過她對各種甜食的極度熱愛而變得具體。在南方講故事的偉大傳統中,她喜歡創造敘述,至少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敘述與事實有著邊際關係。根據她最詳細的故事,“阿格尼絲·弗萊徹燒燬了她住過的每一所房子。八次火災,而且她隨時可能發生新的火災”。媽媽接著說阿格尼絲住在“一座滿是鳥兒的房子裡”,而且阿格尼絲每天吃兩次秋葵“讓她瘋了””(拉達維奇,2011 年,第 116-119 頁)。
“傑西想要自殺,不是因為她的生活比西爾瑪更糟糕,而是因為她拒絕接受它……傑西說,如果她能幫助她的兒子,她不會這麼做。她感到無助於幫助她的兒子或母親,但她並非對自殺無助,因此她的自殺,因為是在她的控制之下,比她的存在更有意義。在她的一生中,她一直遭受著比失去父親、丈夫、兒子更糟糕的東西的失去,她說,“我等待的人從未出現,‘她說道,’而且永遠不會出現。我才是值得等待的人,但我沒有做到’”(比格斯比,1999 年,第 233-237 頁)。雖然傑西否認她的目的受憤怒驅使,但她多次憤怒地回應,例如當西爾瑪建議在這種緊急情況下叫她的兄弟過來時。當提到西塞爾的工藝技能時,她也感到憤怒,因為儘管他可以建房子,但他無法創造幸福。傑西目前的狀態類似於西爾瑪的朋友阿格尼絲,阿格尼絲多次燒燬了破敗的房子,以此作為對與她同住的男人的反應。傑西贊成她的縱火癖。同樣,傑西想要摧毀她的身體之屋,作為最後一種自主行為……在字面和象徵意義上摧毀房屋,女性矛盾地經歷了成長,並[成為]慶祝的原因”(佩奇,2007 年,第 395-396 頁)。
“母親從悲傷和驚慌轉變為憤怒和憐憫,最終以一種疲憊的接受而告終”(霍西,1984 年,第 38 頁)。“西爾瑪的觀點通常是逆來順受,但她認為自己的狀況是普遍的人類狀況,而不是個人狀況。‘事情發生了,’西爾瑪說。‘你盡你所能,然後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另一方面,傑西始終是個人化的。她自殺的理由是:‘我只是沒有過得很愉快,而且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它會變得比現在好’”(多蘭,1988 年,第 24 頁)。“在她離開之前,她需要消除母親任何的內疚感或責任感……傑西也希望得到——最終也得到了——她們第一次享受母女關係的夜晚,她們從未享受過”(卡楚爾,1991 年,第 29 頁)。“是傑西和西爾瑪之間的母女關係構成了《晚安,媽媽》的核心謎團。為了實現她渴望的自我實現,傑西必須擺脫她與媽媽的共生關係……在整部戲劇中,傑西一直在拒絕西爾瑪提供的垃圾食品,……尤其是牛奶”(布魯諾利,2014 年,第 233-234 頁)。“這是一部關於女性賦權的戲劇……[因為它]講述了一個單身女性的故事,她找到了勇氣,以自己的方式寫下她人生故事的最後一章”(波特,1999 年,第 205-206 頁)。傑西在度過生命中的最後一個夜晚時,採取的方法論可能顯得過於情感疏離,幾乎是夢遊般的,但她的外在控制並非掩飾,而是她內心自信的反映”(阿德勒,1987 年,第 7 頁)。
《晚安,媽媽》“是一部令人震驚的戲劇。它毫不妥協地、無情地、痛苦地戲劇化了傑西·凱茨試圖使自己的自殺合理化,以及她的母親西爾瑪試圖阻止她的自殺……她的決定反映了她需要控制她的癲癇病如此恰如其分地象徵的東西,即無法控制的生活……手持理性、嘲諷、威脅、轉移策略以及純粹的意志,西爾瑪努力控制局面和傑西……對母親的敏感、堅定、恐懼和內疚毫無準備,傑西從西爾瑪的字面和母性的控制中掙脫出來,沒有答應的告別之吻……諾曼這部偉大的戲劇證實了戲劇的宣洩力量,以及她本人作為劇作家的才華”(凱恩,1984 年,第 168 頁)。控制程度值得懷疑。“當媽媽抗議傑西不必自殺時,傑西透過說“不,我不用。這就是我喜歡它的原因。”來表達她在獲得這種自我決定的喜悅。在過去,她受制於依賴的女兒和妻子的角色,並且受到疾病的困擾,傑西現在欣喜於能夠決定自己要做什麼,控制自己的命運。如果她無法改變自己的生活,無法讓它變得更好,她可以,她斷言,“停止它。像收音機裡沒有我想聽的東西時把它關掉一樣,關掉它。它是我真正擁有並能決定它命運的唯一東西,而且我要說它會發生什麼。而且它會停止。我要停止它”。然而,傑西經歷了一種深刻的自我分離感,這在她關於自己嬰兒時期照片的演講中顯露出來。她認為自己所行使的控制是否是一種幻想?”(伯克,2002 年,第 120 頁)。
傑西的自殺建議給瑟爾瑪帶來了三個危機。首先,瑟爾瑪擔心在沒有傑西幫助的情況下,她將如何處理日常生活。傑西理解這一點,在戲劇開始前幾周,她一直在努力整理家務,以便瑟爾瑪能夠管理。其次,瑟爾瑪擔心自己的不足是傑西絕望和自殺動機的根源,尤其是她小時候處理傑西癲癇病的方式。瑟爾瑪不想揹負這種罪責。在整個劇中,傑西也努力確立自己的自主權,與瑟爾瑪保持距離,並向她保證,有時會憤怒地說,自殺“與你無關”。然而,第三個危機對瑟爾瑪來說是最毀滅性的,也是瑟爾瑪自身悲劇的根源……傑西的自殺計劃摧毀了瑟爾瑪舒適的自我意識。傑西和瑟爾瑪共同度過了一生,任時間流逝,試圖否認失望,比如瑟爾瑪與傑西父親的婚姻缺乏成就感。瑟爾瑪不想進行傑西一直在忍受的自我反省”(帕爾默,2018 年,第 182 頁)。
時間:1980 年代。地點:美國。
文字位於 https://pdfcoffee.com/x27night-mother-by-marsha-norman-pdf-free.html
傑西向她的母親瑟爾瑪宣佈,她打算自殺。知道瑟爾瑪在大多數家務事上無能為力,她寫下了關於如何管理食物配送和洗衣以及物品位置的筆記。為了勸阻她自殺,瑟爾瑪承諾改變他們關係的性質,特別是不要過分依賴她。她承認,讓傑西在她離婚後回到她家是一個錯誤。在絕望中,瑟爾瑪探究了傑西可能想自殺的可能原因,希望反駁它們,避免獨自一人。傑西討厭世界現狀,感覺自己無法勝任任何有意義的工作,對這一切都感到厭倦。瑟爾瑪探究了過去,承認她從未愛過她大部分時間沉默的丈夫,現在他去世了,儘管他似乎愛著他的女兒。當得知她的母親從未為她丈夫的失神發作或她小時候的癲癇發作尋求醫療幫助時,傑西感到震驚。為了鼓勵她過健康戶外生活,塞西爾和她開始騎馬,但她從馬上摔了下來,從此一直患有廣泛性癲癇發作,雖然得到很好的控制。瑟爾瑪責怪塞西爾離開她,傑西諷刺地回答:“媽媽,你搬家的時候不會把垃圾打包帶走吧。”瑟爾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絕望,試圖透過談論彼此認識的人和曾經喜歡的食物來分散女兒的注意力,但毫無結果。她接下來試圖以同情為動機來動搖她的決心。“傑西,沒有你我怎麼在這裡生活?”她問道,並讓她知道她作為母親的壓倒性失敗感。“傑西,發生這種事後我怎麼能面對自己?”她進一步問道。但傑西並不理會任何繼續活著的理由,或者無力地轉移話題。她安排了她的寡婦禮服清洗,那是她穿起來很漂亮的禮服。瑟爾瑪開始放棄,尤其是在聽到女兒考慮與葬禮相關的事件後。“你可能會看到很多年沒見的人,但我已經想好你應該說些什麼,這樣在你第一次見到他們時,你就可以克服緊張的部分,”傑西說,她一直都是務實的人。傑西接下來指導她如何最好地處理善後事宜。“現在,當你聽到槍聲時,我不希望你進來,”她建議。“首先,你無法獨自進門,但我不想讓你嘗試。”然後,她告訴她的母親,她會給她的弟弟留下一份禮物清單,這份清單是她為了她準備的,要跨越很多年,並向她展示了裝有她物品的盒子,這些物品將分發給她的吸毒成癮的兒子和自己。瑟爾瑪平靜地查看了這些東西,但當傑西站起來準備離開時,她驚慌失措,試圖阻止她,但沒有成功。傑西說:“晚安,母親,”鎖上了她房間的門,然後開槍自殺了。

在“朋友晚餐”(1998 年),唐納德·馬古利斯(1954 年至今)寫了一篇關於被忽視主題的文章:離婚夫婦的朋友會發生什麼?
“當一對夫婦經歷離婚時,兩對夫婦面臨著黑暗的存在主義恐懼。加布和凱倫在得知貝絲和湯姆放棄了婚姻時感到悲痛欲絕。在十多年的週末度假、撫養孩子和作為四人組一起享受美食晚餐之後,加布和凱倫在他們自己關係的邊緣搖搖欲墜。馬古利斯以時尚的方式呈現,朋友晚餐避免了家庭劇的流沙,對話尖銳、坦誠,有時令人痛苦地有趣。然而,倒敘場景減緩了戲劇的勢頭。在選擇回到過去時,馬古利斯讓戲劇在應該前進的時候閒置下來”(詹金斯,1999 年,第 82 頁)。
“在加布和凱倫的世界裡,沒有外部支撐來維持他們的婚姻。他們沒有宗教信仰,也沒有溺愛他們的父母。社會不再關心他們是否保持婚姻。這兩對夫婦所處的精神和文化真空是他們困境的關鍵。因此,當貝絲和湯姆的婚姻關係破裂時,他們十年的朋友和替身,加布和凱倫意識到自己的岌岌可危,並暫時失去了平衡”(帕奇,2002 年,第 283 頁)。“當湯姆和貝絲的婚姻破裂時,加布和凱倫也失去了平衡。他們沒有宗教定義的道德準則,也沒有溺愛他們的父母樹立榜樣並試圖提供指導……他們自己的婚姻中的干擾和不滿像細小的裂縫一樣突破了郊區中產階級和井井有條的表面,幾乎難以察覺,焦慮地被壓抑著”(施密特,2014 年,第 177-178 頁)。
“出於純粹的友誼,加布和凱倫試圖幫助貝絲和湯姆應對他們目前的困境,但他們的行為使朋友晚餐與貝爾蘭特(2011 年)的殘酷樂觀概念產生了共鳴:當你的願望實際上是你繁榮的障礙時,就會存在殘酷樂觀的關係……凱倫對貝絲作為藝術家的支援,以及她與加布希望幫助貝絲成為一個可接受的廚師的願望,是“對她繁榮的明顯“障礙”。對於貝絲——但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適用於湯姆——來說,加布和凱倫提供了本質上有害的生活模式,因為兩者都隱含地否認了其他觀點,這導致了後果。有趣的是,因為這給戲劇增添了更多深度,馬古利斯描繪了加布和凱倫作為優雅個人的正面形象。然而,儘管他們和藹可親,但他們殘酷的樂觀主義,多年來一直在持續進行,卻出乎意料地暴露出來,並導致了最終的危機”(杜博斯特,2020 年,第 277 頁)。
時間: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地點:美國新英格蘭。
文字在 ?
在晚餐招待貝絲時,加布和凱倫收到了一個令人不快的訊息,那就是她和她的丈夫湯姆打算離婚。湯姆很生氣貝絲在他不在場的情況下透露了這個訊息,從而向他們最好的朋友傳遞了一個有偏見版本的他們的困境。一個苦惱的加布試圖確定是否可以阻止離婚,但他發現湯姆很堅決。這不是瘋狂的行為。相反,湯姆說:“我已經恢復理智了。”部分原因是湯姆拒絕貝絲是為了與另一個女人發生關係,凱倫站在她一邊,認為他的行為是男人的典型表現。“男人就像多年來沒有真正和你交談過,然後有一天,當他們終於交談時,就是為了告訴你他們要離開,”她斷言。但當凱倫得知貝絲很快就找到了另一個男人,湯姆的舊律師同事時,她感到震驚,對貝絲的同情也少了很多。當凱倫進一步得知貝絲打算嫁給他時,她認為她的朋友可能會更多地考慮這件事。然而,貝絲不願進一步考慮此事,並對她的朋友說這句話感到不滿。“我終於感到完整了,終於感到我第一次走上了人生的正軌,而你卻做什麼呢?你破壞了我,”貝絲指責她。她進一步指責她的朋友不高興沒有機會始終保持優越感。“我是那個混亂的人、笨蛋、搞笑的人,”她明確地說。“你必須成為完美小姐:一切都剛剛好。”當加布發現湯姆一直對貝絲並不滿意時,他對與湯姆的友誼的看法也受到了嚴重打擊。“等等,”一個憤怒的加布打斷了湯姆。“你是在假裝嗎?你是說那幾年——所有那些年,湯姆!——我們四個人在一起,吃飯,度假,觀看無數錄影帶,你只是在做一個好人?”當加布告訴凱倫說在他們結婚後不久,貝絲就與她的“新男友”發生了婚外情時,她變得沮喪。“這說明了我們之間的友誼嗎?”她想知道。“那些年都是為了什麼?”兩人都認為他們不可能繼續與他們保持親密的朋友關係。相反,他們安心地專注於他們自己的婚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