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戲劇史:17 世紀至今/法國二戰後

讓-保羅·薩特在之前時期作品的基礎上創作了《阿爾託納的禁閉》(更準確地說應該是《阿爾託納的被禁閉者》,1959 年)。
《阿爾託納的禁閉》“探討了罪惡:確定罪惡從何開始,罪惡歸屬於何處,罪惡在何處(以及是否)終結...這部戲劇試圖將良知的生活,道德熱情的生命,與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調和起來,即如果任何罪行都被追溯到其邏輯根源,罪犯並不孤單。在每一次不道德的行為背後,總有社會、心理或歷史上的原因,它又通向另一個原因,然後又通向其他原因,遠離罪犯本身。但是,薩特問道,如果真是這樣,我們該如何像必須那樣去評判呢?我們如何才能知道什麼是善?我們如何才能使生活變得更美好,更易於忍受?薩特為他的主題選擇的戲劇意象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考夫曼,2021,第 23 頁)。“薩特在《阿爾託納的禁閉者》中出現的另一個關注點是,勝利者是失敗者,而失敗者則是勝利者。父親成功地見到了弗朗茨,卻發現他們之間無法交流。勒妮毀掉了約翰娜和弗朗茨之間的關係,卻完全失去了他”(奧康納,1975 年,第 31 頁)。
“在馮·格拉赫家中...時間停止了,因為弗朗茨...他從未對決定性行為負起責任,直到有一天在斯摩稜斯克,他折磨了一名游擊隊員。據稱他這樣做是為了他的國家,但實際上是為了克服一種無能為力的感覺,斷言他對父親的獨立性,並透過一項重大行為來表現自己的個人力量”(傑克遜,1965 年,第 64 頁)。“這些人物都完全意識到他們處於虛偽狀態,並有意識地選擇繼續這樣...虛偽在於用一個角色取代個性...正如勒妮所說,'你知道,我們玩的是輸家通吃的遊戲'...她試圖讓弗朗茨直面他的過去...她失敗了...[並且] 只是想演好她選擇的角色,她對改變現狀沒有任何興趣...她的態度概括在她亂倫的關係中...勒妮選擇成為...一個失敗的叛逆者...[因為] 失敗只需要被渴望就會被轉化為成功...只有當[弗朗茨] 保持自我禁閉時,她才能利用他作為武器來對付她的父親,並在她對家庭所代表的一切的象徵性叛逆中。對於維爾納來說,約翰娜與弗朗茨的關係的意義在於,它是最後的侮辱,[它] 不那麼依賴維爾納與妻子的關係,而是更多地依賴兩個兄弟之間以及他們與父親之間的關係...他什麼都不想比取悅他父親更好...但他總是受到阻撓...正如勒妮和維爾納選擇成為失敗者一樣,約翰娜也是如此...約翰娜的婚禮是她本質上的美麗葬禮...然而,她需要一個觀眾來見證她的殉道:維爾納...格拉赫生活中驅動力一直是對資本主義力量的正直的信念...[他] 漠視了對納粹權力性質的所有正常反對...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在於沒有可見的替代方案...[在自殺中] 是選擇自己失敗方式的可能性...為什麼弗朗茨對謀殺和酷刑感到內疚?...[他] 感到厭惡,因為他無力做任何其他事情...他是有良知的...但主要的慾望是權力...他的懇求是,歷史程序的本質是,邪惡是人類活動的唯一可能結果...他暗示了自己的罪惡,而罪惡假設了自由”(帕爾默,1988 年,第 308-317 頁)。“弗朗茨不僅發現了自己的不真實和無能,而且以一種尖銳的形式體驗到了被錘入地面的主觀狀態。只有一件事,他不是他父親的映象,那就是當他使用酷刑時,所以死亡是他擺脫這種難以忍受的處境的唯一方法——意識到他白白地酷刑——並斷言他自身現實中所剩無幾的東西”(沃德曼,1992 年,第 263 頁)。
“弗朗茨把自己禁閉起來,是因為他過去參與了戰爭罪行,目前也參與了亂倫...勒妮對哥哥的愛...在她哥哥更直接的禁閉的封閉氛圍中蓬勃發展。為了保護這種親密關係,她多年來一直拒絕做她父親的使者。此外,勒妮意識到,她對哥哥的愛是她狂熱地擁護某種部落家庭生活準則的一部分。'亂倫是我讓家庭關係更加緊密的方式,'她說...維爾納天生就嫉妒。被弗朗茨取代,維爾納無法投入任何關係,除非是對他父親一直以來的永久追求的態度...問題是:為什麼他不肯離開?他...根植於自己對自卑的信念...乍一看,約翰娜似乎是一個精力充沛、平衡的女人,準備為她的丈夫而戰...她與其說是同謀,不如說是受害者...她已經朝著自己的個體解放前進...這就是維爾納不理解她的地方,而透過他的不理解,他把她判處了她已經放棄的虛構世界...老格拉赫禁閉了所有人...如果他這樣做,那是因為他自己是最大的'禁閉者'...他的唯一道德準則是目的 оправдывает средства...他說納粹:'我為他們服務,因為他們為我服務...但他們正在打仗,為了給我們尋找市場,我將在一塊土地上與他們發生衝突'...弗朗茨禁閉綜合症的根源”(普奇亞尼,1961 年,第 23-30 頁)。“恐懼是專橫的家父與子女之間唯一的感情紐帶,約翰娜發現他無法愛導致了他的妻子死亡。在情感上和身體上拒絕了他的小兒子,馮·格拉赫長子讓維爾納成為了他虐待的主要目標。同樣的缺乏感情讓他與女兒的感情隔絕”(加勒,1971 年,第 179 頁)。
“五個角色的存在主要為了弗朗茨,他的禁閉也禁閉了他們...格拉赫與納粹的勾結是基於納粹權力的現實;保持老闆的身份是首要的,在戰爭期間保持老闆身份意味著與希特勒合作...當劇目開始時...格拉赫仍然擁有形式,但不再指揮它...弗朗茨的出生和成長是為了像他父親一樣,成為一個老闆,擁有他父親的驕傲和他的父親的激情...三年來,他的父親一直知道他是'斯摩稜斯克的屠夫'。然而,馮·格拉赫既不能也不願評判他的兒子。與弗朗茨無論他是什麼樣的都繫結在一起,馮·格拉赫拒絕了弗朗茨的行為,但他仍然完全愛著他。他的父愛,源於身份,使判斷成為不可能。當馮·格拉赫承擔了弗朗茨作為斯摩稜斯克屠夫的罪行的責任時,父子之間的身份得到了解決。弗朗茨一無所有,他允許他的父親神聖化那種虛無”(麥考爾,1969 年,第 128-139 頁)。“可以推測,在弗朗茨的半清醒意識中,[天花板上看到的] 非人性的甲殼類動物代表著地球未來的居民,是即將搞砸他們最後一次機會的人類的繼承者”(帕塞爾,1986d 年,第 1651 頁)。
“弗朗茨的一生都被他父親的決定所扭曲,他父親決定傾盡一切,包括自己的孩子,去打造一個龐大的資本主義帝國”(布拉德比,1991 年,第 44 頁)。“劇本的結尾,父子倆駕著保時捷從魔鬼橋上跳下自殺,象徵著父親共謀行為的破產,以及兒子最終的道德無力。然而,觀眾也被捲入其中,因為他們被迫在死後聆聽弗朗茨的預錄講話——一種由已故主角創作的倒敘,但卻是針對觀眾的;這也是從過去回溯到現在和未來以澄清事態的另一個例子。在講話中,弗朗茨宣稱‘如果人類沒有被其殘酷、古老的敵人追趕,這個世紀本來會很好,那個發誓要毀滅人類的食肉物種,那個兇殘的無毛野獸——人’。該劇的最後時刻也包含了《蒼蠅》(1943 年)和《無出口》(1944 年)的一些元素。弗朗茨用類似俄瑞斯忒斯的姿態,承擔起這個世界的責任,‘將這個世紀扛在他的肩上’,而與《無出口》一樣,該劇沒有戛然而止。故事並沒有結束……‘萊妮走進他的房間’”,於是成為馮·格拉赫企業下一個囚徒,而這個企業將由維爾納在妻子約翰娜的幫助下繼續經營(範登·霍芬,2012 年,第 69-70 頁)。
約翰娜“是最不隱蔽的人,最害怕成為囚徒;她是唯一一個看穿虛假的人,包括她自己以前作為電影明星的虛假身份。維爾納,一個健壯的體格卻性格軟弱的人,似乎主要感興趣的是想從他父親那裡,遲來的,得到他從未得到過的認可,作為一個小兒子”(布羅斯曼,1983 年,第 95 頁)。
"隔離在阿爾託納"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40 年代至 1950 年代。地點:德國漢堡的阿爾託納區。
文字在?
得知自己只剩幾個月可活後,一位實業家馮·格拉赫希望他的小兒子維爾納接管他的造船生意。他還要求維爾納、他的妻子約翰娜和他的妹妹萊妮留在他們 32 間房的家族豪宅裡,照看他的大兒子弗朗茨,弗朗茨已經被隔離在這個房子裡 13 年了。維爾納和萊妮同意這樣做,但約翰娜想獨自搬到其他地方,這樣父親就必須解釋為什麼這三個人在他死後還要待在一起。1941 年,他收到納粹部長戈培爾的提議,讓他出售自己的田地,併為猶太人建立一個集中營,他接受了。在對猶太人的迫害中,弗朗茨被發現私藏了一名拉比在父親的豪宅裡。這名拉比被黨衛軍官兵當著弗朗茨的面殺害,格拉赫被迫把兒子送到俄國戰線。約翰娜懷疑是她丈夫向黨衛軍通風報信。1946 年,美國軍官被邀請到豪宅,在那裡,萊妮習慣於激起他們的慾望,然後用侮辱的話語打消他們的念頭。有一天,一名軍官試圖強姦她。她用瓶子擊打軍官的頭部,成功地自衛了。為了保護她免受因這件事被追究責任,弗朗茨承擔了罪責,並透過與一名美軍將軍的交易,被允許出國,但最終還是選擇留在家裡躲藏起來。約翰娜討厭這個故事。她沒有改變主意,向丈夫發出最後通牒:要麼留下來,要麼跟著她去其他地方。多年來,弗朗茨拒絕見父親,只允許萊妮進入他的房間。格拉赫試圖說服約翰娜與弗朗茨談談,至少讓他知道自己快死了。弗朗茨並不是他父親故事中描述的那樣的人道主義者。他穿著破損的軍官制服,在房間裡放著希特勒的畫像,並在上面撒滿了牡蠣殼。自戰爭結束後,他認為整個國家都被雜草淹沒,要麼醉酒消遣,要麼與姐姐發生亂倫關係。約翰娜從丈夫那裡得到了萊妮的秘密密碼,去看弗朗茨。她告訴弗朗茨,他父親快死了,她寧願看到他自由或死亡,也不願看到他這樣生活。在得知約翰娜成功地見到了弗朗茨之後,格拉赫也要求見他,但約翰娜拒絕幫忙,她認為這可能會導致他死亡。維爾納認為父親的目的是讓弗朗茨接管他的生意。最終,約翰娜改變了主意,告訴弗朗茨他父親想見他,但無法誘使他回到正常的生活。“我將立刻放棄我的虛幻生活……當我比我的謊言更愛你,當你儘管知道我的真相卻仍然愛我時”,弗朗茨宣稱。他明確表示,他被隔離並非因為他做了什麼,而是因為他沒有做什麼,他被動地允許他手下的一名狂熱士兵折磨了一些平民。他的坦白,在萊妮嫉妒競爭對手的刺激下,讓約翰娜感到厭惡。約翰娜和萊妮都無法說服弗朗茨離開房間。然而,就在約翰娜從他們之間開始萌發的愛情中退卻的那一刻,他終於同意見他的父親。弗朗茨在報紙上讀到他父親的財務成功,他一直都在玩“輸者贏”的遊戲。格拉赫驚訝地發現弗朗茨同意接管生意。在回憶過去的時候,弗朗茨提醒他,他們曾經一起高速駕駛汽車,兩人都希望重溫那段經歷。當他們一起出去的時候,萊妮確信他們會一起死去。
亨利·德·蒙泰朗
[edit | edit source]
亨利·德·蒙泰朗(1895-1972 年)在之前時期之後,又創作了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延續了現實主義呈現歷史的傳統,即“聖地亞哥之主”(The master of Santiago,1948 年)。
在“聖地亞哥之主”中,“一位父親拒絕採取任何措施來確保女兒與她心愛的人的完美婚姻,因為他拒絕與西班牙在摩爾人戰敗後舒適繁榮和權勢燻心的生活中妥協。他的女兒,受到父親極度高尚的品格的激勵,結束了這場本可以為他帶來財富,並讓她得以結婚的騙局。這位父親是一位非凡而逼真的唐吉訶德(儘管沒有荒誕的屬性),他對陰謀詭計的世界以及西班牙對美洲印第安人的奴役的厭惡,達到了真正英雄的程度。這部戲劇中理想主義的火焰無處不在。人們只能希望它也有更多的人性溫暖。這位騎士幾乎超人的純粹動機,無疑是要給普通人——蒙泰朗也許過於輕蔑他們而無法成為真正偉大的劇作家——一記耳光”(加斯納,1954a 年,第 724 頁)。這出戲的宏偉規模“採取了抵抗的形式,用優美的語言表達了對任何庸俗、平庸、平常事物的不滿”(克魯克香克,1964 年,第 110 頁)。
“唐·阿爾瓦羅,他的使命是將新世界的印第安人改宗,蔑視著他所引導的努力……最後,[瑪麗亞娜]相信婚姻制度是偉大與救贖的障礙:難道這不是天主教神父不允許結婚,以及沉思修道院成員最接近上帝的原因嗎?”(西斯馬魯,1986 年,第 1353-1354 頁)。“對他來說,新世界沒有財富,對她來說,沒有婚姻和幸福!這是一種徹底的拒絕,受一種對純潔的虐戀式浪漫主義的驅使……這位主人……不是基督教模範的榜樣,因為他的自私、殘忍以及他所有的行為都帶有可怕的不人道性……阿爾瓦羅的愛是一種消滅的愛;他有一種冷酷,只有他的驕傲才能解釋……”(勒姆利,1967 年,第 345-346 頁)。
“即使在他最好的時候,[阿爾瓦羅]也只是一個半基督徒……因為他所必須應用的基督教是不完整的……他強烈地感受到基督教的第一個組成部分,即它超凡脫俗,它蔑視塵世的舒適和財富,它放棄了世俗的東西,但他對它所賦予的與上帝合一的意識卻一無所知……現在,阿爾瓦羅的宗教幾乎完全……在於對上帝的無限偉大與距離的意識……但化身呢?與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溫柔結合呢?……這些事情仍然超出了阿爾瓦羅的體驗……真正基督教的性格……是……瑪麗亞娜,她最終犧牲了自己,以便與他一起放棄世俗”(霍布森,1953 年,第 179-181 頁)。
“對許多人來說,蒙泰朗的‘基督教’戲劇似乎是對狂熱的探索,缺乏聖潔的品質,這種狂熱遠遠沒有達到神聖的程度,充其量只是對自我的狹隘超越……唐·阿爾瓦羅表達了一種願望,即把自己從所有世俗的商業和關注中隔離出來,進入一個精心策劃的孤立狀態,以進行沉思,並獲得救贖……世界對他來說太過分了,他不理解它,而且他不再想要理解它……瑪麗亞娜被描繪成一個永遠站在她父親和上帝之間的障礙。她的父親對透過允許她結婚來保證瑪麗亞娜的幸福沒有興趣……家庭制度被譴責……騎士團是擁有共同信仰和高貴理念的選民精神的真正家庭。它不會強加附件……瑪麗亞娜嚴肅地宣告她不希望幸福,這為她最終與父親的理解做好了準備……父親用斗篷蓋住自己的雙肩和女兒的雙肩,這是一個象徵他們狂喜和遺忘——或者他們的瘋狂和他們對生命的放棄——的姿態”(約翰遜,1968 年,第 110-113 頁)。
"聖地亞哥之主"
[edit | edit sourc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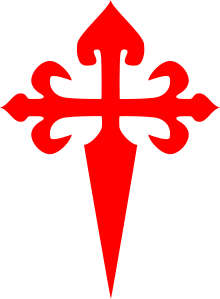
時間:1519 年。地點:西班牙阿維拉。
文字在?
聖地亞哥騎士團的成員在他們的團長唐·阿爾維羅的家中集會。其中三位成員決定在新世界碰碰運氣。對於阿爾維羅來說,現在這個時代已經腐敗不堪,無法與西班牙人在格拉納達戰役中趕走摩爾人時那個輝煌的時代相比,那時他“在戰爭的披風中凝視著上帝”。將印第安人改宗的表面目的不過是“不潔和排洩物”,因為對金錢的渴望,沒有將印第安人送往天堂,卻將西班牙人送往地獄。當他的朋友們離開後,阿爾維羅獨自一人感到欣慰。“哦,我的靈魂,你還在嗎?”他自言自語道,“哦,我的靈魂,終於只有你和我了!”一位朋友,唐·貝爾納爾,聽說他的兒子雅辛託和阿爾維羅的女兒瑪麗安娜之間有婚約。由於雅辛託的揮霍無度,貝爾納爾建議他和其他人在新世界發財,這個計劃立即遭到團長的堅決拒絕。阿爾維羅對金錢毫無興趣,即使是為了他世界上最愛的女兒。 “你不會偷走我的貧窮,”他警告他的朋友。他嚴厲地指責女兒在這件事上的不誠實,稱愛情是“猴子戲”。“女兒的父親還是父親嗎?”他反問自己。為了幫助這對年輕戀人,貝爾納爾請求索里亞伯爵誤導阿爾維羅,讓他以為國王命令阿爾維羅以管理者的身份前往新世界,但瑪麗安娜無法欺騙父親,她向父親坦白了真相,破壞了計劃。厭倦了世俗事務,阿爾維羅前往聖巴拿巴修道院,那裡也是瑪麗安娜可以居住的地方。她接受了提議。他用聖地亞哥騎士團的白袍覆蓋著她,外面的雪正在下,父女倆似乎準備被埋葬在神秘的雪中。
安德烈·紀德
[edit | edit source]
另一部以宗教為主題,但更具批判性的戲劇是安德烈·紀德(1869-1951)創作的《梵蒂岡地窖》(The Vatican cellars,1950),該劇改編自他 1914 年的同名小說。該故事源於 1893 年的一個歷史事件(愛爾蘭,1970 年 p 252),“一位狡猾的律師、一位被逐出教門的修女和一位有爭議的牧師在里昂合謀散佈謠言,說利奧十三世被共濟會樞機主教囚禁,並被一個假教皇取代,他們從信徒那裡收取贖金以釋放教皇”(畫家,1968 年 p 67)。以下評論針對的是小說,但也同樣適用於戲劇。
“有兩個主要情節……拉夫卡迪奧的故事和陰謀的故事……由家庭關係聯絡在一起……[梵蒂岡騙子的目標]……是要愚弄社會”(畫家,1968 年 pp 66-67)。“地球上的教皇,根據定義,應該是無誤真理的寶庫,由神明保證。但當然,教皇的真實性也需要得到保證:只有在你能毫無疑問地確定你面對的是唯一的無誤教皇時,你才能相信教皇言論的無誤性”(愛爾蘭,1970 年 p 270)。
“普羅託斯將人類分為兩種型別:‘微妙的’,普羅託斯當然屬於這一類,他們是那些受變形能力的影響而對任何特定情況做出靈活多變的反應的人,這些人無論出於何種原因,都不會在所有人和所有場合都展現出相同的姿態;他們是‘甲殼動物’的敵人,他們是僵硬的、孤立的、原則性強的人……普羅託斯……接受所有貴族和資產階級甲殼動物……是逃避的化身——逃避社會……自我……過去,以最野性的紀德式意義上的逃避,以及創造性精神的持久流動不安的意義……朱利葉斯……是一位小說家,他的失敗源於他性格的過度邏輯性……拉夫卡迪奧[是] 躁動不安的、放蕩不羈的[但]他給自己強加了嚴格的自我控制紀律……甚至為了最輕微的自我剋制失誤而用刀筆自虐”(托馬斯,1959 年 pp 157-161)。“拉夫卡迪奧,一個年輕的流浪漢……既美麗又無道德”(波拉德,1991 年 p 365)。拉夫卡迪奧的“天生的優雅和優越成就使他在社會下層階層格格不入,而他的出身和身份的謙卑又排除了他進入上層社會”(愛爾蘭,1970 年 p 262)。每個甲殼動物,朱利葉斯、安提梅和阿瑪迪烏斯,“都改變了自己的思想和習慣,從自己所有的過去中根除自己”,但由於他們是甲殼動物,他們又回到了原來的樣子(奧布萊恩,1953 年 p 180)。
人們對拉夫卡迪奧謀殺的動機提出了不同的,但部分重疊的觀點,這似乎是一個毫無必要的行為。作為一個私生子,拉夫卡迪奧“無意識地渴望被認可和得到父愛——他是否擁有它們已經無關緊要了,因為他已經無法知道如何利用它們——已經變成了同樣無意識的復仇需求。在弗勒裡索瓦爾平庸的資產階級形象中,他推翻了拒絕他的社會”(畫家,1968 年 p 72)。“在趕走阿瑪迪烏斯時,拉夫卡迪奧不僅在反抗根深蒂固、錯綜複雜的家庭和所有堅硬甲殼動物的統治制度,而且也在反抗瓦格納和帕西法爾,以及所有崇拜他們的人……拉夫卡迪奧是一個愛玩感覺和情緒的暴躁賭徒”(奧布萊恩,1953 年 pp 185-186)。他是一個自戀狂,“渴望自我認知……源於一種瘋狂的急切麻木,一種對最強烈的感覺的貪婪慾望”(托馬斯,1959 年 p 162)。“對他的同伴感到厭倦和好奇,拉夫卡迪奧讓自己的想象力漫遊……正是[這種]明顯的缺乏動機才構成了命題的興趣所在……他好奇的是他自己”(愛爾蘭,1970 年 p 263)。
"梵蒂岡地窖"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 世紀 90 年代。地點:義大利。
文字在?
安提莫斯是一位無神論者,也是一位殘疾人,他對他妻子維羅妮卡感到憤怒,因為維羅妮卡向聖母瑪利亞獻上了祈求他恢復健康的蠟燭。令他驚訝的是,在黑暗中獨自一人,他聽到了聖母的聲音,並奇蹟般地恢復了健康,高興地扔掉了柺杖,並皈依了天主教信仰。安提莫斯的富有的姐夫朱利葉斯是一位作家,他的垂死的父親,一位伯爵,要求他去看望父親的私生子,一個名叫拉夫卡迪奧的年輕人,他從未見過。為了獲得拉夫卡迪奧的資訊,朱利葉斯給他提供了一些秘書的工作。在他父親的遺囑中,他將一大筆錢留給了拉夫卡迪奧,前提是拉夫卡迪奧承諾不再用自己的身份打擾家族的其他成員,因此他不需要接受朱利葉斯提供的工作。在去朱利葉斯家的路上,拉夫卡迪奧從一棟著火的房子裡救了兩個孩子,贏得了朱利葉斯女兒詹妮弗的讚賞。拉夫卡迪奧向朱利葉斯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時,被伯爵去世的訊息打斷了。與此同時,朱利葉斯的另一個姐夫阿瑪迪烏斯聽到一個謠言,說教皇利奧十三世被綁架,並被關押在聖安吉洛堡壘的地下室裡,該堡壘與梵蒂岡相連,而一個冒牌貨取代了他的位置。這個謠言是假的,是由拉夫卡迪奧的校友普羅託斯散佈的,目的是為了從愚蠢的天主教徒那裡騙取大量的錢,以釋放教皇。當阿瑪迪烏斯到達羅馬時,普羅託斯偽裝成牧師,與他交朋友,並帶他去那不勒斯,去看望他的同夥巴多萊蒂,後者假裝成樞機主教,要求他將 6000 法郎的債券兌換成現金。與此同時,朱利葉斯也來到羅馬,向教皇請求賠償安提莫斯損失的收入,因為安提莫斯不再受到他曾經在職業生涯中依靠的共濟會的保護。然而,他的任務沒有成功。阿瑪迪烏斯向他透露了他知道的關於失蹤教皇的事情,但朱利葉斯很難相信這樣的故事。儘管如此,他還是幫助阿瑪迪烏斯從銀行取回了錢,並給了他一張以他名義的車票。巧合的是,當阿瑪迪烏斯從羅馬乘坐火車前往那不勒斯時,他遇到了拉夫卡迪奧,兩人互不相識。拉夫卡迪奧對自己的生活感到厭倦,但他願意將命運推向極點,於是將他從車門扔了出去,導致他喪生。他帶走了阿瑪迪烏斯的車票,但沒有帶走 6000 法郎。在羅馬與朱利葉斯見面時,拉夫卡迪奧驚訝地發現,被殺的人是朱利葉斯的姐夫。為了嘲弄他的同父異母兄弟,他在桌子上留下了阿瑪迪烏斯的車票。朱利葉斯發現後,非常擔心自己會成為這個未知兇手的下一個受害者。拉夫卡迪奧不知道的是,他的謀殺被普羅託斯看到了,普羅託斯建議他的老朋友,他們可以以此來勒索朱利葉斯。拉夫卡迪奧拒絕了,並將自己的罪行告訴了朱利葉斯,詹妮弗聽到了他們的談話。這場謀殺讓詹妮弗更加愛上了這個男人。拉夫卡迪奧帶著她逃跑了,最後說:“我們會一起找到自救的辦法。”
雅克·奧迪貝爾蒂
[edit | edit source]
一座橋樑連線了雅裡的《尤利西斯王》(1888)與 20 世紀 20 年代的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運動以及 50 年代的荒誕劇。達達主義戲劇的一個例子是特里斯坦·查拉的《煤氣心臟》(The gas heart,1921),該劇以荒誕無稽為主。超現實主義戲劇的例子包括羅傑·維特拉克的《維克多,或孩子們掌權》(Victor, or the children come to power,1928)和《愛的奧秘》(The mysteries of love,1927)。這兩個運動的劇作家都試圖用夢境般的意象推翻中產階級的習俗。超現實主義者表現出對用新社會取代主流習俗的興趣,包括共產主義社會,而達達主義者則很少願意用任何東西來取代它們。一座橋樑還連線了存在主義戲劇和雅克·奧迪貝爾蒂(1899-1965)的《惡貫滿盈》(Le mal court,1947),該劇也表現出與過去的親緣關係,包括格奧爾格·畢希納的《萊昂斯與萊娜》(Leonce and Lena,1836)和阿爾弗雷德·德·繆塞的《幻想曲》(Fantasio,1834)。
在《邪惡蔓延》中,“情節和主題故意採用傳統手法,籠罩著童話般的神奇光芒。角色大多擁有功能性名字……並且缺乏心理上的實質。他們傾向於用抽象的術語交談……但他們的虛構世界從未受到來自外部的懷疑或問題的困擾”(Bradby,1991年,第188頁)。“情節本身並不重要,只是為了說明主題,即邪惡的無所不在和不可阻擋的力量。奧迪貝爾蒂使用了一個傳統的童話情節:美麗的年輕公主,一位貧困國王的女兒,要去嫁給一位富有的年輕國王;邪惡的紅衣主教出於政治原因干預並阻止了婚姻;美麗的年輕公主心碎,等等……奧迪貝爾蒂只將他的經典童話公式推進到一定程度:富有的年輕國王並沒有將邪惡的紅衣主教扔進地牢,以便他最終能娶到美麗的年輕公主。相反,公主,阿拉麗卡,隨著劇情的推進,發現自己一直被邪惡和欺騙所包圍。她對美好生活以及人們的善良和可信的幻想,在痛苦的震動中,一個個地從她身上脫落。她發現,她計劃中的婚姻很久以前就被秘密放棄了,她被當作誘餌,以便年輕國王可以與政治上更有利的人結婚。甚至她年邁忠誠的保姆也參與了陰謀。她絕對沒有人可以信任。每個人都自私、腐敗、不誠實,因為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虛假和腐敗的社會中,並按照這個社會的規則生活。隨著她不得不經歷的一系列衝擊把她打入對世界真實本質的認識,阿拉麗卡意識到,如果她想作為棋子以外的人生存下去,她就必須與之妥協。她決心用邪惡對抗邪惡——讓“邪惡蔓延”。她廢除了她友善、笨拙的年邁父親,無視他對她孝敬的懇求,並決心以徹底的冷酷統治。如果一切都邪惡,那麼最邪惡的人就會獲勝”(Wellwarth,1962年,第336頁)。
《邪惡蔓延》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40年代。地點:虛構國家肖特蘭。
文字在?
阿拉麗卡,肖特蘭的公主,必須出於政治原因嫁給奧西丹特的國王帕菲特。她聽到有人敲門,一個聲音說國王已經到了。在公主和所謂的國王交談時,她的副官發現這個人是冒牌貨。當入侵者費迪南德試圖離開時,副官向他開槍,但讓他活了下來。當阿拉麗卡和她的女管家討論此事時,又聽到有人敲門,再次說國王已經到了。這次是真正的國王,他發現公主很吸引人,但與他同行的紅衣主教透露,他們的婚姻前景已被取消,因為國王娶西班牙國王的女兒更有利於他們的國家利益。“我們將與西班牙結婚,讓她懷孕,”紅衣主教肯定地說。然而,在他離開期間,國王向阿拉麗卡求婚,並得到了她的接受。他們出發前往奧西丹特,但當談到如何處置費迪南德時,阿拉麗卡建議讓他與他們同床共枕。國王對這個建議感到震驚,不再知道自己會怎樣。雖然阿拉麗卡和費迪南德睡在同一張床上,但他們發現很難達成一致。“你應得的只是讓我把你像梳子在湯裡一樣,在你的想法中游蕩,”他說。與此同時,肖特蘭國王塞萊斯廷辛克要求知道一個陌生人為什麼在他女兒的臥室裡。她越來越奇怪,以至於塞萊斯廷辛克懷疑他的女兒瘋了。“邪惡蔓延。一隻雪貂!一隻雪貂!無論如何都要讓它蔓延,”她說。塞萊斯廷辛克下令逮捕費迪南德。阿拉麗卡不同意這個決定。到目前為止,她的生活只是為了“掩蓋我兇猛的當前龍捲風,”她說。在阿拉麗卡的啟發下,費迪南德提議在肖特蘭土地上進行重大改進,令元帥感到震驚,他發現他的計劃“完全驚人”。阿拉麗卡提議副官和元帥放棄對他們父親的忠誠,完全服從她和她的丈夫,成為肖特蘭的女王和國王。他們同意。“邪惡蔓延,”阿拉麗卡高興地總結道。
阿圖爾·阿達莫夫
[edit | edit source]
阿圖爾·阿達莫夫(1908-1970)是另一位超現實主義劇作家,他的成名之作尤其在於在《入侵》中呈現了作家的困境(《入侵》,1950年)。
“至少我們可以說,皮埃爾的生平,以及在較小程度上其他人的生平,都被讓的難以解讀的遺產所入侵。然而,一個真正的問題是,讓是否知道自己在寫什麼。因此,我認為,我們完全有理由將手稿視為一種象徵,象徵著不可辨認的意義,這種意義從本質上入侵了生命……因此,皮埃爾成為了一種現代人的典型,他陷入試圖發現生命的意義的任務中,而生命的意義仍然模糊不清,同時,他又無法放棄這種鬥爭。皮埃爾的策略是放棄一切集體努力,獨自追求一種禁慾的生活方式。因此,他的個人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宗教探索的特徵,這種宗教探索是在隱居中進行的。當他獨自一人在房間裡時,他拒絕與任何人交談。他的母親用托盤送來食物,但沒有和他交談……艾格尼絲的存在總是代表著更新的可能性。在第一幕中,她是使用打字機的人,一種交流工具。當她在身邊時,房間很凌亂,但感覺是在混亂中存在著創造性的可能性。然而,隨著皮埃爾越來越從他與艾格尼絲的關係中抽離,這些可能性減少了。然後,當皮埃爾退縮到孤獨中時,艾格尼絲的性意義轉移到第一個出現的人身上,艾格尼絲就和她的新情人離開了。我們從她回來拿打字機時得知,第一個出現的人病倒了,她只能努力維持他的生意。因此,也許,瓦解和更新都體現在她身上,但就她與皮埃爾的關係而言,更新仍然是一種可能性。當皮埃爾在最後對他的母親評論說,如果艾格尼絲有更多的耐心,他們兩個人就能在手稿上開創一個新的開始,一個四月式的更新的話,這種可能性就被強調了。但這種可能性最終被母親挫敗了,皮埃爾的命運被封印了”(Sherrell,1965年,第401-403頁)。
“皮埃爾、艾格尼絲和他們的朋友兼合作者特拉德爾,他們之間意見不一致,無法實現集體的重新單一化,使他們能夠有效地抵抗母親及其同夥的入侵……母親是一個入侵者。她在她兒子的公寓裡住了下來,逐漸將自己對秩序的標準強加於此……房間整潔有序,移民也被阻止了。隨著場景的推進,皮埃爾消失在他的房間裡,獨自一人死去。他是否自殺尚不清楚,但透過鼓勵艾格尼絲離開,然後阻止她回來,母親無疑促成了他的死亡……皮埃爾、艾格尼絲和特拉德爾無法聯絡起來,制定出抵抗保守勢力的策略,因為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他們共同的利益。觀眾可以看到母親的權力攫取,但那些將受到這種權力攫取最嚴重傷害的人卻看不到”(Chamberlain,2015年,第154-155頁)。
“死者的檔案對皮埃爾來說既是一種職業,也是一種對意義的探索,儘管在整部戲劇中都有諷刺性的暗示,表明讓的遺產可能並沒有表面上那麼大……艾格尼絲本人似乎代表著混亂;畢竟,正是透過她,皮埃爾才與她的兄弟及其檔案有了牽連……《入侵》對工作的有效性以及愛和友誼的有效性提出了嚴重的質疑;阿達莫夫似乎在說,這就是所有人類努力的最終結果:徒勞”(Parsell,1986a年,第15頁)。
“《入侵》強調了真理的相對性,在一個絕對真理無法獲得的世界中,標題指的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它入侵了已故作者的家人和朋友的生活。這些人費力地試圖破譯筆跡,澄清作品,最終以一種令人沮喪的僵局告終,因為除了他們自己之間意見不一致外,他們還對每一個詞都有不同的解讀,直到沒有人能確定真正的含義”(Bishop,1997年,第56頁)。
“關於某些關鍵段落的轉錄和含義存在著廣泛的分歧。皮埃爾努力整理他朋友的作品失敗了;在這個過程中,他失去了妻子、朋友,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皮埃爾的危機發生在他不再能感受到語言的活力之時……當他說語言失去了空間存在的性質時,他的意思是思維不再可能,因此他的存在本身也危在旦夕”(Bradby,1991年,第83-84頁)。
《入侵》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50年代。地點:法國。
文字在?
彼得努力破譯妻子艾格尼絲已故兄弟留下的手稿。他慢慢地整理著這些文字,艾格尼絲則負責打字。他們的朋友特拉德爾也提供了幫助,但這兩個男人在處理方法上意見不合。彼得認為應該獲得最準確的逐字逐句版本,而特拉德爾則認為應該獲得一個近似的版本,透過他們對文字含義的直覺理解來完成。由於分歧,彼得獨自工作,儘管特拉德爾警告他們必須抓緊時間,因為已故朋友的家人正在尋求法律途徑獲得這些檔案以供自己使用。彼得認為他們對此無能為力。一個陌生人出現,要買下隔壁的公寓。這個陌生人對看起來很悲傷的艾格尼絲心生憐憫,而她卻幾乎完全被專心致志的丈夫忽視了。彼得無法繼續他的工作,決定暫時放棄,住在他們公寓裡一間僻靜的房間裡,免受任何打擾。“只要事情沒有呈現出一定的視角,我就無法得到安寧,”他斷言。艾格尼絲和特拉德爾不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彼得的母親像往常一樣給他送飯,但他警告她不要對他說話。當彼得躲進小房間後,陌生人毫不猶豫地向艾格尼絲表達了自己的愛意。他們一起離開了,令彼得的母親忍俊不禁,她笑著拍著大腿。當彼得從房間裡出來時,他準備過上普通的生活。他撕毀了那些他花費了大量時間整理的紙張,然後得知他的妻子離開了。他表示理解她的決定,考慮到他們在一起的混亂生活,但他的母親責怪她是混亂的根源。當他離開房間時,特拉德爾回來,透露艾格尼絲的家人準備從他們手中拿走這些檔案,但發現所有檔案都被撕毀了。出乎意料的是,艾格尼絲回來了,但只是暫時,因為她的朋友病了。短暫的交談後,母親把她推了出去。當特拉德爾尋找彼得時,他發現他已經死了。“我永遠不會原諒自己,”他說道。母親對這件事感到震驚,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
讓·熱內
[edit | edit source]
這一時期的另一位主要劇作家是讓·熱內(1910-1986),他的代表作有《女僕》(Les bonnes,1947)和《黑人》(Les nègres,1958)。
“《女僕》的開場是當代戲劇中最精彩的場景之一。完全摒棄了鋪墊,它將我們直接帶入到我們最終會理解為兩個女僕姐妹定期進行的儀式中。觀眾最初會被女主人和她的女僕的怪異行為所迷惑,但他們會發現一種將她們聯絡在一起的、風格化的支配遊戲……姐妹們每天進行的結構化的幻想之旅是她們在令人窒息的現實中生存的方式。她們對“夫人”的舞臺化反抗使她們不必反抗真正的“夫人”……事實上,當我們在劇中看到真正的“夫人”時,她顯然不是儀式中描繪的暴君,但這絲毫沒有改變女僕們的看法。她們反抗的需要是真實的,但她們反抗的願望被她們對“夫人”的迷戀所破壞。因此,她們滿足於模擬反抗,這種反抗既針對彼此也針對“夫人”,是一種刻意限制的風格化表演,旨在僅止於謀殺之前”(Bishop,1997年,第125-127頁)。從《女僕》一開始,索朗日就扮演著她的女主人“專橫和侮辱”的角色……女僕們對夫人的反應是矛盾的,混合著仇恨和愛,嫉妒和崇拜,其中仇恨和嫉妒占主導地位……“女僕”中的戲劇衝突是僕役地位或角色與夫人地位之間的衝突”(Jacobsen and Mueller,1976年,第138-143頁)。“這兩個女僕之間存在著相互憎恨的紐帶,她們是彼此的映象……同時,在夫人的角色中,克萊爾將所有僕役視為上層階級的扭曲映象。因此,她們在彼此身上憎恨的反射,是她們崇拜、模仿和憎恨的,安全的主人們世界的扭曲反射”(Esslin,1974年,第174頁)。“戲劇對話一開始顯得奇怪地漫無目的——她們似乎只是在談論自己、她們的處境以及她們想要改變的方式——但觀眾逐漸開始理解她們討論背後的戲劇驅動力:她們試圖說服自己進入一種轉變狀態,在那裡她們可以逃脫她們受限的存在,成為她們不是的東西:自由主體。因為在熱內的戲劇中,表現的目的是不是為了表現世界本來面目,而是為了表現我們透過想象力構建的我們自己和塑造那些想象中的自我的力量的誇大和扭曲……女僕們反覆宣稱她們對夫人的忠誠,可以被看作是她們渴望分享夫人所擁有的存在,而不是簡單的愛情表達。她們痛苦地意識到夫人是如何恩賜她們,如何僅按照她的心情變化對待她們,而沒有考慮她們的感受,但她們仍然認為,與她們相比,夫人的存在非常令人嚮往”(Bradby and Finburgh,2012年,第35-36頁)。“因為她們如此憎恨自己的位置,她們也憎恨彼此和自己。正如索朗日所說,“汙垢不喜歡汙垢”。僕人們因為這種憎恨而失敗了。正如馬爾羅和薩特提到的,“革命只有在受壓迫者能夠將自己的現狀視為未來尊嚴的潛在來源時才有可能”……索朗日和克萊爾沒有其他價值觀可以提供……她們想擁有夫人的品質,雖然她們無法做到這一點的憤怒可能會在謀殺的夢境中表達出來,但最終她們只是懲罰了自己”(Thody,1968年,第165-167頁)。“當夫人出現時,她並不是我們所期望的可怕人物,而是一個相當普通、富有、過於浪漫、膚淺的世俗女人……克萊爾現在意識到,她們對夫人的第一次行動必須是殺死她們自己內心的那些她們如此憎恨的夫人元素——她虛偽的優越感和她的自以為是……索朗日的最後一段話是第一次誠實而平靜的”(Gascoigne,1970年,第191頁)。Henning(1980年)認為,“當夫人回來時,迴圈似乎已經完成。但這同樣只是幻象。僱主自己並不是她最初看起來的那樣真正的資產階級夫人,也不是真正為她所愛的男人而受苦的忠誠女人。她也只是在扮演一個角色。她的行為甚至像是女僕們開場儀式動作的模仿。她自己只是另一個替代君主……克萊爾確實表現出她們夫人的行為,但在女僕們的私人儀式中,是索朗日,而不是夫人,扮演著僕人的角色。因此,角色的儀式逆轉只實現了一部分,僕人們只能貶低自己”(第80-81頁)。“女僕們穿著制服和夫人的衣服,在多個方面具有雙重身份:受辱的苦工和勝利的復仇者,囚犯和想象中的旅行者,創造者和廚房爐灶的奴隸,她們還添加了另一種形式的二元性,即孩子和成年人……當克萊爾穿上夫人的衣服時,必須用別針別起來,因為她太小了,無法穿下成年人的衣服。克萊爾和索朗日可能沒有長大,這一點可以從她們睡在摺疊床上得到進一步證明。雖然她們把自己的生活獻給了復仇,但她們在房間裡以虔誠的孩子的方式背誦祈禱文。她們用護身符裝飾閣樓,包括夫人的花束,這表明孩子拒絕放棄任何財產”(Hubert,1969年,第204-205頁)。“女僕們模仿夫人,因為她們渴望被融入社會貴族階層……克萊爾和索朗日除了與夫人之間的關係之外,沒有自己的身份;因此,她們想擁有唯一定義她們存在的人……夫人美麗、善良、富有,是男人的磁石;女僕們醜陋、惡毒、貧困,沒有男性朋友。克萊爾和索朗日因無法改變她們的社會或經濟地位而感到沮喪,因此嫉妒並因此鄙視夫人,她對僕人的恩賜態度只會加劇她們的復仇慾望。女僕們憎恨屈服,感到無法誠實地與她們的“保護者”說話,並且在夫人周圍越來越受到性壓抑,夫人的本質是由她的效能力定義的。克萊爾和索朗日參與了一種儀式化的儀式,旨在摧毀“夫人”的精神,以便這些被排斥的人……可以超越她們低下的地位,蔑視已建立的統治階級”(Plunka,1992年,第176-177頁)。“夫人當然是被包養的女人,因此與女僕們本身有著奇特的關係。她實際上是另一個次世界的成員,當然比女僕們更高的次世界,但無論如何都是次世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她也依靠幻想和想象生活。我們立即從她戲劇化地描述了先生被捕的方式中看到了這一點。她並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被疏遠了,就像女僕們一樣。我們還進一步看到,她在與先生的關係中扮演的角色實際上是兩個女僕角色的原型。她現在講述了關於他被捕的故事,匿名信以及她在整個事件中扮演的英勇角色。索朗日試圖安慰她。她說先生是無辜的,將會被無罪釋放。“他是,他是,”夫人回答。然而,一個錯誤的音符出現了。我們瞭解到夫人很享受她作為殉道者和聖徒的角色。無論發生什麼,她都會忠於先生。她會從一個監獄追隨他到另一個監獄。她會放棄她優雅的生活,她的香奈兒定製的漂亮衣服,她的皮草。她甚至對她的兩個僕人表現出虛假的同情。她們會一起退休到鄉下。她們會忠於她,她會照顧她們”(Pucciani,1963年,第53頁)。“這部非凡的戲劇,它擁有完美的單幕結構,壓倒性的戲劇張力,以及思想和象徵的密度,被公認為當代戲劇的傑作之一。這是一部關於面具和雙重的戲劇,關於身份的虛無縹緲”(Coe,1986b年,第682-683頁)。
“黑人”這個詞是對白人對黑皮膚人民的看法、言論以及他們因偷偷摸摸的內疚和壓抑的厭惡而無法說出口的蔑視的諷刺和嘲弄。這一切都帶著一絲微笑,這微笑缺乏幽默感,但會激起人們的恐懼的笑聲”(克魯爾曼,1966 年,第 74-75 頁)。“拒絕了普遍的愛這一‘白色’價值觀,儀式參與者必須努力發現絕對的仇恨。儀式核心是 Village 對白人女性的謀殺重演。舞臺中央擺放的靈柩據說是她的屍體,並且關於 Village 是否被她吸引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這對負責儀式的 Archibald 很重要,因為他必須確定這是否是一起出於純粹的仇恨而犯下的罪行:‘他的罪過救了他。’” (Bradby 和 Finburgh,2012 年,第 75 頁)。“主要的問題是……Village 是否出於正確的動機和精神犯下了謀殺。他的行為是否以一種能充分體現黑人靈魂的方式執行?……因此,Village 就有必要重演謀殺……Archibald 提醒他們目標:‘我們必須贏得他們的譴責,讓他們做出判決,讓我們受到譴責’……他們必須符合白人定義的黑人概念。但是,[之後] 黑人已經走向……他們自己行為的決定者……法官……震驚於沒有發生謀殺,看到了自己角色的消失……被附身者……必須止步於謀殺……因為[那] 會剝奪[他們]的佔有”,因此角色發生了逆轉(Jacobsen 和 Mueller,1976 年,第 158-162 頁)。“在彼此的關係中,Village 和 Virtue 無力為力;他們都是黑人,他們的黑人身份是否定,僅僅是白人的一種功能。它自我實現的唯一機會是顛倒影像和倒影的角色。只有透過摧毀、征服、統治或吸收白人,透過堅持自己的價值觀來對抗征服者的價值觀,黑人才會成為影像,而白人則會淪為鏡中之像”(Coe,1968 年,第 292 頁)。舞臺事件與幕後起義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為觀眾上演的戲劇是一種欺騙,掩蓋了舞臺上黑人的真正動機:一種儀式性的自我毀滅和隨後對白人價值觀的驅除,產生了一種通往新身份的過渡儀式……觀眾席上的白人很樂意看到黑人模仿白人文化……黑人與 19 世紀殖民主義者對非洲的野蠻原始世界的看法相關聯……法庭,由戴著白色面具的黑人扮演,代表著白人社會,或者至少是黑人對白人社會的刻板印象……黑人剝奪了白人權威和力量,建立了自己的身份,並開始做出自己的判斷,這些判斷體現在幕後對一名黑人叛徒的審判中……Diouf,以 Marie 的身份,生下了五個代表著白人法庭的玩偶……[象徵著] 白人種族的滅亡”(Plunka,1992 年,第 226-233 頁)。“儀式的目的是瓦解白人形象,起義的目的是瓦解白人”(Brustein,1964 年,第 408 頁)。“在 Genet 的戲劇中,所有白人都是制服的,他們代表的不僅僅是他們自己。事實上,他們是權威的象徵。在殖民地非洲,當地秘密社團和社交俱樂部經常為他們的官員提供女王、總督、法官和傳教士的服裝和頭銜,因此既模仿了白人,又挑戰了他們對權威象徵的壟斷”(Graham-White,1970 年,第 210-211 頁)。“法庭由戴著白色面具的黑人組成。這些戴著面具的人暗地裡渴望顛倒事物的秩序,成為壓迫者,成為權威的聲音。但他們很清楚自己屬於黑人無特權種族……白人法庭的成員想要履行他們的義務,這表明他們對未來抱有一定的信心;然而,他們不想以白人的身份履行他們的職責,而是以黑人的身份”(Knapp,1968 年,第 137 頁)。“這出戲中的法庭是無效的。必須由黑人審判他們中的一員。白人法庭無效的部分原因是他們無法進行正常的對話。他們的講話充滿了隨機的爆發,導致審判無果而終。對這一點的解讀可以是白人法庭無法理解和解釋黑人罪行……另一種解讀可以是……正義對黑人來說是不可能的”(Bennett,2011 年,第 82 頁)。“摧毀白人形象被認為是改善他們狀況的唯一途徑。黑人在獲得政治獨立、能夠享受除了仇恨之外的其他情感的目標上與白人作鬥爭”(Thody,1979 年,第 199 頁)。“‘黑人’首先以莫扎特的旋律跳著小步舞曲圍繞著一個靈柩,靈柩佔據舞臺中央。雖然他們的動作中明顯帶有模仿的元素,但小步舞曲象徵著黑人對白人文化的奴役。這種奴役是這出戲的起點和終點”(Oxenhandler,1975 年,第 422 頁)。“演員分成兩組出場……但最終的舞臺形象是團結一致的:‘所有黑人——包括那些曾經是法庭的人,現在沒有面具——站在一個用白色覆蓋的棺材周圍……白人社會的傳統價值觀被嘲笑、貶低,並淪為‘演奏查爾斯·古諾的曲子’、編織‘給煙囪掃煙的人用的毛線帽’、在‘風琴上唱歌’和在星期天祈禱……演員正在為 Diouf(偽裝成白人受害者)的‘謀殺’而激動起來,這時 Village 停止了行動。到目前為止,Village 一直努力地用反覆出現的旁白向觀眾解釋他的行為,但現在整個儀式將超出觀眾的理解範圍,因為敘述讓位於魔法……在 Diouf 的敘述中,法庭與儀式中的演員融為一體。他們為模仿的動作鼓掌和歡笑,就好像它們是真的。與此同時,被困在舞臺上的白人觀眾,他的手被編織的毛線帽綁著,可以說,除了看著之外,無能為力……這出戲的行動不是為了解決最初情境的衝突;相反,它傾向於加劇它們”(Webb,1969 年,第 455-458 頁)。“傳教士……自豪地宣稱,白人信徒默許,黑人信徒則感到困惑地拒絕,上帝是白色的,這個信念在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用來阻止敬畏上帝的黑人尋求爬上平等階梯的頂峰。‘兩千年來,上帝一直是白色的。他用白色的桌布吃飯。他用白色的餐巾擦拭白色的嘴。他用白色的叉子挑著白色的肉。’黑人意識到,他們最終的精神解放只有在他們能夠拒絕和修改白人使用的顏色符號之後才能實現。因此,Felicite 在這出戲的最後說道:‘一切都改變了。任何溫柔、善良、美好和溫柔的東西都將是黑色的。牛奶將是黑色的,糖、米飯、天空、鴿子、希望都將是黑色的’……這出戲中的黑人從強調社會反對他們的觀點和看法中獲得極大的樂趣……從一開始,黑人就進行著一種黑人美麗的儀式,從不放過任何機會來強調他們的黑人身份,如果他們表現出不這樣做,就會受到斥責。Archibald,他一直在推動劇情發展……建議 Neige:‘你想變得更有吸引力——還剩下一些黑粉’”(Warner,2014 年,第 201-203 頁)。“整部戲都是一首仇恨的讚歌:黑人對白人的憎恨被故意地渲染和讚美……靈柩在整部戲中都以視覺形式佔據舞臺中央。因此,正是所有種族主義恐懼中最深刻的一種,即種族間性嫉妒,被 Genet 利用”(Martin,1975 年,第 519-522 頁)。“無論他的白人觀眾對黑人在做什麼持多少反對意見,他們並不是為了邪惡本身而尋求邪惡,而是為了可以理性地表達的政治目標:獨立、自由、自尊”(Thody,1968 年,第 200 頁)。
Antonin Artaud 預示了 Genet 的戲劇在創造神話的目標、將語言用作咒語、傳達情感而不是交換思想、以及使用“音樂、舞蹈、造型藝術、啞劇、模仿、手勢、語調、建築、佈景和燈光”等形式的視覺和聽覺輔助方面的先見之明 (Artaud, 1938)。“Genet 從一個完全解放的潛意識的深處汲取了他的神話,在那裡,道德、抑制、優雅和良知沒有任何影響;他的作品的基礎是 Artaud 認為是所有偉大神話根源的黑暗性自由”(Brustein,1964 年,第頁)。“Genet 的所有戲劇都向我們展現了反社會。監獄、妓院、黑人或叛亂者的世界都是透過反對傳統、習慣、正確思考的社會來定義的。生活在這些世界中的人們都知道,他們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意識本身都是由他人的蔑視所決定的。但 Genet 的戲劇並沒有像一些荒誕劇那樣,在一個噩夢般的恐怖景象中消解所有社會差異。相反,他們精確地考察了將壓迫者與被壓迫者聯絡在一起的相互依賴的層次,他們展現了變形儀式,在這些儀式中,被壓迫者透過接受和誇大自己的處境,希望將恥辱轉變為自豪,改變遊戲的規則,從而扭轉壓迫者的局面”(Bradby, 1991 年,第 179 頁)。
"女僕們"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40 年代。地點:法國。
文字位於 https://web.mit.edu/jscheib/Public/phf/themaids.pdf https://pdfcoffee.com/genet-jean-the-maids-amp-deathwatch-grove-1954pdf-2-pdf-free.html
克萊爾命令她的女僕索朗日,讓她穿上所有的華服。她不斷地指責激怒了索朗日,讓她怒火中燒。她打了克萊爾,並威脅要做出更糟糕的事情,直到鬧鐘響起,克萊爾才喊到:“快走吧,夫人要回來了。”克萊爾也是一名女僕,她們只是在玩角色扮演遊戲。克萊爾責怪她姐姐總是遲到,因此她們永遠無法到達殺害主人的時刻。儘管她們在奴隸狀態中存在著固有的挫折,但克萊爾仍然認為,在內心深處,他們的女主人愛著她們。“是的,”索朗日諷刺地評論道,“就像她廁所裡的粉色琺琅一樣。”為了報復她們在角色扮演之外的命運,克萊爾給警察寫了一封匿名信,指控她主人的情人搶劫,導致他被捕。索朗日打算走得更遠,透露她曾經在主人睡覺時動過殺她的念頭,但她行動時卻膽怯了。“她會用她的溫柔腐蝕我們,”她警告道。令她們沮喪的是,克萊爾從電話中得知那個人被保釋了。克萊爾更加責怪她姐姐沒有殺掉她。現在,她們很有可能被指控為誣告而入獄。“我已經受夠了做蜘蛛、傘柄、骯髒無神的無家可歸的修女,”克萊爾沮喪地說。她們又編造了更多針對她們主人的指控,但毫無實際作用。“可是我們不能為了這麼點小事就殺了她,”索朗日承認道。她突然改變了主意,建議在她們主人的菩提花茶中溶解巴比妥類藥物。她們的主人走了進來,為她情人的處境而感到難過,準備追隨他到遙遠的監獄。“我會擁有更新更漂亮的衣服,”她決定道。她給了克萊爾她的絲綢長裙,給了索朗日她的毛皮大衣。然後,她注意到電話沒有結束通話。索朗日脫口而出,說她的情人打電話了。她被引導著透露,她的女主人將在一家餐廳與他見面。女主人想要立刻加入他,在喝下毒茶之前就離開了。“所有的陰謀都無濟於事。我們完蛋了,”克萊爾總結道。索朗日建議她們逃跑,但克萊爾認為這個建議不切實際,因為她們都很窮,無處可去。她們毫無用處地詛咒著她們的奴隸身份。在絕望中,她們又開始玩角色扮演遊戲,這次是索朗日扮演女主人,要求她的茶。但克萊爾又重新扮演了女主人,吞下了毒茶,而索朗日的手交叉在一起,彷彿已經被手銬銬住。

時間:1950年代。地點:白人殖民統治的非洲。
文字在?
一群黑人在舞臺上表演了一個白人女性被謀殺的場景,觀眾是另一群偽裝成白人的黑人,包括女王、總督、法官、傳教士和一個僕人。阿奇博爾德·阿布薩隆·韋靈頓是儀式主持人,引導著表演的精神,對白人殖民統治的仇恨越來越深。在靈車前,阿奇博爾德問村民早上發生了什麼事,村民回答說他親手勒死了名叫瑪麗的白人女性。聽到這個訊息,女王悲痛欲絕。“放心,陛下,上帝是白人,”傳教士安慰她說。當一些黑人分心,無法為任何有價值的事業做出貢獻時,阿奇博爾德提醒他們,他們必須贏得法庭的譴責。在他們的舞臺表演中,瑪麗的角色由牧師迪奧夫扮演,瑪麗母親的角色由妓女菲利西蒂扮演,還有一個人叫博博是她的鄰居。當瑪麗和即將強姦並謀殺她的人說話時,她的母親一直在大聲哭喊著她的“糖果和阿司匹林”,並提醒她說該祈禱了。鄰居走過來提醒瑪麗,如果她繼續在黑暗中工作,她的眼睛可能會毀掉。在晚上,瑪麗彈鋼琴,這是女王認可的一種藝術:“即使在逆境中,在崩潰中,我們的旋律也會唱出來,”她熱情洋溢地宣稱。瑪麗意外地即將臨盆。鄰居作為接生婆趕到,從她胸前的衣服下拿出了代表五位法庭成員的玩偶。然後她被謀殺了,法庭召開會議譴責兇手。傳教士認為受害者應該被封為聖徒,但女王不確定這個想法是否明智。“畢竟,她被玷汙了,我希望她能堅持到最後,但她可能會讓我們想起她的恥辱,”女王思考道。在法庭審判期間,黑人暴動起來,五位法庭成員必須逃脫他們的憤怒。為了緩解他們在道路和田野上行進時的疲憊,傳教士批准使用酒精飲料。然而,他們喝醉了。“只有在晚上跳舞,沒有人會不打算讓我們死。停下。這是一個可怕的國家。每一叢灌木叢都隱藏著一個傳教士的墳墓,”傳教士警告他們說。法官成功地重新組織了法庭,黑人人口的成員開始顫抖,但他們的領導人之一菲利西蒂站了起來挑戰女王。另一位黑人領導人維爾·德·聖納澤爾透露,他們內部的一個叛徒已被處決,但找到了新的叛亂領導人。法庭成員被包圍了,但女王告誡他們要勇敢面對逆境。“向那些野蠻人展示我們偉大之處,在於我們對紀律的重視,以及向那些觀看的白人展示我們值得他們流淚,”她宣稱。儘管受到這樣的鼓勵,但法庭成員一個接一個地被處決了。

荒誕戲劇起源於1940年代的法國,其主要倡導者之一是出生於羅馬尼亞的尤金·艾翁斯科 (1909-1994),他的作品包括 "光頭女歌手" (更準確地說是 "光頭女主角",1948年) 和 "犀牛" (1959年)。“艾翁斯科和貝克特都致力於向他們的觀眾傳達他們對人類狀況荒謬性的感受”(埃斯林,1960年,第671頁)。“如果一部好的戲劇(以現實主義風格)必須有一個巧妙構建的故事...[荒誕戲劇]沒有故事或情節可言;如果一部好的戲劇是根據人物刻畫和動機的微妙性來評判的,那麼這些戲劇往往沒有可識別的角色,而是向觀眾呈現幾乎是機械的木偶;如果一部好的戲劇必須有一個充分解釋的主題,該主題被清晰地揭示並最終解決,那麼這些戲劇往往沒有開頭也沒有結尾;如果一部好的戲劇要照亮現實,並以細緻入微的寫實手法描繪時代的風俗和習性,那麼這些戲劇似乎往往是夢境和噩夢的反映;如果一部好的戲劇依賴於機智的妙語和尖銳的對話,那麼這些戲劇往往充滿了語無倫次的胡言亂語”(埃斯林,1974年,第3-4頁)。“荒誕的慣例源於一種深深的幻滅感,即對生活中意義和目的的感知的消退,這在二戰後的法國和英國等國家很常見。在美國,沒有相應的意義和目的的喪失”(埃斯林,1974年,第266頁)。與加繆的論文 “西西弗神話” 和薩特的《噁心》不同,這兩部作品都從理性角度探討了非理性,艾翁斯科和其他荒誕戲劇的成員以非理性的方式處理了非理性。“非理性主義戲劇不僅僅是一種攻擊理性主義偶像的戲劇,即透過科學實現幸福的無限進步...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種旨在成為非理性真實表達的戲劇”(杜布羅夫斯基,1973年,第12頁)。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荒誕戲劇或帶有荒誕元素的戲劇盛行,以至於在費吉看來(1986年),“只有荒誕劇本身不是荒誕的”(第204頁)。
在《禿頭歌女》中,“人類狀況的圖景……是殘酷而荒謬的(在沒有意義的意義上)。在一個沒有目的和終極現實的世界裡,中產階級的禮貌交流變成了腦殘木偶的機械化、無意義的滑稽動作。個性和性格,與每個人的靈魂終極有效性的觀念有關,已經失去了意義……觀眾對機械化無意義對話的意義一無所知,就像人物本身一樣。這部作品是對禮貌對話語言的解體和化石化的野蠻諷刺(這與反諷完全不同),是對失去所有個性的、甚至性別特徵的角色的可互換性的諷刺。這些角色過著毫無意義、荒謬的生活……我認為,……笑聲的來源並非來自任何諷刺,而是來自觀眾自身壓抑的挫敗感。透過看到舞臺上的人機械地表演日常交往的空洞禮儀,透過看到他們被簡化為機械木偶在完全的虛空中行動,觀眾在認出自己在這幅圖景中的同時,也能感受到自己優於舞臺上的角色,因為他們能夠理解其荒謬性——這會產生狂野的、解放性的笑聲——一種基於內心深處焦慮的笑聲”(艾斯林,1960 年,第 671-672 頁)。這部劇“幾乎完全是透過諷刺手法來誇張地描繪資產階級生活的空虛……可怕的是……它與每晚在中產階級家庭裡進行的平淡無奇的談話非常相似……這些角色用禮貌語言的陳詞濫調和傳統行為的程式化來掩蓋他們的無聊和彼此之間的厭惡。他們的生活變得如此機械化,以至於他們無法學習任何東西”(阿博特,1989 年,第 159 頁)。“對話主要以獨立的語句的形式出現,很少嘗試相互交織……當對話開始時……談話只不過是意義的破壞……[當] 馬丁夫婦被介紹時……對話……源於他們對他們平行存在巧合的相互驚奇。這個過程與未能引起驚訝的不協調相反;在這裡,意料之中的事情引起了刻板的驚奇”(格羅斯沃格爾,1962 年,第 53-54 頁)。《禿頭歌女》呈現了“角色……已經失去了人性……他們甚至沒有關於美好時代的記憶,他們在落幕時與開始時一樣,似乎不關心任何可能從他們被囚禁的處境中解脫出來——事實上……他們沒有意識到任何囚禁……缺乏任何對他們狀況的悲劇感……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很少讓人感到驚訝,[比如消防員按門鈴],普通的事情卻讓人感到難以置信”(雅各布森和穆勒,1976 年,第 46-54 頁)。史密斯夫婦和馬丁夫婦之間的談話源於掌握一門新語言的說明手冊(海曼,1976 年,第 17 頁)。“劇中日常語言的錯位是漸進的,經歷了幾個階段。在劇的開頭,語言的主要特點是其純粹的無意義……依翁斯科對語言的攻擊的第二階段涵蓋了劇的其餘大部分;它從史密斯先生開始說話開始,一直持續到消防隊長離開(第十幕)。一旦獨白變成對話,就明顯看出,這部劇的世界所遵循的邏輯與觀眾世界所遵循的邏輯毫無關係。在這部分劇中,禮貌對話的形式基本保持不變,但其內容卻扭曲而古怪”(萊恩,1994 年,第 31-32 頁)。“史密斯夫婦和馬丁夫婦……缺乏身份。這些角色彼此模仿,因為缺乏想象力,鸚鵡學舌般地重複著當代的陳詞濫調和老生常談,因為他們太渴望取悅別人,以至於他們失去了群體之外任何自我意識”(克拉斯納,2012 年,第 308 頁)。“馬丁夫婦的問題是,儘管他們被介紹給我們時是夫妻,但他們彼此並不瞭解……我們看到一對典型的夫婦,結婚多年,卻彼此不瞭解”(韋爾沃斯,1971 年,第 62 頁)。“鐘聲敲了十七下,史密斯太太宣佈現在是九點。一個笑話?當然是一個笑話。但它也表明,一天中具體的時間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從一小時到另一小時,從一天到另一天,他們的生活基本上是一樣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對夫婦的名字叫史密斯:一個非常傳統、平淡無奇、中產階級的名字,適合傳統、平淡無奇、中產階級的人……當史密斯夫婦討論鮑比·沃森時,資產階級成員生活中的一致性以及缺乏活力被揭示出來……一個資產階級與另一個資產階級之間存在模式沒有區別……依翁斯科經常採用一種怪誕的顛倒常態的方式。他透過選取一個熟悉的情景,在那個情景中注入一個使其完全不可能的元素,然後像那個不可能的元素不存在一樣寫下場景。當馬丁夫婦進來時,就出現了這樣一個場景……依翁斯科不僅對雞尾酒會上的談話進行了精彩的諷刺,而且——更重要的是——對資產階級沉迷於無關緊要的事物的諷刺。起初,每個人物都試圖找到一些深刻的東西來打動別人。結果就是一大堆陳詞濫調……史密斯先生走到門口,然後帶著消防隊長回來……[對門鈴事件的解釋] 使所有相關人員都滿意,因為這是資產階級解決爭議的經典方式:選擇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間道路……女傭進來,結果是消防隊長的愛人。在這裡,激情也消失了,因為正如消防隊長所說,‘是她熄滅了我最初的火焰’……當消防隊長離開時,依翁斯科又呈現了這些人的生活枯燥乏味的另一個例子。聚會上的談話變成了陳詞濫調的連串:‘各人自掃門前雪’、‘英國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愛人者人恆愛之’——[這些] 彼此之間沒有邏輯上的聯絡”(杜科爾,1961 年,第 176-177 頁)。萊恩(1996 年)列舉了邏輯話語的破壞,包括偽解釋(病人死亡是因為手術失敗)、錯誤的類比(一個盡職的醫生必須像沉船的船長一樣與病人同歸於盡)、矛盾(史密斯夫婦已經吃過晚飯,直到女傭進來)、似是而非的推理(當門鈴響起時,是因為沒有人在那裡)、對顯而易見的事情感到驚訝(為什麼報紙從來不刊登新生兒的年齡)、人名不可靠(沃森一家)、失語症(一個女人被勒死,因為她以為煤氣是梳子)、言語行動矛盾(消防隊長說他會脫帽,但不會坐下,而他卻做了相反的事情)。這些人物缺乏任何可辨別的動機、理性或內心生活,相反,他們就像木偶……彼此沒有區別,也與周圍環境沒有區別,他們被語言穿透,語言利用他們,而不是相反”(第 32-39 頁)。
“犀牛”將幻想與現實融合,透過將角色變成犀牛的荒謬手法,來表達強烈的政治觀點,並對社會壓迫的本質進行評論。 “犀牛”甚至透過讓一個角色問貝蘭傑是否讀過尤涅斯庫的劇本,模糊了虛構與現實之間的界限,從而模糊了表現與真實的界限”(薩迪克,2007 年,第 31 頁)。“意志的嚴重癱瘓、想象力的空虛、官僚腐敗、惡毒的威權主義、自私自利的利益、自我吹噓的自我吹噓,以及最重要的,為了個人利益而無情地取悅他人的需求,對尤涅斯庫來說是現代文化困境的象徵。左翼和右翼極端主義的喧囂,在穿梭於城鎮的犀牛群的轟鳴聲中得到體現。犀牛象徵著缺乏遠見的權力過剩;對尤涅斯庫來說,我們生活在悲劇的時代……因為我們改變環境的力量已經達到了死衚衕”(克拉斯納,2012 年,第 313-314 頁)。“宿命論和冷漠成為常識……尤涅斯庫對犀牛心態的呈現如此令人信服,如此具有說服力……是因為它得到了親屬關係模式的強化……家庭感情凌駕於本應凌駕於家庭感情之上的一切”(霍奇森,1992 年,第 135 頁)。“當第一頭犀牛打破了社群的禮儀時,他們的評論是令人愉快的不足……他們無法理解這場新入侵的意義,角色們逃離到無關緊要的事情中,這些事情迎合了他們的自尊心……他們的思想太靜態了。他們沒有原則。他們的想象力很遲鈍。他們只能重複生活中正常時期中的陳詞濫調。應該指出的是,唯一拒絕變成犀牛的人是頭腦最平凡,個性最少的人”(阿特金森和希爾斯菲爾德,1973 年,第 272-273 頁)。“貝蘭傑……是一個不太可能的英雄:他宿醉、衣衫不整、無方向。他非英雄的性格使他成為一個普通人,一個可能是,或可以激勵任何人的普通人。雖然普通,但他卻非凡。透過抵抗犀牛,他是唯一一個保留其獨特性的人,並且按照字面意思,沒有因為順從而變得沒有人性。此外,他不僅優先考慮自己的個性,也尊重他人的個性,在朋友和同事變身之前,對他們表示安慰和同情。因此,他是唯一一個具有心理深度的角色”(芬伯格,2015 年,第 119-120 頁)。貝蘭傑“從一個無精打采的懶漢變成了一個熱心捍衛一組不可替代的人類價值觀的捍衛者”(蓋恩斯鮑爾,1996 年,第 102 頁)。“他對犀牛的厭惡是發自內心的。‘僅僅看到它們就讓我心煩意亂,’他說。他無法表達,他不是用辯論而是用感情反駁約翰對犀牛的辯護”(萊恩,1996 年,第 114 頁)。“貝蘭傑……軟弱、困惑、害怕、酗酒。但他不會屈服”(布魯姆,2005a 年,第 248 頁)。“這部戲劇所傳達的是反抗的荒謬性,以及順從的荒謬性,這是一個無法加入快樂人群的個人主義者的悲劇,而這些人沒有那麼敏感”(埃斯林,1974 年,第 151 頁)。“在貝蘭傑的生活中,我們發現很少有值得捍衛的東西。在第一幕的開頭,他對他的朋友讓承認他感到無聊、疲倦,不適合他盡職盡責地完成的辦公室工作……劇中的其他角色在創造一種值得為之奮鬥的人性方面,並不比貝蘭傑更成功……如果意義深長的思考是存在的必要標準,那麼邏輯學家在舞臺上扮演了一個次要但令人難忘的角色,作為錯誤三段論的掌握者,比舞臺上任何人都沒有生命。他自信地無視邏輯限制前提,他得出結論說,四足生物一定是貓……貝蘭傑缺乏辨別力的標誌是他對邏輯學家的印象非常好……作為犀牛中那些假定角色所遭受的智力萎縮的最後一個例子,考慮一下學校教師博塔德的精神活動。就像幾年前那些拒絕承認人類真的登上月球的狂熱者一樣,博塔德斷然拒絕……報紙上關於犀牛存在的報道……當博塔德後來譴責學術界時,他實際上是在進行準確的自我評估:‘大學人士所缺乏的是清晰的思想、觀察能力、常識’……在戲劇中,人類文明的剩餘部分只是一些幾乎無法理解的人類語言碎片,邏輯的相互獨立的片段,以人類為名義的空洞人物……因此,當貝蘭傑在著名的那段長篇演講中逐漸完成反抗的姿態時,他的處境很尷尬,另一方面,也是對人類的辯護……他將如何與犀牛溝通?……無論對錯,在他看來它們是有吸引力的,而他對比之下卻很醜陋……他最後的幾句話與其說是英雄主義或勇敢,不如說是固執的愚蠢……[這出戲的教訓可能是:]為了非人性而存在的個人主義不是美德……獸性作為非理性人類存在的替代品不是缺點”(丹納,1979 年,第 210-214 頁)。“讓在譴責貝蘭傑的道德鬆懈,而教授則在舞臺的另一邊進行邏輯論證,他們最終說了完全相同的話,以完美的和諧相互呼應,儘管他們的意圖完全不同……然而,犀牛不連貫的咆哮能夠直接與那些開始感到被誘惑加入它們的人交流”(布拉德比,1991 年,第 76 頁)。貝蘭傑是唯一一個發生改變的角色。“只有他一個人不願把它們視為理所當然。從冷漠到參與,從瀕死到生,他的轉變是隨著他對一個又一個角色關於犀牛病的奉承的辯論而描繪出來的”(雅各布森和穆勒,1976 年,第 66 頁)。相比之下,杜達德認為犀牛病是“社群精神戰勝無政府主義衝動”的標誌(海曼,1976 年,第 110 頁)。約翰“一心想要保持表面現象……最虛偽和自以為是……挑剔,吹噓自己想象中的優於貝蘭傑……第一個放棄自己人性……博塔德是最傲慢、固執、不講道理……他最初斷然拒絕犀牛的故事……但……有強烈的責任感……遵守任何或任何擁有權力的人……杜達德是一個相對主義者。他平靜地做出反應……敦促最好的做法就是簡單地忽視這些野獸,讓自己適應不斷變化的時代……黛西……選擇“自然”的生活,稱犀牛為“真正的人類”(雅各布森和穆勒,1976 年,第 42-46 頁)。“博塔德和年輕的暴發戶杜達德一樣心胸狹隘,固執己見。博塔德懷疑且固執,他確信犀牛病的瘟疫是一個右翼陰謀,由媒體支援,被大眾所吞噬。博塔德否認鎮上有犀牛的存在,稱之為‘你們的宣傳’和‘臭名昭著的陰謀’的一部分,他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為了賺錢而採取的策略。博塔德指責記者捏造事實:‘他們不在乎他們為了出售他們可憐的報紙和取悅他們所服務的老闆而編造什麼’”(昆尼,2007 年,第 46 頁)。“這出戲,儘管主人公蔑視獸性,但本質上是無政府主義的、苦澀的、幾乎絕望的。理性思維和邏輯是荒謬的,尤涅斯庫告訴我們;它們與生活的真相(即混亂)幾乎沒有關係”(克魯曼,1966 年,第 86 頁)。相比之下,貝內特(2011 年)提出,“極權主義政權取得成功的很大程度上是大眾的 complacency。但犀牛沒有已知的捕食者(除了人類),而且可能是有史以來人們最不願意想到可以被趕來趕去的動物之一……不同的物種可以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社會特徵,從獨居到群居……一個人如何在需要作為一個整體行動的群體中保持個性?……貝蘭傑承擔了西西弗斯式的使命……我們可以透過反抗來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有意義,並創造一個我們可以依靠的生存目標”(第 95-98 頁)。“早期的英雄們認為他們在為比自己更偉大的東西而奮鬥,希望支撐著他們在追求中。在尤涅斯庫的宇宙中,貝蘭傑拒絕投降沒有賦予任何宇宙或宗教意義”(阿博特,1989 年,第 165-166 頁)。“因此,犀牛成為對社會中的人類的令人不寒而慄的刻畫,任何社會,都被他的同類排斥,原因是他無法完全理解”(帕塞爾,1986c 年,第 1002 頁)。“在戲劇中,就像在小說中一樣,……衰弱的標誌是目前不願意(我認為,源於無能為力)創造角色。某種反人道主義與這種品質有關,即使在像犀牛那樣明確表達了對人類異化的擔憂的作品中,人們也能感受到這種品質的存在”(加斯納,1968 年,第 502 頁)。
“尤涅斯庫是一個了不起的模仿者,一個憤世嫉俗的懷疑論者,一個幾乎不可抑制的快樂虛無主義者;他在喜劇和悲劇中都一樣有效。他能夠挑戰反思,同時激怒感官或用他的滑稽表演來撓我們的癢處,並能夠在幾乎同一口氣中讓我們沮喪和娛樂”(加斯納,1960 年,第 261 頁)。“當他的角色體驗到輕盈、快樂、短暫時,它總是孤獨的情感。他們無法從與他人的共同歡樂中獲得快樂。事實上,幾乎總是社會存在的壓力和侵入性破壞了他們內心的幸福感”(布拉德比,1991 年,第 81 頁)。
"禿頭歌劇"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50 年代。地點:英國倫敦。
文字位於 https://macaulay.cuny.edu/eportfolios/smaldone2011/course-readings/
史密斯太太喋喋不休地談論家事,史密斯先生則嘖嘖稱奇。他從報紙上讀到鮑比·沃森去世的訊息。史密斯太太特別提到,她現在想到的是鮑比·沃森的妻子,鮑比·沃森。史密斯夫婦建議,鮑比和鮑比·沃森的孩子,分別由鮑比和鮑比·沃森的叔叔和嬸嬸照顧,這樣寡婦就可以再婚。“她有中意的人嗎?”史密斯太太問道。“是的,鮑比·沃森的堂兄。”史密斯先生肯定地說。“誰?鮑比·沃森?”他的妻子問道。“你指的是哪一個鮑比·沃森?”他反問道。“老鮑比·沃森的兒子,也是已故鮑比·沃森的另一個叔叔。”她回答。“不,不是那個。”他說。“鮑比·沃森,老鮑比·沃森的兒子,鮑比·沃森的姑姑的兒子。”在確定了這件事後,他們邀請的客人來了,一對彼此不認識的男女。在交談中,兩位客人驚訝地發現他們有很多共同點,直到意識到他們是夫妻。門鈴響了。史密斯太太起身去看看是誰,但沒有人。同樣的情況又發生了兩次,直到憤怒的史密斯先生起身看到一個消防員站在門口,他已經在那裡等了45分鐘。當被問及如何解釋時,消防員透露,前兩次鈴聲響起時他什麼也沒看到,但第三次是他自己按響鈴聲,然後躲起來,當作一個玩笑。他背誦了一些實驗性的寓言,例如狗和公牛:‘另一頭公牛問另一條狗:你為什麼不吞下你的鼻子?—對不起,狗回答,因為我認為自己是一頭大象。’ 他們的談話被史密斯夫婦的女傭瑪麗打斷,她想表達自己的軼事,但這兩對夫婦對一個區區女僕這樣做感到反感。消防員認出瑪麗是他失散多年的戀人,一個“熄滅了我初次火焰”的女人,他說,瑪麗也同意是“他那小小的噴泉”。當她試圖背誦一首名為“火”的詩時,史密斯夫婦將她趕出了房間。在離開之前,消防員問起了那個禿頭的歌劇女主角。“她像往常一樣把自己遮蓋起來。”史密斯太太回答。消防員離開後,這對夫婦越來越難以理解對方,然後迷茫地四處奔走。
"犀牛"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50年代。地點:法國巴黎。
文字連結:https://archive.org/details/in.ernet.dli.2015.167320 https://archive.org/details/in.ernet.dli.2015.58383
約翰責怪他的朋友貝蘭熱過度飲酒和生活無序。突然,他們之間的談話被一隻在街上奔跑的犀牛打斷了。他們討論了這隻動物可能來自哪裡,但每個建議都比另一個更不可信。貝蘭熱的同事黛西過來談論同樣的話題。又一次,談話被一隻犀牛打斷了,這次它朝著相反的方向奔跑。一位家庭主婦過來抱怨犀牛壓死了她的貓。約翰、貝蘭熱和黛西討論了它是否是同一只犀牛還是不同的犀牛。一名雜貨商認為是同一只,但約翰不同意,解釋說前一隻有兩根角,因此是亞洲犀牛,而第二隻只有一根角,因此是非洲犀牛。考慮到它們奔跑的速度,貝蘭熱質疑他的朋友是否能可靠地數出角的數量。“此外,它身上沾滿了灰塵。”他補充道。在他看來,約翰是一個自命不凡的學究。約翰感到被冒犯了。一位老人插話詢問,那隻獨角犀牛真的是非洲的嗎?約翰和貝蘭熱就這個問題也發生了爭吵。根據黛西的說法,兩個人都錯了。“亞洲犀牛隻有一根角,非洲犀牛有兩根角,反之亦然。”雜貨商斷言。約翰憤怒地離開後,貝蘭熱對自己的態度以及他朋友的態度產生了疑慮。“最小的異議都會讓他怒火中燒。”貝蘭熱宣稱。一位邏輯學家過來表示,即使第一隻犀牛有兩根角,第二隻只有一根角,也仍然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兩隻犀牛是不同的,因為第一隻犀牛可能失去了一根角。在貝蘭熱工作的辦公室裡,關於犀牛是否存在有不同的意見。他的同事波塔德認為它們是虛構的,這種觀點冒犯了貝蘭熱和黛西。相反,另一位辦公室職員杜達德,愛著黛西,相信她的目擊證詞。“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看到了多少。”波塔德談到貝蘭熱時說道。在街上看到一隻犀牛後,另一位辦公室職員,比夫斯泰克夫人驚慌失措地衝了進來。一隻犀牛破壞了辦公樓的樓梯,導致員工無法出去。然而,波塔德繼續否認它們的存在,直到他親眼看到一隻犀牛。比夫斯泰克夫人認出門口的一隻犀牛是她的丈夫。貝蘭熱看到了一隻長著兩根角的動物,但仍然不確定它是亞洲的還是非洲的(不知道如果它是白色或黑色,那麼它就是非洲的)。與此同時,部門主管巴特弗萊鼓勵所有員工返回工作崗位,而黛西則打電話求助。比夫斯泰克夫人抓住機會,從高層直接跳到犀牛背上,與她的犀牛丈夫一起逃跑。波塔德假裝知道犀牛出現背後的原因,但不願意在此時透露。在緊急情況下,消防員趕到,將員工從大樓中帶出來。貝蘭熱對自己和朋友的爭吵感到不安,於是去約翰家道歉,但當他看到自己的朋友在他眼前變成犀牛時,他感到很害怕。巴特弗萊和杜達德也隨著人群的增長而遵循同樣的模式,黛西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廣播中聽到他們的聲音後。貝蘭熱不惜一切代價抵制這種轉變,他抵抗了變成其中之一的誘惑。
塞繆爾·貝克特
[edit | edit source]
塞繆爾·貝克特 (1906-1989) 繼續或完善了荒誕劇,有人會說,用 "等待戈多" (1952)、"終局" (1957) 和 "快樂的日子" (1961)。
"Waiting for Godot" “marked a clear break with the dramaturgy of the 1940s and...established a new frame of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theatre...Where ‘Waiting for Godot’ seemed initially incomprehensible to its first...audiences...its meanings are now self-evident” (Innes, 2002 p 307). “Who...is the unseen Godot? To some, he is death, to others, life, to a few, nothing...one could probably settle on Godot as standing for God...His absence does not signify negation...but...infinite possibility” (Bennett, 2011 pp 27-43). “Vladimir and Estragon...are clearly derived from the pairs of cross-talk comedians of the music hall...Vladimir remembers past events, Estragon tends to forget them as soon they have happened. Estragon likes to tell funny stories, Vladimir is upset by them. It is mainly Vladimir who voices the hope that Godot will come and that his coming will change their situation, while Estragon remains skeptical throughout” (Esslin, 1974 pp 26-27). “Vladimir thinks more, he is more cultured, his anguish is more intellectualized, he is more hesitant and demanding in his choice of words. Estragon is more spontaneous and more lethargic, he is more childish, he sulks more, he is more eager for protection, he is more egoistical and more obstinate, he holds to his own vocabulary and refuses Vladimir’s nuances. Vladimir is more restless, more active, Estragon more inert. Vladimir has the responsibility: he is in charge of the carrots, radishes, and turnips that constitute their meals. Estragon is more the victim: he is kicked by Lucky. While Vladimir tries to make conversation with Pozzo and to seem well-bred, Estragon listens only because he is threatened or ordered to; otherwise, he independently follows the flow of his own thoughts” (Guicharnaud, 1967 p 236). "Didi is the contemplative, the listener, the seeker, the one expecting messages, the ascetic, the one who suppresses his physical side, while Gogo is the active, the non-reflective, the one who tries to wipe the tears from the eyes of sufferers, who must eat when he is hungry, and who bellows when he is hurt. Neither can do without the other" (Baxter, 1965 pp 10-11). “Estragon, who's nickname is Gogo, is of the earth. His name is French for ‘tarragon’, an aromatic herb used as a seasoning in pickling. His obsession with his ill-fitting boots that cause him pain indicates that he is close to or of the earth. Gogo also goes and comes. He is the wanderer who always stumbles back to his companion Didi. He can be sarcastic and skeptical, but mostly he is resigned to an inevitably unhappy fate. Vladimir, whose nickname is Didi, continually looks and feels into his hat, seeking cooties or some other irritant, just as Gogo is tormented by his ill-fitting boot. He is more rational and less emotional than Gogo. Vladimir seems more in touch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nd more aware of his immediate world. He is better spoken than Gogo, and he sings in both acts. He is the leader of the pair, and, significantly, he is the one who most believes in Godot...Pozzo is a sadist, enjoying his power over his slave, Lucky, but he is also weary of the relationship. After all, a master is always tied to the slave who serves him…Pozzo stands for capitalism exploiting the worker, Lucky. The derby or bowler hat enforces this consideration. Pozzo is all materialism, concerned about his baggage, his comfort, his food, his pipe, and his watch. Lucky has nothing but his hat and his burdens. Lucky is a slavish masochist who does not want relief from his pain and thus attacks Estragon. The fact that he does not take advantage of Pozzo's blindness in act 2 to escape or kill his enslaver indicates that he has need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even the punishment. Lucky is not only a symbol of the exploited worker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but also the tormented intellectual made ineffectual by that society. It may be that Pozzo and Lucky are yin and yang in their relationship: part of one personality or entity” (Sternlicht, 2005 pp 54-55). “Serious subject matter is presented in music hall form...Much of the surface is taken up with farcical satire of conventional social behavior. Pozzo, for example, is unable to take a simple action like sitting down without an attendant barrage of ceremony, and the two tramps are always trying to strike up what will pass for a polite conversation, using catch-phrases like Vladimir’s: ‘this is not boring you, I hope?’” (Gascoigne, 1970 p 186). "What makes the play more than just a pastiche of clown and music hall comedian is partly the philosophical overtones and partly the self-conscious elements...The characters watch themselves act, reflect at the very moment of acting on the significance, or absence of significance, of those actions” (Bradby, 1991 p 59). “Beckett’s extraordinary feat of blending pathos and comedy is accomplished by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human characters who are, despite their bloviated portentousness and inane banter, filled with enormous charm. They are hilarious as they are tragic, exquisite amalgams of clownishness and grandeur. They can be pompous and stubborn, yet just as quickly brought down to earth with humility and despair” (Krasner, 2012 pp 343). According to Durán (2009), The play "reflects Albert Camus' 'The myth of Sisyphus' (1942)...For Camus, the absurd issues from the clash of two contradictory phenomena: rational man and an irrational world...It soon becomes clear that Vladimir and Estragon live in a world wholly devoid of reason. The characters engage in pointless acts, the dialogue abounds in non-sequiturs and contradictions, and memories are short. Characters often forget whom they know or what they know. In Beckett's play, things happen not according to any logic or order, but as a result of sheer fortuity...Vladimir and Estragon thus find themselves disoriented and alienated from the irrational world they inhabit...Consequently, the two characters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and energy devising ways to fill the emptiness of their mundane lives...Camus explains that one continues to live this type of absurd existence largely out of habit...But Camus warns that the protective walls of habit can unexpectedly fall away making one suddenly aware of life's absurdity...Thinking poses a danger because it can expose one to that 'suffering of being' provoked by a consciousness of the absurd...Suicide affords one means of escape...After learning from the young messenger that Godot will not come that day, Estragon gazes at the tree and laments... He asks Vladimir to remind him to bring a rope the next day and recalls a past attempt at suicide...The rejection of suicide still leaves the possibility of eliminating the other opposing term: an irrational world. Despite all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one may choose to view the world as truly rational. Camus calls this strategy 'the philosophical suicide'...By adopting systems of belief such as religion, philosophy, astrology, or what have you, one imposes a false logic and order on this world...Lacking the courage to commit physical suicide, Vladimir and Estragon find solace in philosophical suicide. They see their hope in the coming of a Godot, someone who will satisfy all their wants and needs...No matter what occurs, Vladimir and Estragon cling tenaciously to their hope in Godot's appearance...As a result, the two tramps end up doing nothing...Camus believes that an authentic response to the absurd resides in neither physical nor philosophical suicide...Rather than elude the absurd, one must not only accept but also sustain its truth, constantly confronting its reality through what Camus calls a metaphysical revolt...In the final pages of his essay, Camus illustrates his concept of 'revolted man' through the character of Sisyphus...[who] chooses instead to embrace his fate, fully conscious of all that that implies. [But the tramps] incarnate, in fact, the exact opposite of Sisyphus. Rather than embrace their reality, the two tramps use every means available to evade it" (pp 982-989). “Vladimir and Estragon play the game of waiting for an entity that they have invented to save them from the unknowable. They have even hired a boy/priest to reassure them at regular intervals that they are not waiting in vain. Meanwhile they eat, sleep (and have nightmares), engage in futile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 and otherwise parody human existence” (Wellwarth, 1986 p 71). "In Waiting for Godot, auditory and visual scenic means convey the tension between comedy and tragedy to the audience. Act Two ends in nearly an identical way to Act One. Estragon and Vladimir discuss suicide and separation. A tree, the only permanent prop in the play, has sprouted four or five leaves. However, what might signify the meaningful fullness of life the participation of humanity in a scheme of things larger than itself, a metaphysical reality capable of supporting the form of tragedy is reduced to mere occurrence" (Como, 1989, pp 68-69). Brater (2003) emphasized the movement of the play from the particular to the universal, as in Vladimir's following comments to his fellow tramp: 'let us do something while we have the chance. It is not every day that we are needed. Not indeed that we are personally needed. Others would meet the case equally well, if not better. To all mankind they were addressed, those cries for help still ringing in our ears! But at this place, at this moment of time, all mankind is us,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Let us make the most of it, before it is too late'" (p 145). “The clearest statement of Beckett’s belief in the uselessness of thought is in the tremendously effective scene of Lucky’s tirade in Waiting for Godot. Beckett here implies that it is only in modern times that man has become impotent in thought and action” (Wellwarth, 1971 p 46). Lucky’s tirade "is one magnificent moment when a bestially slave-driven underdog bursts into an incoherent speech which gives an extraordinary Joycean impression of overcharged meaning" (Williamson, 1956 pp 69-70). “We have no superficial allegories and personifications of abstractions, but characters who are both symbolic and real in a situation which is a metaphor of the human condition...This is the true metaphysical Pascalian and Kierkegardian absurdity and nonsense of life without God or purpose and it is something which is very remote from the dehumanized, incoherent world of Ionesco...The Pozzo-Lucky relationship is the mirror of human degradation and shallowness. Pozzo hides his insignificance and hollowness under a cloak of ritual gestures and ceremonies which are part of the social apparatus of power...Lucky is merely an object, a thing, and his life is reduced to mechanical reactions; he not only serves Pozzo, he has also to think for him; he is therefore materially and spiritually Pozzo’s slave and has no individual existence” (Chiari, 1965 pp 68-74). The tramps “appear as a social unit outside society...like prisoners free to amuse one another...It is as though they ad lib for their very lives...The play takes up themes of many kinds- religious, philosophical, psychological- without any of them to become the drama’s motif, and with a fierce comic opposition to their pretensions...Pozzo and Lucky are emissaries from the realm of time and from the life of society, with its institutionalized relationships, its comforts and delusions, above all its thirst for hierarchies...the principles of huma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delusory, ultimately disastrous, but maintained by them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lives...Whenever a character appears to be feeling some definite emotion or to have entered some decisive area of commitment, it is all undone by an opposite remark, a corrosive scornfulness, a physical jape” (Gilman, 1999 pp 242-250). “The word ‘divine’, used three times in the play, is spoken not by the seekers for Godot but by the slave commanded to ‘think’, the broken-down scholar, Lucky, in his wild meditation on the existence of ‘a personal God [including] referring to the ‘divine Miranda’, which points us to Shakespeare’s heroine in The Tempest, someone able to suffer ‘with those who for reasons unknown but time will tell are plunged in torment’. That she could so feel for total strangers understandably makes her ‘divine’ for the maltreated Lucky” (Worth, 2006 p 239). “Sober expression of misery is rare in this nearly wholly stichomythic play whose words are never allowed to inflate the period. The words remain simple, idiomatic, slangy” (Grossvogel, 1958 p 329).
“終局” “揭示了一種單一的基調和一種執著的目的,它令人敬畏和困惑……在“終局”中什麼都沒有發生,而那什麼正是重要的……苦澀很重要……被困的感覺很重要……哈姆的蔑視的強度很重要……哀歌般的氛圍很重要”(加斯納,1960 年第 256-258 頁)。“哈姆癱瘓了,再也站不起來了。他的僕人克洛夫無法坐下……一些巨大的災難,劇中人物認為自己是唯一的倖存者,殺死了所有生物……哈姆不修邊幅。克洛夫是秩序的狂熱者。哈姆的父母是怪異的感情上的白痴”(埃斯林,1974 年第 41 頁)。哈姆可能是錘子的縮寫,克洛夫可能反映了“clou”或釘子,從中可能得出奈爾(或釘子)和納格,來自德語翻譯“Nagel”(門德爾森,1977 年)。“納格和奈爾在他們的垃圾桶裡似乎是棋子;克洛夫,帶著他任意限制的動作(‘我不能坐’)和他的騎馬背景(‘你的巡邏呢?一直步行?’ ‘有時騎馬’)類似於騎士,他完美的立方體廚房(‘十英尺乘十英尺乘十英尺,很好的尺寸,很好的比例’)類似於棋盤上的一個方塊,被翻譯成三維。他來回移動,進入和走出它,來到哈姆的身邊,然後退卻。在終局結束時,棋子永遠保持靜止,克洛夫準備最後一次離開棋盤,現狀永遠受到透過窗戶看到的預期棋子的威脅,國王哈姆被遺棄在將軍狀態”(肯納,1961 年第 156-157 頁)。“不斷地提到遊戲、玩耍和戲劇的問題。哈姆在他第一個和最後一個獨白中用‘我— [他打哈欠]—要玩’ 開頭。對於克洛夫的‘有什麼能留我在此?’ 的問題,他回答‘對話’。哈姆在瞭解潛在的戲劇慣例和表演規則的情況下表演,‘既然我們就是這樣玩它的……我們就那樣玩它’。他教克洛夫:‘旁白,猴子!你以前從來沒有聽到過旁白嗎?[停頓] 我正在為我的最後一個獨白熱身’。他以戲劇性的方式開始和結束這部戲:在開頭,他讓幕布升起(‘他從臉上拿開手帕’)而在結尾,他讓它落下(‘他用手帕遮住臉’”(菲舍爾-利希特,2002 年,第 331 頁)。這種型別的自我意識是後現代風格的縮影,與以前時期缺乏自我意識形成對比。“哈姆關心一天中所有行動都要精確地進行,尤其是他對被置於房間的正中心的痴迷,呈現出一個試圖建立自己尊嚴和重要性的人的形狀,這種嘗試在他的環境中變得荒謬”(布拉德比,1991 年第 70 頁)。“熵與秩序之間的張力,力量耗盡與意志的堅定之間的張力,身體限制或無力與玩耍的能量之間的張力——僵局的戲劇張力——在“終局”中至關重要。這種張力在哈姆和克洛夫的關係中體現出來。最後快要死了……哈姆請求‘幾句話’……克洛夫的回答是關於藝術和秩序之美的願景……哈姆無法與之匹敵,他認輸了……克洛夫說他要離開牢房,離開結構,但我們看到他站在陰影中……他的眼睛一直盯著哈姆,直到最後……哈姆……以為自己獨自一人在結構中,獨自一人死去”(羅森,1983 年第 275-276 頁)。
“幸福的日子”是貝克特另一部關於人類悲慘命運的輓歌,人類被歸結為荒謬的僵局,從這個僵局,人類只能走向更糟糕的境地……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對人類韌性和堅定意志的讚頌,他們決心維護信仰或妄想的內心防線,抵禦失敗,不屈服於感傷,作家用持續的諷刺來抵禦這種感傷,因此,人類的英雄主義也顯得像是一種荒謬的自欺欺人能力”(加斯納,1968 年,第 504 頁)。“一方面,溫妮在她可怕而絕望的困境中如此樂觀,這很悲劇,另一方面,這也很有趣;從某種意義上說,她的樂觀是純粹的愚蠢,作者似乎對人類生活做出了一個非常悲觀的評價;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溫妮在面對死亡和虛無時的樂觀,是人類勇氣和高尚的體現,因此,這部戲劇提供了一種淨化,溫妮的生活確實充滿了幸福的日子,因為她拒絕被沮喪”(埃斯林,1974 年,第 59-60 頁)。“溫妮……被埋到腰部,後來被埋到脖子,保持著邏輯學家、語法學家的超然態度,超然於她的困境……儘管地球現在轉得如此緩慢,以至於在炎熱的白天,她感覺自己的身體受到自燃的威脅(“哦,我並不一定是指突然著火”),但她還是有些不安地考慮著,她刷梳的頭髮或頭髮是否應該被正確地稱為“它們”或“它”(“刷梳它?聽起來有點不妥”),她覺得弄清楚“豬”的正確定義比一天的痛苦更有意義”(肯納,1961 年,第 93-94 頁)。“溫妮最奇怪的特徵是她快樂……溫妮已經認命了,渴望吞噬任何舊的謊言,甚至是詩歌,利用任何“舊詞枕頭”來枕她的頭……溫妮是一個受害者,人類狀況的受害者……她擁有生存的常用慰藉:她給自己講故事,她有她的包,她有各種各樣的物品……然而,她對抗荒謬的最強大武器是她漠不關心”(科伊,1986 年 a,第 163-164 頁)。在溫妮的歌聲中,歡樂寡婦圓舞曲平淡無奇的歌詞,被它輕快的曲調和歌曲與殘暴地被禁錮的歌手之間的反差所提升,進入另一個維度,在那裡,舞蹈可能會永遠持續下去,就像婚禮當天的回憶和曾經說過的話語一樣”(沃思,2006 年,第 242 頁)。
“儘管貝克特的失敗戲劇充滿了智力遊戲和文字間的相互參照,但它依然是嚴謹的非概念性的。它的目的不是讓我們思考,而是讓我們感受,創造出能夠深入皮膚,產生強烈、錯位體驗的引人入勝的氛圍”(拉弗裡,2015 年,第 28 頁)。
"等待戈多"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50年代。地點:法國。
兩個流浪漢,弗拉基米爾和埃斯特拉貢,在一條鄉間小路上等待一個名叫戈多的人,這個人答應過會來,但還沒有到。在等待的過程中,這兩個朋友試圖娛樂自己。然而,時間過去了,戈多還是沒有出現。為什麼?他們是否記錯了約定日期?他們是否來對了地方?埃斯特拉貢餓了,但弗拉基米爾拿出一根胡蘿蔔,大部分都吃掉了。“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根胡蘿蔔,”他在幾乎持續不斷的無聊狀態中說道。他們的等待被波佐和拉奇的到來打斷,拉奇似乎是波佐的僕人,如果不是奴隸的話,就被一根繩子牽著,走在波佐的後面。這種關係似乎讓弗拉基米爾和埃斯特拉貢感到震驚,但他們並沒有干預。更糟糕的是,弗拉基米爾和埃斯特拉貢開始對那個顯然是啞巴的拉奇施加與他對主人所受的同樣可憎的待遇。但拉奇並不是啞巴。他最終爆發出一段沒有標點符號的獨白,其中很多部分是語無倫次的,沒有任何結果,之後他和波佐一起離開了。一個年輕的男孩突然出現,是戈多派來告訴他們,他明天會來。弗拉基米爾似乎曾有過類似的經歷,但男孩否認了。第二天,一切都和以前一樣,除了樹上長出了幾片葉子。類似的滑稽劇式的對話被重複了,卻毫無用處。儘管弗拉基米爾提到他們前一天在同一個地方等待,但埃斯特拉貢不記得了。波佐和拉奇走了進來,很快便摔倒了,但兩個流浪漢都沒有幫助他們,儘管弗拉基米爾說有必要這樣做,埃斯特拉貢也願意在得到錢的情況下幫忙。波佐現在失明瞭,拉奇啞巴了,雖然波佐不記得什麼時候發生的這種不幸。他們繼續上路。男孩回來了,留下了和前一天一樣的訊息,卻不記得自己前一天說過什麼。作為唯一一個似乎記得的人,弗拉基米爾的生存似乎更加徒勞。兩個朋友決定在樹上吊死自己。如果是這樣,他們會勃起。埃斯特拉貢解開腰帶,像滑稽劇一樣,褲子掉了下來。他們還沒來得及嘗試,腰帶就斷了。他們放棄了。他們決定離開,但沒有動。
"終局"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50年代。地點:法國。
文字地址:https://pdfcoffee.com/endgame-by-s-beckett-pdf-free.html https://edisciplinas.usp.br/pluginfile.php/3346220/mod_resource/content/1/ENDGAME%20BY%20SAMUEL%20BECKETT.pdf
漢姆從臉上取下一條血跡斑斑的手帕。他雙目失明,無法站立,由克洛夫服侍,克洛夫有視力,但無法坐下。在打哈欠的時候,漢姆問道:“我的痛苦比這更高尚嗎?”漢姆害怕克洛夫可能沒有讓他承受足夠的痛苦,但聽到保證說他承受了足夠多的痛苦後,他感到寬慰。漢姆的父親納格住在垃圾堆裡,要他的嬰兒粥。“該死的祖先!”漢姆憤怒地喊叫著。他命令克洛夫給他一塊餅乾。漢姆絕望地認為大自然已經遺忘了他們,但克洛夫糾正他說,不再有大自然了。納格抬起垃圾堆的蓋子,試圖親吻他隔壁垃圾桶裡的妻子內爾,但沒有成功。當納格嘲笑漢姆的痛苦時,內爾責備他。“沒有什麼比不幸更有趣了,我承認,但……”她說道,卻無法說完。突然,漢姆決定要被放在房間的正中央。克洛夫費了很大勁才終於滿足了他的願望。漢姆接下來要求他用望遠鏡向外看,但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一片灰色的景象。漢姆又有了另一個可怕的想法。“我們難道沒有開始變得有意義了嗎?”他大聲自問道。當一隻跳蚤困擾著克洛夫時,漢姆命令他立即殺死它。“人類可能會從那裡重新開始,”他警告道。他接下來要求一個導尿管來排出尿液,但克洛夫還沒來得及拿來,他就尿在了自己身上。然後他要求克洛夫擺好一隻懇求的黑玩具狗的正確位置。不久之後,內爾去世了,納格哭了起來。漢姆多次問克洛夫是否該吃止痛藥,最後發現沒有止痛藥。繼續下去已經毫無意義。克洛夫離開了。漢姆吹了吹口哨,但沒有人回應,他就扔掉了口哨,用一條血跡斑斑的手帕捂住臉。
"幸福的日子"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60 年代。地點:法國。
文字地址:https://archive.org/details/happy_days_a_play_by_samuel_beckett
溫妮直立地半埋在一個土堆裡。一個來自未知來源的鈴聲是她開始新一天的訊號,她從包裡拿出梳子、牙刷、牙膏、手帕、口紅、指甲銼、開胃藥、眼鏡和左輪手槍。拿出這些東西后,她親吻了左輪手槍。她的丈夫威利住在土堆後面的洞穴裡,閱讀報紙和明信片,並在陰莖上塗抹舒緩溶液。她能聽到他,但看不到他。她在陽傘下,以防陽光照射過度,繼續進行她每天的例行公事,例如在同一時間唱歌。當她喋喋不休時,威利似乎沒有在聽,所以她有時不得不打他來引起他的注意。來自未知來源的音樂聲響起,她欣喜若狂。威利沒有做出太多貢獻,但至少他設法為她定義了“豬”這個詞。天氣很熱。最終,陽傘因過度高溫而著火,但她仍然樂觀地認為,這一天可能會順利結束。在一天結束時,鈴聲再次響起,這時她把包裡的所有東西都放了回去,除了槍。溫妮對物質要求很少,感到很滿足。“這將是另一個幸福的日子,”她總結道。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同一個喚醒鈴聲響起,她現在被埋到脖子,無法再操作任何物品,但她仍然確信,這將是她的另一個幸福的日子。她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聽到威利的聲音了,但她相信他仍然能聽到她,或者,即使聽不到,他無論如何仍然在那裡。“哦,毫無疑問,你已經死了,和其他的人一樣,毫無疑問,你已經死了,或者你離開了,拋下了我,和其他的人一樣,這並不重要,你就在那裡,”她說。出乎意料的是,威利終於出現了,朝她走來,或者朝槍走來,但在到達槍之前,他從土堆上摔了下來。他設法喊出了她的名字,她欣喜若狂。“溫妮!哦,這是一個幸福的日子,這將是另一個幸福的日子!畢竟。到目前為止,”她為自己總結道。
費爾南多·阿拉巴爾
[edit | edit source]
荒誕戲劇的另一位倡導者是西班牙出生的費爾南多·阿勞巴爾 (1932-?),他以“汽車墳場”(1959 年),“格爾尼卡”(1959 年) 和“盛大儀式”(1963 年) 而聞名。與英國廚房水槽派一樣,荒誕派作家最好的作品似乎都出現在他們戲劇生涯的早期。他也是“恐慌劇”的倡導者,用阿勞巴爾自己的話說,將“機會、記憶和意外”融入其中,以破壞官方寫作(Drumm, 2009 p 437),“以潘為名,並以酒神支配為原則”(Farmer, 1971 p 155)。“荷馬讚歌第 19 首,題為‘致潘’,提供了對這位神的最完整描述,阿勞巴爾從這位神那裡得出了“恐慌”一詞。潘是牧羊人的神,住在高山上……[不像阿波羅的甜美音樂,潘演奏的是]“原始物質……用他粗陋的蘆笛演奏著野蠻的曲調”(Arata, 1982 pp 7-8)。
在“汽車墳場”中,“墳場成為文明崩潰的象徵,是科技社會道德毀滅的象徵”(Podol, 1978 p 46)。“這個微觀世界中這些人物用來應對日常生活無意義的中心視覺形象是墳場本身,那裡充滿了報廢的汽車,象徵著現代文明的破壞性”(Podol, 1988 p 134)。“原始的善良以及它引發的激情是《汽車墳場》的主題,在作品中,阿勞巴爾用極大的想象力,把舞臺上擠滿了悲慘而積極的性行為的社群,他們居住在墳場裡一堆堆報廢的汽車中。在他們可憐而滑稽的中間,出現了一個優秀的小號手,還有兩位其他音樂家。這個英雄當然是一個屠夫,每當他感到衝動時,但他被稱為埃瑪努,最終被背叛和毆打,最後被綁在腳踏車上抬過舞臺,一個女人用一塊布擦他的臉。耶穌激情的移置過於明顯,象徵的幼稚削弱了劇本的力量,否則劇本會充滿創造力和意義”(Guicharnaud, 1967 p 186)。“也許他更像是一個有遠見的作家,而不是一個劇作家,[阿勞巴爾]有忠於他所看到的優點:他那匿名語言 - 正確但沒有風格,與亞當諾夫非常相似 - 使他無法作弊。他看到了汽車墳場,它的角色、他們的動作和他們的形狀;但當他用埃瑪努-基督象徵擊打我們時,效果就被破壞了”(Guicharnaud, 1962 p 119)。“迴圈模式從劇本開場的對話中就建立起來了。阿勞巴爾把當代生活的縮影,汽車廢車場,擠滿了廢棄的汽車,每一輛都住著看不見的顧客。當客人在第一幕中安頓下來準備過夜時,他們像往常一樣被女僕迪拉擁抱,我們很快就知道警察“又回來了”,他們正在尋找三個音樂家,這些音樂家像往常一樣會逃跑……在對話中發現的迴圈結構被延續到劇本的非語言方面。不斷地穿過舞臺,賽道跑步者和警察與強盜的運動是空間辯證法的另一個組成部分。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一次未完成的朝聖,因為這個圓圈沒有中心,沒有解決方案,沒有最終目的地。跑步者拉斯卡和提奧西多正在進行一次空虛的遊歷,它沒有通往任何地方……兩種對立的力量相互追逐:一方面是純潔和無辜,另一方面是腐敗和妥協。後者,就像拉斯卡和提奧西多,毫無疑問地屈服於規章制度,屈服於三份一式填寫的表格,屈服於嚴格的訓練和紀律。他們致力於維護現狀。即使是住在廢車場裡的棄兒也屬於這個世界,模仿著它的儀式,這些儀式在米洛斯熱心的照料下變成了怪誕的模仿。他們與強者團結起來,反對埃瑪努的純潔。似乎在順從的保護下,被統治者和統治者之間終於達成了休戰……迪拉在這個世界中扮演著調解者的角色。只有她清醒;只有她既瞭解埃瑪努的純潔,也瞭解她生活的墮落。她也“想做好事”,渴望純潔,但她知道已經太晚了……她保護埃瑪努,把他藏起來,拒絕為了獎賞而背叛他。然而,她對他的理想主義和他的盲目感到厭煩”(Luce, 1974 pp 33-35)。“那些流浪者……都是成年的孩子,無辜的兇手、窺視者和展覽狂。他們喜歡撒尿和做愛。他們討厭警察,卻不斷被警察追捕……當我們第一次見到迪拉時,她像一位偉大的母親一樣四處走動,強迫所有住在這裡的人晚上睡覺。然後,她把自己交給了任何想要她的男人……迪拉冷嘲熱諷地提醒埃瑪努,在一個這樣的世界裡做好事只會惹麻煩……她是對的……當他在人群中給一些人餵了幾條沙丁魚和一些麵包時,其他人變得嫉妒了。最終,他的顛覆活動導致了警察的追捕,以及他被朋友之一的背叛……透過埃瑪努,阿勞巴爾……揭穿了慈善和愛的基本基督教倫理……他的善舉對他所在的社群幾乎沒有影響,我們假設,對他們沒有任何持久的影響”(Donahue, 1980 pp 12-15)。埃瑪努代表著以馬內利的縮寫形式,即耶穌基督。他的先例是相似的,出生在馬槽裡,木匠和瑪麗的兒子,用魚和麵包餵食人群,被一種食物記住,被一個吻背叛,並以一個類似十字架的位置暴露出來。“劇中的人物變成了現代的聖經人物……遵循中世紀神秘劇和奇蹟劇的傳統……拉斯卡和提奧西多……變成了會逮捕耶穌的羅馬士兵(警察),提奧西多也扮演了彼拉多的角色,模仿他洗手的那一刻,福德雷……扮演了彼得的角色,說出三次否認耶穌的話,迪拉……首先像瑪利亞·馬達拉,後來變成了維羅妮卡,為耶穌洗臉,託佩……扮演了猶大·伊斯加里奧的角色,米洛斯……最後變成了西蒙,為耶穌背十字架的古利奈人”(Arata, 1982 pp 33-34 and p 68)。“米洛斯通常控制著迪拉;他在幾個場合懲罰了她,一次是因為她沒有提供性恩惠,另一次則是非理性地懲罰她,因為她恰恰做了那樣的事。然而,迪拉在劇本中的另一個時刻,咄咄逼人地威脅著膽小的米洛斯,要懲罰他。戲劇的迴圈結構源於拉斯卡和提奧西多的身體運動。這兩個角色以尋求新的世界紀錄開始和結束作品,但角色顛倒了。他們的關係反映了雄心勃勃的母親的堅強意志,以及男性在將自己與女性比較時,為了應對自卑感,而需要在身體上表現自己的需要。拉斯卡和提奧西多也代表著國家的壓迫性。在劇本的結尾,他們侷限而窒息的路線的荒謬性得到了肯定,他們變成服務於體制的警察的可能性保持不變……埃瑪努犯了謀殺罪和其他社會不能接受的罪行。然而,他確信自己會被赦免,因為他記住了善良的意義……如果基督可以被認為是愛,那麼他和那種情感都被汽車墳場那個機械化、非人性化的世界所廢除了。墳場本身構成了一種中心、視覺上的文明崩潰象徵”(Podol, 1986a pp 125-126)。
在“格爾尼卡”中,“法恩丘和莉拉既是西班牙內戰和所有戰爭的無辜受害者,又是導致毀滅性爭吵的人類弱點和麻木不仁的代表……法恩丘不願努力去解救莉拉,他對她的戰爭性質的無知進行斥責,莉拉對法恩丘性無能的引用以及她對沉默的利用,在絕望的處境下既幽默又令人不安”(Podol, 1978 p 51)。“1937 年巴斯克精神之都遭到轟炸時,莉拉被困在廁所裡,這在令人毛骨悚然和滑稽之間製造了一種緊張感,這正是怪誕的特徵。她與丈夫法恩丘的對話,暗示了他的性無能,揭露了他們相互的自私和缺乏真正的同理心,這指責了他們,但並沒有減少他們困境和空襲本身的恐怖。作品中的惡棍是小說家和記者,他們對自己的國家和人民漠不關心,並試圖利用這種情況來謀取他們自己的職業利益……在最後,概括和悲觀情緒被氣球的象徵所抵消,氣球無法被剛殺害法恩丘和莉拉計程車兵擊落。在視覺上,阿勞巴爾利用垂直運動來表達希望和解放”(Podol, 1988 pp 134-135)。“當巴斯克人民的古都格爾尼卡在 1937 年 4 月 26 日被德國空軍摧毀時,指揮這次襲擊的沃爾夫拉姆·馮·里希特霍芬及其隨行人員正在附近的一座山上觀望。眾所周知,這次襲擊的一個潛在目的,以及德國在西班牙內戰中站在國民黨一方的參與,是測試新的戰爭技術。馮·里希特霍芬以及聚集在奧伊茲山的人們見證了第一次閃電戰式轟炸的實施,這種轟炸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納粹戰略的核心。從最初的可怕時刻起,格爾尼卡的毀滅就是一個戲劇化的事件,在這個事件中,大多數平民受害者都是不知情的演員……當記者出現時,“阿勞巴爾對那些會從對平民人口毀滅的藝術呈現中受益的人提出了明確的指控:文學風格取代了任何準確描述所發生事件的意圖;重點不再放在受苦的人民身上,而是放在假裝講述他們故事的聲音上”(Drumm, 2009 pp 427-436)。
在《盛大的儀式》中,主人公“鞭打玩偶並謀殺了一個小女孩,他被專制和馬基雅維利式的母親所維持在精神病狀態”(Guicharnaud,1967 年,第 185 頁)。主人公的名字是偉大情人的字謎,突出了怪誕變形的強烈意味。儘管有這些模仿的元素……這部戲劇也成功地捕捉到了主人公的極度痛苦……Cavanosa 患有由對母親形象的固著引起的複雜症,這使他無法在心理上整合自己的父母或發展獨立的個性和自我……Cavanosa 對 Sil 的令人髮指的對待實際上是對其日益增長的害怕意識到自己壓抑的慾望的反應。死亡、暴力和色情交織在一起;母親對兒子的亂倫渴望以希望被他殺死的方式出現,並有助於解釋 Cavanosa 自己扭曲的愛的感覺的本質,這在他對待玩偶和 Sil 的方式中得到了證明。身體折磨成為內心衝突的表現,而身體畸形則是精神痛苦的外化。當這些力量占主導地位時,戲劇的氣氛仍然沉浸在潛意識的世界中……Lys 出現了,她是 Sil 的另一個自我(由他們共同的名字互為迴文來證實);她覺得 Cavanosa 可愛迷人,因為她沒有接觸過其他男人……如果他的話透過暗示愛仍然只能作為以死亡告終的破壞性行為來引入一種模稜兩可的意味,他對 Lys 的溫柔親吻以及他夢囈般地和她說話的事實至少部分地證明了主人公從典型的吞噬母親的監禁影響中解放出來的希望感”(Podol,1978 年,第 65-66 頁)。“不承認道德標準,生活在自己的痴迷世界中,Cavanosa 每次進入公園的另一個世界時,都會遇到一種存在和行動的方式,這與他自身完全相反……Cavanosa 的所有行為都與人們的預期相反:愛只帶來他的輕蔑,任何對他表現出的愛意都會激怒他,任何對他提供的善意都會產生殘酷的反應……結果是一個角色不僅與其他人不同,而且意識到自己與眾不同,並且能夠以諷刺的距離觀察自己運作……與必須被告知什麼才能取悅 Cavanosa 的 Sil 不同,Lys 本能地知道……Lys 是早期的 Arrabal 劇本中常見的妓女女人孩子……[Cavanosa 和 Lys 的世界] 重合。她像 Cavanosa 在情感上與母親相連一樣,在身體上與母親相連;她做鞭子,他用它們;她畫玩偶,Cavanosa ‘愛’它們。Cavanosa 的母親是專制、虐待狂和典型的報復者。她對兒子的控制力正在慢慢減弱,她知道自己很快就會被 Cavanosa 在日常儀式中在公園裡遇到的其中一個女孩所取代……更重要的是,她知道她的兒子想殺了她……她知道她的兒子沒有力量殺死她,因此她非常勉強地控制著他……他對無能的恐懼部分地透過他與真人大小的玩偶的自慰活動得到緩解,而他的戀母情結焦慮部分地透過他在公園裡每天的追求和謀殺他遇到的一個女孩得到緩解。然而,Cavanosa 無法區分幻想和現實。實際上,他的幻想就是他的現實……直到他遇到了 Lys,她能夠參與他的幻想世界變成的現實。當然,Lys 只是他母親和玩偶的替代品。她讓他一勞永逸地將施加在他母親身上以及她反過來施加在他身上的關係外化”(Donahue,1980 年,第 17-21 頁)。
“將他的戲劇視為一個整體,我們可以透過提取 11 個主要特徵來對 Arrabal 宇宙進行分類:1. 一個半夢半神話的童真王國,有時幼稚;一種帶有孩子氣的玩樂的準天堂,在那裡孩子們淘氣的遊戲變成了戴著手銬和腳鐐的酷刑,甚至變成了不悔改的謀殺。2. 懷舊的、頭腦簡單的孩子氣與成人含糊不清的共存(一個對母親著迷的英雄,有厭惡女人的傾向,是這種雙重性質的典型代表)。3. 受害者面對折磨者的強迫性緊張,在神話中被戲劇化。4. 歡樂與恐懼的 rapprochement;同樣,怪誕的來回搖擺相反的情緒。5. 角色倍增或雌雄同體的角色。6. 極權主義隱喻:宗教裁判所、酷刑、絕望、暴力死亡、家庭成員之間的背叛。7. 倒置的基督教、神秘的象徵、褻瀆、色情聳人聽聞、怪異的儀式和儀式、狂野的色情和死亡的聯盟;虔誠和褻瀆動機的同時性。8. 幻覺中的幻覺的根本對比。9. 一種衝動、有時不連貫的風格;一種不均勻、奔流或野蠻的戲劇節奏,依賴於誇張的衝擊效果。10. 奇特的光學影像:矮人、巨人、駝背、巨大的氣球、機器人象棋手、鞭子、棺材、裸體和豐滿的屍體。11. 神話或隱喻的底層結構,將各種深奧的連貫模式相互連線”(White,1971 年,第 99 頁)。
“汽車公墓”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50年代。地點:法國。
文字在?
精力充沛的 Lasca 鼓勵精疲力盡的 Tiossido 在汽車墳場周圍慢跑,而一個穿著優雅的管家 Milos 則在住在舊車和廢棄汽車裡的人群中接聽第二天早上的早餐訂單。Lasca 還鼓勵他的妻子 Dila 親吻她的顧客。當他注意到她不願這樣做時,他用尺子打了她的每一隻手。當 Dila 朝著各個汽車乘客走去,準備提供性服務時,她遇到了 Emanou,他出生在馬槽裡,是木匠和一個名叫瑪麗的女人的兒子,他表示想與她同床共枕。“我們會轉身擁抱,像兩隻水下松鼠一樣,”他提議道。她接受了。第二天早上,Emanou 宣佈警察正在追捕他,因為他向窮人吹喇叭。Milos 看到 Dila 和一個男人在一起,勃然大怒,一把抓住她的頭髮,把她摔倒在地。在這一天,Lasca 和 Tiossido 的角色顛倒了,後者顯得更有活力。當 Emanou 的朋友 Topé 獲悉有人懸賞抓捕他時,他主動向 Lasca 和 Tiossido 親吻以出賣他。Emanou 無動於衷,從袋子裡拿出杏仁給 Topé 和 Dila。“如果警察抓住你,我們會以你的名義吃杏仁,”Dila 宣稱。當 Topé 親吻 Emanou 時,Lasca 和 Tiossido 立刻逮捕了他。Tiossido 在擺脫了這件事後,他們帶走了 Emanou 去鞭打他。他隨後被發現騎著一輛腳踏車,雙臂伸直,Dila 在他被帶走之前為他擦汗。第二天像往常一樣開始,Milos 和 Dila 在做著他們平常的家務。
“格爾尼卡”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30 年代。地點:西班牙格爾尼卡。
文字在?
在她去浴室的路上,一顆炸彈落在了大樓上,導致 Lira 被埋在瓦礫堆下,她的丈夫 Fanchou 無法把她救出來。他試圖鼓勵她,但一塊石頭掉下來傷了她的手臂,血流不止。一位作家和一位記者趕到那裡,調查格爾尼卡市各地轟炸造成的破壞。“加上我正在準備一部關於西班牙內戰的小說,甚至可能是一部電影,”這位作家宣稱。為了幫助妻子消磨時間,Fanchou 建議他給她講個故事。“你想聽那個關於在浴室裡被埋在瓦礫堆下的女人的故事嗎?”他問道。為了進一步取悅她,他像小丑一樣扮鬼臉,但 Lira 看不見他。她問附近的樹是否還完好無損;他回答說它完好無損。當他再次試圖營救她時,Fanchou 被一位軍官推倒,軍官阻撓了他的前進,然後一言不發地離開。Fanchou 無法再做任何事,於是給了她一個兒童氣球。一個女人和一個小女孩路過,前者推著一輛裝滿炸藥的手推車。氣球爆了,留下 Lira 抱怨她的狀況。軍官回來了,一邊吃著三明治一邊笑著,然後又走了。Fanchou 問 Lira 為什麼她從來沒有情人。“那會很時髦,”他斷言。“你從來沒想過我……當我當著朋友的面脫掉你的衣服時,你總是看起來很不高興。”當他建議她也許會因為牧師的出現而感到安慰時,她提醒他他們是無神論者。“誰,我們?”一個驚訝而害怕的 Fanchou 問道。女人和女孩又回來了,女人背上揹著各種各樣的武器。Fanchou 越來越沮喪,因為無法幫助他的妻子。“都是你的錯。你總是那麼著迷,在浴室裡讀書!”他脫口而出。女人和女孩第三次路過,推著一輛裝滿舊槍的手推車。現在 Fanchou 建議 Lira 可能會寫下她的遺囑。當他最後一次試圖救她時,他自己也被埋在地下,成為又一次轟炸的受害者。女人回來了,這次沒有小女孩,她帶著一口棺材。兩個氣球升向天空。軍官試圖把它們擊落,但沒有成功。Fanchou 和 Lira 的聲音從上面傳來,他們笑著。
“盛大的儀式”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60 年代。地點:法國。
文字在?
一個駝背的卡瓦諾薩人偶然在公共公園遇到了一個名叫西爾的女子。儘管他看起來很粗魯,但她還是同意和他在一起。她善良體貼的男朋友出現了,想要帶她走,但她更願意和這個粗魯的陌生人在一起,直到他叫他們倆都走。她走了,但後來帶著一根鞭子回來了。但他還是更加粗魯,踢了她,踐踏了她。然後他叫她在他的房子外等一個燈光訊號,在那裡她可以幫他移走他母親的屍體,他說他最近殺了她。然而,他的母親並沒有死。她懇求他遠離女人,因為女人只會偷他的錢。他坐在她膝蓋上,然後送給她一個小棺材,裡面放著一個娃娃。她稱他為怪物,他對此表示輕蔑。她接下來要求看他手中的刀,然後要求他用刀刺她,但他做不到。他們似乎有所和解。然後她在他的嘴上咬了一口,開始回憶往事。“還記得有一次,你不讓我沒有你陪同就出去,你就把你的手釘在了通往外面的門上,威脅說要那樣一直待著,直到我回來,”她提醒他。她注意到他的床單底下伸出了兩條腿,他解釋說那是他習慣撫摸的玩偶之一。母親離開後,西爾敲門進了房間。當卡瓦諾薩把她打扮成基督形象時,她同意為他而死。她也注意到床單底下伸出的腿。那不是玩偶,而是一個穿著和她一模一樣的死女人,她幫著把這個女人抬到屏風後面。西爾的男朋友再次出現,西爾向他解釋了她在房間裡做了些什麼,但她把屏風拉開,準備讓他看看屍體,卻發現屍體不見了。卡瓦諾薩突然出現,抓住男朋友,把他綁起來,威脅他,但最後還是放了他。母親回來了,在窗外看著警察帶走一具屍體,卡瓦諾薩解釋說那是他前天殺的。 “我告訴過你不要把她留在地窖裡,”她責怪他。卡瓦諾薩想讓西爾離開,但她堅持要留下來,直到他同意把她變成她母親的奴隸。第二天晚上,他遇到了另一個名叫莉絲的女人,她的性格和西爾很像。他也對她很粗魯,但她仍然想和他在一起,從裙子下面拿出一根鞭子給他。他決定從他的車裡拿出一個娃娃,和她一起離開。
讓-克勞德·布里斯維爾
[edit | edit source]在後荒誕主義戲劇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趨勢,包括歷史劇的迴歸,儘管在讓-克勞德·布里斯維爾 (1922-2014) 的《笛卡爾先生與帕斯卡爾先生的對話》(1647 年,兩名數學家和哲學家唯一一次會面的基礎) 中,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布里斯維爾還創作了兩部歷史劇:《晚餐》(1989 年),以 19 世紀政治家塔列朗與警察部長約瑟夫·傅歇之間的衝突為基礎;《侍從室》(1991 年),以瑪麗·杜德凡伯爵夫人與朱莉·德·萊斯皮納斯之間的關係為基礎。由於眼睛失明,伯爵夫人把她哥哥的私生女朱莉接到了她家,讓她當她的讀者。伯爵夫人的房子最初吸引了各種各樣的知識分子,直到她與朱莉接受的更自由的理念疏遠,而朱莉的侍從室引起了她保護者的嫉妒,迫使她離開。
《笛卡爾先生與帕斯卡爾先生的對話》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647 年。地點:法國巴黎。
文字在?
勒內·笛卡爾遇到了布萊茲·帕斯卡,這兩位數學家和哲學家對宗教特別感興趣。笛卡爾承認,到目前為止,他知道表達宗教觀點的風險,他一直“戴著面具前進”。與笛卡爾不同,儘管帕斯卡在數學方面取得了成就,但他開始對科學失去興趣,因為他正在尋找只有宗教信仰才能提供的確定性。帕斯卡對笛卡爾對數字的信仰感到憤怒。“一個基督徒能這樣推理嗎?”他反問,“難道你沒有看到理性會讓你不再需要上帝嗎?”笛卡爾否認了這一點。帕斯卡害怕上帝和他搖擺不定的缺乏信仰,他只希望為自己的救贖而工作,而笛卡爾對此充滿信心,同時也在研究科學問題。帕斯卡請他寫一封信來支援一位被耶穌會士錯誤指控的詹森派同仁,耶穌會士是當時的統治派別。笛卡爾拒絕了,因為他不想捲入不必要的宗教爭端。帕斯卡感到失望,指責他膽小,笛卡爾否認了這一點。另一個有爭議的話題是,薩布萊夫人在領聖餐的同一天晚上跳舞的決定,笛卡爾認為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帕斯卡卻對此感到震驚。帕斯卡進一步疏遠了他的同行哲學家,宣稱他歡迎磨難,因為肉體的痛苦“把我與基督聯絡在一起,”他說。笛卡爾對帕斯卡的禁慾感到沮喪,他講述了一個關於一個男人曾經救過他性命的故事,當時他被困在馬下面,很可能會凍死。那個男人,儘管他很慈善和善良,後來卻因為帕斯卡指責他信仰古怪而失去了他作為教士的職位,現在已經成了一個窮人:這是侍奉上帝嗎?笛卡爾最後認為,與地獄危險有關的事情是可辯論的,不可能有任何確定性。帕斯卡不同意。“我所追求的一切都超出了數學,”他斷言。
貝爾納-瑪麗·科爾特斯
[span>edit | edit source]在後現代時期,貝爾納-瑪麗·科爾特斯 (1948-1989) 的《重返沙漠》(1988 年) 也值得注意。
在《重返沙漠》中,“瑪蒂爾德的到來”擾亂了上層資產階級家庭中的所有事物:家庭內部的關係,亞德里安被保持在依賴狀態,而他的第二任妻子瑪特大部分時間都在喝酒,以及城外的人際關係,當地權力的俱樂部式聯絡將被打破。瑪蒂爾德部分出於純粹的固執,部分是因為她想重新獲得自己的一部分遺產,部分是因為她對第一任妻子瑪麗的死感到真正的沮喪,才引發了這場革命……瑪蒂爾德和亞德里安只能透過以物易物來相互聯絡,他們的孩子也像他們從父親那裡繼承的房子和工廠一樣,變成了商品”(布拉德比,1991 年,第 276-277 頁)。“暴力在每個場景中都潛伏著,從一開始瑪蒂爾德·瑟佩努瓦茲從阿爾及利亞回到她的祖傳家園,就無法和她的尊敬的資產階級兄弟亞德里安打招呼,而不互相辱罵。這個場景很有趣,因為亞德里安對中產階級尊嚴的虛假主張與他和姐姐之間實際上爆發的惡性狗咬架之間存在著諷刺的距離。這出戲中的暴力始終以諷刺的視角呈現。在戲的結尾,城裡的領導人(包括亞德里安)參與了一個成功的陰謀,在阿拉伯咖啡館裡放置炸彈。當炸彈爆炸時,亞德里安自己的兒子正在裡面尋找性冒險,當他渾身是血地回家面對他的父親時,亞德里安所能做的就是因為他不經允許離開家而打他”(布拉德比,1994 年,第 377-378 頁)。
“流亡者、外國人、局外人是在科爾特斯的戲劇景觀中生活著的[陌生人]。他那麼多角色可以說是四處逃竄,離開了祖國,來到一個他們的差異既明顯又清晰的國家。瑪蒂爾德在《重返沙漠》中質疑她的祖國。“我屬於哪個國家?”她問道。“也許你的家是你不在的地方?”……瑪蒂爾德註定要在一片她徘徊在外國人與本地人之間的景觀中游蕩。她最初以從阿爾及利亞不斷升級的衝突中逃出來的難民身份出現;15 年前,她離開梅斯,因為她被她的哥哥和他的朋友們公開羞辱;在劇本的結尾,她再次離開梅斯,帶著她爭吵不休的哥哥一起離開……對於馬修來說……家庭僅僅是關於遺產;強迫性的結構,在那裡厭女症從父親傳給兒子,孩子在“踢打和明智的訓誡”中長大,父親永遠被困在破壞性的青春期,一生都在和學校的朋友們沉迷於陰謀遊戲……在科爾特斯創造的世界裡,男子氣概被揭露、傷害、陷入困境,受到威脅。在《重返沙漠》中,它是透過亞德里安的印象派兒子表達的,即“打別人的臉……一起喝酒和打架的夥伴……要殺要征服的敵人。”它的運作方式被揭露和嘲弄,就像第九幕中城鎮官員(由警察局長、律師、部門長官和亞德里安代表)在密室裡策劃反對那些質疑他們過度的行為”(德爾加多,2011 年,第 28-31 頁)。
“科爾特斯的戲劇與當代戲劇寫作中以敘事驅動的傳統相去甚遠。他角色的行為總是令人驚訝,抵制心理因果關係的運作,而心理因果關係是許多現實主義戲劇的核心。科爾特斯的戲劇頌揚不可預測性和未言明的部分;他們對與方法演技通常相關的對角色的現實主義描寫有一種反感”(德爾加多和布拉德比,2015 年,第 141 頁)。
《重返沙漠》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60 年代。地點:法國。
文字在?
在阿爾及利亞缺席十五年後,瑪蒂爾達帶著她的女兒法蒂瑪和兒子愛德華回到了法國,住進了她哥哥阿德里安留下的房子。阿德里安以為她只是短暫地回來,並非如此,正如她從一開始就說明的。她打算住在屬於她的房子裡,就像工廠屬於他一樣,這是他們父母去世時決定的。阿德里安很不高興,因為他負責對房子進行了改進,所以某種程度上也屬於他,但仍然被迫接受。當他的兒子馬修堅持要繼續擁有自己的房間,而不是和愛德華合住時,他打了馬修的臉。法蒂瑪向她的母親承認她在花園裡遇到了一個人,但當被問到是誰時,她拒絕說出。在花園裡,阿德里安發現馬修試圖離開家族領地,加入法國軍隊參加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1954-1962)。“我不想繼承,”沮喪的馬修宣稱,“我想在說出優美的語句時死去。”阿德里安阻止了他。看到一位名叫普蘭特斯的警官出現在房子裡,愛德華跳到他身上並把他制服了。這個困惑的男人問瑪蒂爾達這樣做的意義。她回答說,十五年前,這個人是她被流放的罪魁禍首之一,他指責她未婚生子,有傷風化。為了羞辱他,她剪掉了他的頭髮。看到他這樣暴露無遺,阿德里安建議,被羞辱的警官可能會報復,跟蹤法蒂瑪並把她關起來,說她瘋了,更何況她還假裝看到了他已故妻子的幽靈瑪麗。阿德里安和瑪蒂爾達因為他們各自的需要而發生爭吵,涉及多個話題。阿德里安尤其擔心愛德華如何鼓勵馬修去阿拉伯咖啡館跟著他。阿德里安打了瑪蒂爾達,瑪蒂爾達還擊。他們被愛德華和一個僕人阿齊茲分開。在花園裡,馬修試圖和法蒂瑪發生性關係,但被她拒絕了。瑪蒂爾達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她鼓勵馬修繼續與她的兩個孩子保持友好關係。一個心煩意亂的法蒂瑪指著一個看起來像瑪麗鬼魂的東西,但她母親什麼也沒看到。晚上,瑪蒂爾達和她的女兒在床上,她告訴女兒,她覺得在哥哥家裡有危險。她特別想知道瑪麗是怎麼死的。阿德里安進來告訴他們,馬修已經參軍了。他對他兒子能否活著從戰爭中回來沒有信心。當法蒂瑪表達了她想回到阿爾及利亞的願望時,瑪蒂爾達沒有回答。阿德里安深夜與普蘭特斯和律師波尼會面,等待他們炸燬阿拉伯咖啡館的炸彈的訊息。令他們驚恐的是,爆炸炸死了馬修和阿齊茲。阿德里安和瑪蒂爾達決定搬到阿爾及利亞,遠離這棟像沙漠一樣的房子。
雅絲敏娜·雷扎
[edit | edit source]
雅絲敏娜·雷扎(1959-?)仍然延續著荒誕主義傳統的風格,創作了“藝術”(1994)。“在某種程度上,這部戲是對現代藝術市場的諷刺,[另一方面]僅僅是探索友誼的考驗和磨難的藉口”(格林,2020年,第266頁)。
“雷紮在緊張、巧妙的結構和經常令人捧腹的場景中探究了藝術和感情的曖昧性......藝術作品是否有內在價值,或者價值是由市場、時代還是觀眾的突發奇想創造的?是否有無私的友誼?...雷扎用外科醫生的精準度來衡量她角色的氣質,劇本中不斷變化的憤怒、怨恨和同情的潮流在一場基本上是一場長篇討論的戲劇中創造了驚人的懸念。對話具有光學錯覺的悖論般的多功能性:塞爾吉、馬克和伊萬透過批評藝術來批評對方,每個人在攻擊對方時都會出賣自己。他們對文字和概念的爭論(是畫中的白色,還是白色的概念,是如此令人不安?) 可以讓他們加入解構主義者的會議”(溫,1998年,第2頁)。
“塞爾吉在馬克認為毫無價值的東西中看到了價值。而這種威脅破壞了他們的友誼......西方思想中最早對友誼的概念之一是亞里士多德關於他所稱的性格友誼或品格友誼的概念。這不是唯一存在的友誼型別——還有基於權宜之計等因素的友誼——但是,對於亞里士多德來說,性格友誼是最高階的友誼。這是存在於平等者之間,具有相同美德和卓越的人之間的友誼......亞里士多德認為,如果沒有朋友,沒有與我們平等的朋友,我們就無法客觀地評估我們自己的品質,也無法客觀地衡量我們是否具有美德或卓越。真正的自我認知需要一個外部視角來驗證它......現在,如果我們假設馬克和塞爾吉之間的友誼是這種型別,那麼就更容易理解馬克的激烈反應。從馬克的角度來看,塞爾吉對這幅畫的難以理解的欣賞意味著塞爾吉和馬克不是彼此的化身,這當然威脅著馬克,然後也威脅著塞爾吉對自己身份的認識......如果馬克和塞爾吉要維持他們的友誼,他們必須以某種方式重新建立共同的感知能力。馬克必須在塞爾吉的畫作中看到某種價值。當然,這發生了,儘管經過了一系列非常奇怪的事件......比喻地說,友誼促使馬克以新的眼光看待事物,在塞爾吉看到的地方找到價值,儘管不是以塞爾吉的方式,但這使得他們的友誼得以恢復,強調了藝術不僅可以確認友誼的存在,而且還有可能擴大友誼的卓越性,在這種情況下,是另一個自我的感知能力的卓越性”(卡羅爾,2002年,第200-206頁)。雖然馬克對這幅畫的新看法可能是真誠的,但他的新觀點也可以被解釋為“放棄對權力的渴望”來確保友誼(卡沃夫斯基,2009年,第78頁)。
“皮膚科醫生塞爾吉懷有藝術和智力方面的野心;航空工程師馬克更腳踏實地,發現這幅畫的購買,他明確地稱之為‘那塊狗屎’,很可笑。這兩個男人,每個人都在他們選擇的職業中獲得了成功,把第三個角色伊萬拉進了他們的爭論。伊萬賣文具,而且是一個相當笨拙的拖延者。顯然,這出戲的成功並不完全取決於它的情節,以及它提出的各種問題:友誼是否能夠經受住個人固執或社會分化的考驗;安特里奧斯是否可以被歸類為‘藝術’作品;這些‘單身漢’(一個是離婚的,一個是婚姻出現問題,另一個即將結婚——他的婚禮在戲劇進行期間在幕後舉行)是否能夠建立持久的關係。這出戲也不僅僅是其組成主題的總和,儘管這些主題對大西洋兩岸的觀眾來說都很熟悉:友誼的脆弱性,勢利,金錢,攀附權貴,孤獨,追求幸福,以及現代藝術的煽動性作用”(雅克馬爾,2013年,第234頁)。
這部戲“圍繞現代男性友誼的權力動態和情感扭曲的揭示而構建。隨著情節的發展,所有角色都嚴厲地批評了對方的情侶、事業和家庭缺陷。貫穿始終,這場戰鬥都時刻關注著這幅畫,直到塞爾吉邀請馬克用伊萬的筆之一去毀壞它。他們的關係,‘被言語和行為摧毀’,在塞爾吉所說的‘試用期’的基礎上重新開始——戲劇以馬克重新審視這幅畫,不再看到一片白色,而是看到‘一個穿過空間然後消失的人’而結束。這部戲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藝術的分裂力和調和力的悖論:透過對這幅畫的意見分歧,這些男人解構瞭然後重建了他們的關係,並以尖刻的智慧,以及在某一點上的身體和言語暴力”(蓋爾,2015年,第197-198頁)。
"藝術"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90年代。地點:法國盧瓦雷省。
文字在 https://pdfcoffee.com/art-yasmina-rezapdf-pdf-free.html http://pvp.org/Play%20Reading/ART%20by%20Yasmina%20Reza.pdf https://kupdf.net/download/art-the-play-yasmina-reza-english-pdf_59f0c2bbe2b6f598324f005f_pdf
塞爾日買了一幅安特里奧斯創作的昂貴畫作,畫作以白色背景上白色的線條構成。他的朋友馬克對塞爾日缺乏判斷力感到非常沮喪。為了緩和氣氛,馬克笑了,但塞爾日沒有。當馬克向他的另一個朋友伊萬宣佈了這筆購買時,伊萬並沒有那麼生氣。伊萬甚至對塞爾日說他喜歡這幅畫。塞爾日伴隨著伊萬開懷大笑。塞爾日告訴伊萬,馬克的笑聲是“諷刺的,沒有魅力”。當伊萬向馬克報告他們的談話時,馬克明確表示塞爾日只是為了取悅他而笑,而不是出於正確的理由,因為這幅畫很荒謬。塞爾日向馬克報告伊萬喜歡這幅畫。馬克報告說他有點改變了主意,問自己:“屈服於這毫無邏輯的購買,難道不是一種高度詩意的姿態嗎?”伊萬即將結婚,但與他的女朋友在婚禮邀請卡上發生了衝突。她希望她的繼母被列入邀請卡,但由於伊萬討厭自己的繼母,他拒絕讓她被列入。馬克和塞爾日一致認為他應該取消婚禮。但伊萬說他不能,因為他的老闆是女方叔叔。馬克對伊萬的態度感到惱火,“因為他是一個小妓女,”他說,“卑躬屈膝,被金錢愚弄,被他認為是文化的東西蒙蔽了,我絕對要嘔吐的那種文化。”這時,塞爾日挑戰馬克。“你有什麼資格制定法律?”他咄咄逼人地問道。另一方面,馬克無法接受塞爾日喜歡他購買的畫作,而塞爾日則憤慨於馬克從不被他自己的意見所傷。塞爾日明確表示,他從未對馬克的女朋友說過負面評價。當馬克堅持要求他的朋友改變對他女朋友的看法時,他拒絕了。他們發生了爭執。在爭鬥中,伊萬不慎被打中了耳朵。他們停下來照顧他。最後,馬克揭示了他對這筆購買如此生氣的主要原因,因為他不能再以塞爾日的導師的身份來代表自己,用塞爾日的意見來衡量所有事物。為了證明他認為友誼比畫作更重要,塞爾日允許馬克用記號筆毀壞這幅畫,這讓伊萬感到震驚。馬克的渲染改變了他對這幅畫的看法。他現在在這抽象的藝術作品中看到了價值,儘管與塞爾日的觀點不同,但它使他們更加親近。塞爾日和馬克能夠修復損壞。當被問及他是否認為可能損壞的畫作可以修復時,馬克承認他並不認為可以修復。塞爾日撒謊說他也不認為可以修復。
讓-瑪麗·貝塞
[edit | edit source]
讓-瑪麗·貝塞(1959-?)創作的《精英學校》(1995 年)以更傳統的現實主義風格撰寫,講述了發生在知名商學院學生之間互動的故事。
"精英學校"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90 年代。地點:法國巴黎。
文字在?
深夜,阿涅斯為自己準備茶水,保羅加入了她。她懷疑伯納德、路易-阿諾德和維厄斯,保羅的室友,密謀在週末離開公寓,以便保羅能夠把她弄到床上。特別是,她猜測是路易-阿諾德建議保羅給她打電話。她提議一個交易:他們兩個人中誰先能勾引路易-阿諾德?如果她贏了,她和保羅將在他們自己的公寓裡住在一起;如果他贏了,她會離開他。後來,當阿涅斯和她的朋友埃梅琳等待男學生到來時,她們爭論著關於一起謀殺案的當前事件的解釋。埃梅琳離開時,伯納德提著一個沉重的包裹走了進來,解釋說路易-阿諾德落後是因為他在慢跑。令她們驚恐的是,路易-阿諾德帶著沾滿鮮血的側面走了進來。保羅加入他們兩人,幫助他們的朋友前往醫院。當伯納德和保羅學習時,前者無法集中注意力,離開了房間,因為後者只能哲學地思考發生在路易-阿諾德身上的事情。當後者穿著浴袍以發燒的狀態進入時,他也把保羅的思想斥為毫無新意。儘管如此,路易-阿諾德還是試圖幫助保羅完成學業。“真正能幫助我的是,”保羅說,“你處理這個案子,然後把我的名字寫上去,”對他朋友來說,這是一個令人費解的想法。凌晨 3 點,路易-阿諾德驚訝地看到阿涅斯走進他們的公寓,門被粗心地留著沒有鎖。阿涅斯提醒路易-阿諾德,他在醫院床上向她表達了溫柔的感情,而且是她,而不是他的朋友埃梅琳,去看望了他在醫院。當他們即將接吻時,埃梅琳從隔壁房間走了進來,嚇了一跳,她獨自睡在那裡,暫時代替了缺席的室友維厄斯。“我以為我們之間有一種親密的關係,”埃梅琳宣稱。“這並不賦予你製造場景的權利,”他回答。“性會捆綁,但不會固定,”阿涅斯宣稱。“我不跟你說話,”埃梅琳反駁道,然後在看到路易-阿諾德對繼續討論不感興趣時離開了。他離開了,然後又回來了,帶了一些錢,這樣阿涅斯就可以回家了,但她拒絕了。他撕掉了鈔票,扔在地板上。她撿了起來。當伯納德回到公寓拿遺忘的講義時,他發現有一個陌生人梅西爾,保羅的明顯床伴。當梅西爾離開去他們的公寓洗澡時,路易-阿諾德問保羅是否會加入阿涅斯去她學校參加週六晚上的聚會,因為他已經收到了邀請,但保羅不確定自己是否也被邀請了。路易-阿諾德突然退縮,並舉起椅子自衛,因為他看到梅西爾從浴室裡出來,因為梅西爾就是刺傷他的人,現在正迅速消失。後來,埃梅琳告訴保羅,路易-阿諾德將離開他的公寓,搬到其他地方住。當路易-阿諾德出現要搬走他的東西時,保羅諷刺地列舉了他未來商業生涯的優勢。路易-阿諾德沒有回應,而是和埃梅琳一起前往她的公寓。阿涅斯告訴保羅,她差點同意和路易-阿諾德睡覺;反過來,保羅告訴阿涅斯,他自己成功地和路易-阿諾德睡了。她認為他可能在撒謊,但無論如何都離開了。
吉爾達·布林代
[edit | edit source]吉爾達·布林代(1947-?)仍然以現實主義風格創作了《加油站》(1985 年)。布林代還創作了《月球的吐口水》(1986 年)。就像比漢的《人質》一樣,故事發生在一個妓院酒吧裡,那裡有一個保守的老闆、一名士兵和兩個同性戀。皮條客雷格洛威脅要把他的妓女,姓公主,送到更糟糕的地方,因此她試圖透過割腕自殺。一個擔心錯過火車船班次,無法與他的小隊一起前往海外計程車兵,一個失敗的搖滾藝術家香蕉,以一種超然的方式評論著行動,一個富有而瘋狂的麻煩製造者,打嗝,他挑戰著所有人,以及一個受到另一個皮條客保護的妓女,帕基塔,構成了這個令人不快的群體的一部分。與 20 世紀後期普遍存在的以非現實主義戲劇結構呈現現實主義對話的趨勢不同,例如,角色直接與觀眾對話,布林代以現實主義戲劇結構呈現現實主義對話。
“加油站”
[edit | edit source]
時間:1980 年代。地點:法國機場附近。
文字在?
在一條最近被封鎖的道路上的加油站,一位名叫 Samson 的修理工正在修理一輛標緻汽車。與此同時,Theresa 的智障兒子 Tut-Tut 正在角落裡小便。Theresa 是一位老師,是 Madeleine 三個女兒中最年長的一個。不幸的是,尿液濺到了正在汽車下面修理的 Samson 身上。一位名叫 Winnock 的騎摩托車的人希望 Madeleine 的小女兒 Doris 和他一起離開法國,但 Doris 還沒有成年,需要她母親的同意。離考試還有 15 天,Doris 甚至不願意向她母親提出要求。一位陌生人找到 Samson,請求使用電話。這個陌生人名叫 Humbert,他希望與 Madeleine 通話,Madeleine 是他的妻子,也是加油站的老闆。18 年前,Humbert 拋棄了 Madeleine,現在他不願空手而來,他告訴 Madeleine,自己只剩下一個月的生命,因為肺部患了癌症。他希望在去世前與 Madeleine 處理好財務問題。與此同時,Madeleine 的二女兒 Maud 曾經離過婚,正在和她的未婚夫 Thomas 討論結婚計劃。Thomas 是一位醫科學生。然而,Thomas 離開後,Maud 馬上打電話給另一個男人,安排秘密約會。Maud 和 Doris 遇到了他們的父親,他再次解釋說他回來是為了避免在他死後出現法律糾紛。Humbert 向 Maud 和 Theresa 詳細說明,他離開家是為了成為一名畫家,現在擁有 100 幅可能很有價值的畫作,打算將這些畫作留給她們。在他有生之年,Madeleine 無法在沒有他同意的情況下出售加油站。無處可去,Humbert 便前往 Tut-Tut 在樹林裡的小屋。第二天早上,Maud 在汽車裡醒來,她身旁是她的情人 Richard。除了 Samson,沒有人注意到這件事。Samson 諷刺地將 Maud 的內褲和長襪掛在汽車的天線上。Doris 告訴她母親,她想在 Maud 婚禮之前離開家。在森林裡度過一夜後,Humbert 又添加了一個解釋他離開的原因,18 年前,他發現了妻子與她情人之間的信件。Madeleine 感到驚訝,但毫無悔恨,她拒絕了 Humbert 住在她家直到他去世的願望。Winnock 怒氣衝衝地回來了,因為 Doris 沒有在他們約定的地點出現。然而,他很高興拿到了 Doris 父親的書面同意書,這使得他們可以前往西班牙聖塞巴斯蒂安參加搖滾音樂會。然而,Madeleine 拒絕給出她的同意,直到 Doris 獲得高中畢業證。Richard 回來尋找他遺失在汽車裡的錢包和刀子。Theresa 並不知道這個男人是她的妹妹的情人,她坐上了 Richard 的車去為她的姐姐購買結婚禮物。在婚禮前夜,Thomas 對 Maud 的婚紗讚不絕口。然而,Thomas 一離開,Maud 就再次打電話給 Richard,但她只能打到他的語音信箱。“是我,又是你,”她在電話裡說。“我渴望你,渴望我們。我需要你,我們必須見面。”當 Richard 突然出現,告訴她他打算加入他朋友在塔希提島開設的影片店時,她感到很驚訝。儘管如此,Richard 仍然想要她,猶豫之後,Maud 也想要他。然而,Pinnock 打斷了他們的談話,準備前往西班牙。但 Doris 看到 Richard 之前和 Theresa 在一起,現在又和 Maud 在一起,感到很驚訝,她此刻不想跟隨 Pinnock。Maud 擔心 Richard 在和 Theresa 做什麼。因此,她大量喝了茴香酒,然後搖搖晃晃地走進樹林去見她的父親。與此同時,Samson 已經修好了汽車。在婚禮當天,Thomas 發現只有 Richard 和 Theresa 的客人以及大量掛在牆上的抽象畫,感到很沮喪。Thomas 認出 Richard 的車,因為幾天前,這輛車曾經在他面前魯莽地行駛。整個家庭遲到了 15 分鐘,才趕到市政廳,但 Maud 的婚紗破了,而且很髒,Humbert 的衣服也因為在樹林裡躺著而沾上了泥土。Thomas 非常生氣,抓住 Maud,Maud 於是打電話給 Richard 求助。當 Thomas 問她為什麼打電話給婚禮上的客人求助時,Maud 坦白說 Richard 已經是她幾個月的情人了,Theresa 聽到後感到震驚。Thomas 威脅 Richard,Richard 拔出刀子,Thomas 則拿起了傳動軸,過分興奮的 Tut-Tut 則向 Richard 潑汽油,Madeleine 拿出打火機阻止這場爭鬥。Thomas 對整個事件感到厭惡,他將戒指扔在 Maud 的腳下,然後離開。Madeleine 打算關店,她將標緻汽車送給了 Samson。Samson 需要考慮一下。Richard 仍然有可能讓 Maud 加入他。Theresa 認為 Richard 的評論對她的女兒很不禮貌,但她仍然無法抗拒這個男人。Doris 仍然不確定是否要跟隨 Pinnock。
